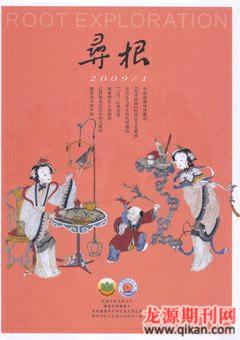曉云褚家
褚納新

一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一位老人,因與我同姓,從而聊起了家事。老人說:姚北褚姓的先祖是從四明山遷徙過來的,褚家的肇基之地是在一個叫曉云村的地方,幾年前他從山里的朋友處打聽到曉云還有一座褚氏祠堂,他很想去看看。我們約定擇日同行。
一個月后的一天上午,我與老人一家五口一起驅車同行,從陸埠鎮袁馬村盤旋上山,午后到了曉云村境內。入村數里,只見一座漂亮的石橋橫跨于山溪之上,宛若長虹。這是一個依山而成的古村,一條大溪由西而東貫穿其中,綿延數十里,村邊竹影婆娑,山上青翠環繞,如詩如畫之中盡顯出山鄉的清幽與恬靜。
曉云原名曉嶺,位于浙江省余姚市鹿亭鄉境內。相傳張果老云游四明時,見群山間有一條大溪蜿蜒東去,正值霞光漸生,溪水泛起的七彩光芒燦如錦帶,張果老以為是仙境,騎驢入境后,方知是人間,遂起名為:曉嶺。1940年整編地名時,把原曉嶺、云巖二鄉合并為曉云鄉,1958年,曉云鄉又納入了鹿亭公社,現在的曉云村屬鹿亭鄉管轄,是四明山區最大的自然村之一。
二
清人有詩云:“翠絕群山異秀鐘,屹然水口擁雙峰。尖巍并指云和日,黛媚叢凝竹與松。”詩中描繪的正是曉嶺褚家村的旖旎風光。村中曾有曉嶺八景,分別是:雙峰聳翠、曉嶺凝煙、石筍參天、巖魚戲水、九曲呼嶺、七星名巖、洞橋石砌、三井天成。這是一座有著豐富歷史文化底蘊的古村落。據道光三十年(1850年)重修的忠清堂《姚江四明褚氏宗譜》記載:姚江褚氏奉東漢關內侯褚招為鼻祖,唐朝河南郡公褚遂良為本祖。北宋初,遂良公裔孫褚昭亮由明經仕昌國州,轉明州奉國軍節度使,由河南遷于鄞,生頊、頊二子。頊官臺州觀察推官,分居寧海新寧;(豈頁)官明州錄事參軍,遷居慈溪金川。(豈頁)長子褚理,登進士第,仕至翰林學士;褚理長子彥仲,字唐輔,嘉祐八年進士,封榮祿大夫。彥仲公玄孫褚邦英南宋時以賢才舉仕,官鎮江錄事參軍,辭官后隱居于越州余姚四明曉嶺,經近千年的繁衍生息,遂聚成今日有一萬余后裔的浙東大族。
當我們的車子停在村頭,幾位村民熱心地迎了上來,聽說我們是從姚北前來尋根的褚家族人,他們顯得更加熱情了。一位村民說,始祖太公的墳墓還在曉嶺崗二十九甲。一位叫超根的族叔說愿意帶我們上山。一路上,超根叔說:“曉云村是個船形村,祖上傳言,這始祖墳是桅,是曉嶺村的活龍地,風水極好,褚氏子孫世代不能在墓邊動土。”我們從一條鋪著不規則石條的山徑上山,行半里多路,果然在藤蔓密布的山岡上找到了一處由山石壘成的墓基,超根叔欣喜又帶著幾分惶然的神色說:“這里就是。”始祖墓背靠青山,前臨山谷,沒有墓碑,沒有禁石,千百年來,山下的子孫們一直默默地守護著這座祖墳,誰都不敢犯這祖先的大忌。
從山岡上極目遠眺,山鄉的景色一覽無余,青煙繚繞中,曉嶺村果然就像一葉飄浮于青山綠嶺間的小船。從山上下來,已有七八位族中老人在村口等著我們,我們的到來,顯然激起了他們很高的熱情。從他們布滿老繭的手掌、古銅色的皮膚及濃郁的山里話可知,他們都是曉嶺的山農,但當我說起了先祖褚遂良,我竟驚詫于這些族老們的見識,“唐朝的宰相”“唐朝的大書法家”,老人們都能說上一二.一位老人面露自豪地說:“遂良公是我們的太祖公,我們都是宰相的后代啊!”
聽說我們是來宗祠祭祖的,族老們執意要帶我們去看村中的家廟。這是一座讓山村人自豪與神往的地方,是近幾年由村民們集募所建。大殿氣勢宏偉,木結構仿古構建。步入大殿,香樟味與油漆味混合著撲面而來,殿內供奉著的是披著黃袍的大王菩薩,案前香煙繚繞,蒲團上坐著好幾位正在一心念佛的老太太,這難道是曾經的褚家祠堂嗎?在廟里,我們感到有些失落。穿過大殿,里進是一座建于上世紀80年代的大樓,從室內的黑板可知這里曾經是所學校,在三樓一教室內,我們驚喜地看到了族老們保存著的一塊道光年間的匾額,上有“石君祠”三個大字,右側書有“道光乙酉年小春月重建,小峰方庶敬書”,左側書有“董事褚可才、褚文林敬立”字樣。
三
據傳姚江褚氏曾有三廟六祠,褚氏大宗祠正殿曾懸掛有宋大儒朱熹所書“忠清堂”金匾以及明褚模所書“德澤昭敷”“永鎮乾坤”等七八方大匾,祠堂內供奉著褚招、褚遂良等列祖列宗的牌位。據宗譜記載,明清時期,姚江褚氏有不少后裔因經商、宦游而分居于松江、湖州、仁和、乍浦、峽石、南京、象山等地,在余姚境內,褚姓的分居范圍也較廣,在縣城、梁弄、烏坭塘、低塘、深坑、高巖、王家莊、里巖頭等地均有曉嶺褚氏后裔徙居。說起家祠,同行的老人動情地說:新中國成立前在姚北也有兩座褚家祠堂,一座在低塘堰東,規模恢宏,另一座在周巷萬壽寺旁,規模略小。可惜兩座祠堂如今都已拆毀了。一位老人說:“曉嶺村還有一座祠堂,叫忠清堂,如今還在,可惜快坍塌了!”沿著曉嶺村的老街,步行500余米,果然見到一座古老的建筑,就是祭祀遂良公的“忠清堂”了。
如今的忠清堂,已經是一座處于風雨飄搖中的古祠了,祠內雖然還完整地保留原先的格局,但主廳的一間已坍塌,廂房的門窗飄零四落,天井內彌漫著因柴草霉爛而產生的氤氳味。殘垣斷壁間,我們茫然地徘徊。終于,在大殿的側墻邊,我們發現了一通鐫刻于道光二十四年的“忠清世家”祠碑,石碑寢風沐雨,疏松的石質已隨歲月層層脫落,我們站在瓦礫與荒草間辨認著碑文,心中涌上陣陣酸楚。
這是一座孤寂的古祠,顯然已被世人遺忘了。當人們在書房里抱著景仰的心情對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帖百臨不厭時,斷然不會想到有一座紀念褚公的祠堂竟在這山村的荒涼間任歲月侵蝕。從宗祠出來,我們心里似乎罩著一層陰霾,時代的變遷,萬物的消泯,總是讓人恍惚。走出古老的市弄,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座漂亮古樸的石橋,這就是我們剛進村時看到的那座古橋,名“大方橋”,曉嶺八景中的“洞橋石砌”就在這里。只見規整的石條泛著苔綠,層層相疊,一如山鄉人的耿直與狷介。在橋畔,我們逗留了很久,陪伴我們的族老們已一一與我們告別,我們卻久久不愿離去,也許是因為眷戀這山鄉美麗的景色,也許是因為這心底里涌動著的不舍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