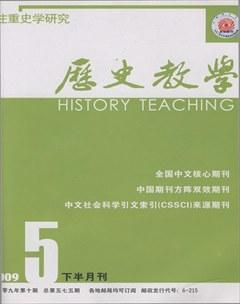民國時期家族文化的歷史嬗變述論
李永芳
[摘要]民國時期,延續數千年的傳統家族文化受到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人等諸種社會力量的不斷沖擊,但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家族組織仍保持著比較完整的形態,維系家族情感和活動的實體普遍存在,維持家族團結的祭祖等活動綿延不斷,族長的權力亦得到不同程度的承認。究其主要原因是延續數千年的中國傳統家族文化根深蒂固,物質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制約,歷屆政府對家族制度的保護和利用等。
[關鍵詞]民國時期,家族文化,宗族制度,要素嬗變
[中圖分類號]K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57-6241(2009)10-0030-07
家族文化即指由血緣、地緣以及業緣關系所產生的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家族亦稱宗族,自殷商時期即成為基本的社會組織。至清代,家族無論是在制度上還是在觀念上都已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民國時期,延續數千年的中國傳統家族文化受到了所未有的沖擊與挑戰,卻未發生根本性的變革,本文就此做一粗淺探討。
一、民國時期各種社會力量對傳統家族文化的沖擊
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一書中就提出了改造家族主義為國族主義(即民族主義)以圖救國的主張,指出:“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在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因此,必須對家族進行改造,“合各宗族之力來形成一個國族,以抵抗外國”。辛亥革命期間,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對封建家族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認為其“扼殺自由、剝奪人權,提倡愚昧,是夫權、父權、君權等強權的根源”,強調“要推翻滿清王朝的專制統治,揭開社會革命的序幕,必須從家族革命開始做起”。
“五四”前后,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與發展,一大批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掀起了批判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浪潮,家族文化成為被批判的重點對象。其批評的揭橥者章太炎在提倡反清排滿的民族主義時,指出宗族的小團體主義妨礙民族的統一,“偏陋之見,有害于齊一明矣”,現在必“定法以變祠堂族長之制,而盡破宗法社會之則矣”。被稱之為“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的吳虞認為,家族是宗法國家與社會的“基礎”,封建專制主義的“根據”,其危害“不減于洪水猛獸”。在這種社會,“人民無獨立之自由,終不能脫離宗法社會,進而出于家族圈以外”。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陳獨秀對于家族主義的批判更具有系統性和理論性,指出宗法制度具有四大惡果,即“一曰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礙個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剝奪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如尊長卑幼同罪異罰之類);一曰養成依賴性戕賊個人之生產力”。要改變“種種卑劣、不法、殘酷、衰微之象”的關鍵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家族主義的社會根源和危害進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家族制度是兩千年來中國社會的“基礎構造”。強調要推翻封建專職統治和批判封建禮教,就必須消滅封建家族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學者們全面批判家族制度的呼聲中,還有“不少年輕的社會活動家、青年學生乃至少年”亦積極投人與之呼應。“他們向父兄及周圍的人作宣傳,并投書于報紙”,倡議“廢除姓氏與不要遺產”“取消輩分”,“主張組織小家庭”等,“使得反對家族主義的思潮在一個時期內來得相當猛烈”。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更多的是從革命實踐出發對家族主義予以批判,形成了家族革命的理論主張及其政策實踐。其家族革命的理論主張大致可歸納為三個方面:其一,族權是封建宗法社會的四種權力之一。“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其二,以農村階級分化戰勝家族主義。“村子內階級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義不能戰勝”。其三,破壞家族主義應講究策略方法。“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中國共產黨關于家族革命的理論首先在轟轟烈烈的農村大革命運動中付諸踐行。對此,毛澤東在1927年3月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曾進行過生動的描述:“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成為農民運動中的十四件大事中的“第七件”大事。“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著動搖起來。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營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不敢再侵蝕祠款。從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殘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了。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總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隨著農民權力的升降而動搖。”在其后蘇區及解放區所制訂的有關政策和實踐中,中國共產黨關于家族革命的理論亦有著充分的展現。如在1930年5月的《全國蘇維埃土地暫行法》、1931年11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1934年12月的《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員會沒收和分配土地暫行條例》、1946年7月的《中央實現耕者有其田提議》、1948年10月的《中原局減租減息綱領》等文件中,均規定:“凡屬于祠堂、廟宇、教會、官產……占有的土地,一律無償沒收。”因為“這些祠田、廟宇、教會、官產……等土地,大半都是歸豪紳、僧尼、牧師、族長所私有。即或表面上是一姓一族或者當地農民公有,實際上還是族長、會長、豪紳所壟斷,利用來剝削農民,所以這樣的土地一律沒收。”“族地、社地、公地、學田,應由本族本社本村本地區人員組織管理委員會管理之,其收入除依法收繳負擔外,應經公議充作公益事業之用。”不難看出,中國共產黨關于沒收一切宗族所有公共財產的規定,其目的就在于既能促進農村階級的分化,又能使宗族失去其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以便從根本上消除農村宗法勢力。
同時,民國時期頻繁的戰爭以及經濟生活環境的惡劣,迫使農村人口大規模地遷移,亦形成了對家族文化的較大沖擊。從北洋軍閥之間的直皖戰爭、兩次直奉戰爭等,到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蔣桂戰爭、蔣馮戰爭、中原大戰以及西南軍閥的內部混戰等,再到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等,幾乎連年不斷的戰火加之災荒頻仍,致使農村社會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農民經濟生活環境惡劣,其或為逃避戰禍或為外出謀生的背井離鄉現象甚為普遍。如據史料記載,民國年間流入東三省即“闖關東”者就有3000萬人左右。抗戰8年間移入內蒙、青海、甘肅、新疆、寧夏等地即“走西口”者亦在3000萬人以上。20世紀30年代流往東南亞等地即“下南洋”者約達800萬人之多。這種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對于族民的聚居方式、宗族的儀式和活動等,無不產生一定的影響。
二、民國時期家族文化嬗變的有限性
通觀民國時期的傳統家族文化,首先我們應當肯定,其在前述各種社會力量的不斷沖擊之下開始發生前所未有的漸變。尤其是在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洗禮的地區,由于貧苦農民因獲得土地而免去了對宗族土地的依賴,“宗族等級秩序失去了經濟的基礎”;革命使民眾認識到了民主和平等的意義,“家族制度中人為的等級意識受到沖擊”;革命也使廣大農村貧雇農的階級覺悟大為提高,“對于地主階級、壓迫階級,不管同姓不同姓,同族不同族,均不再視為同路人了”;革命還使鄉村權力機構中起作用的分子發生了變化,“既不是長老專政,也不是族長專權”,而往往是那些“比較能適應新興政權的要求”的“家境中等或中上的壯年分子。他們比較能適應新興政權的需要”。總之,經過革命之后,“宗族勢力逐漸在鄉村中失去其決定性的影響”,“宗族的活動變得越來越狹窄和不經常”。
但是,我們認為,民國時期諸種社會力量對于傳統家族文化的沖擊作用畢竟是有限的,傳統家族文化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孫中山雖然提出了改造家族主義為國族主義的主張,但并沒有提出如何使家族聯合為國族的具體辦法,更沒有付諸實踐中。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雖然對于傳統的家族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但這種囿于學界的吶喊并沒有滲透到幾千年來孕育滋養家族文化的鄉土民間。誠然,共產黨在國民革命時期領導開展的以兩湖地區為中心的農村大革命,委實使家族勢力“隨著農民權力的升漲而動搖”了,但其成果僅限于較小的范圍之內,且這些變化隨著國民革命的失敗很快又得到了恢復。其后共產黨在蘇區、解放區所主張的家族革命及其政策實踐,也“至多是清除了村落家族中血緣關系的外化形態,其內在機制沒有受到損傷。因此,那個時代對村落家族文化的改造沒有明顯的成效”。
概括民國時期家族文化嬗變的有限性,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以血緣與地緣統一為基礎的家族組織仍保持著比較完整的形態。
由于受千百年來敬宗收族理念的影響,傳統的“聚族而居”的現象在民國時期仍然普遍存在。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調查時曾經指出:農村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無論哪一縣,封建的家族組織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個村子,或一姓幾個村子”。美籍學者黃宗智研究認為,在南方的廣東、福建、江西等省,“多同姓的村莊”,而在華北平原,“多姓村占的比例較大”。其實,無論江南或華北,結構龐雜且比較富有的家族均還存在。1942年張聞天在神府縣的調查統計表明,“每一個村子都是同姓的,某些村子內雖夾雜著少數外來的異姓居民,但那是無足輕重的”。宗族的輩序關系也很明了,“全村內同一輩的名字均以同一字放在名字的前或后,以資識別”。另據1940年至1942年日本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對河北、山東的調查也證明,“在廣大的農村,宗族勢力仍是很強的”,如冀南的欒城縣及附近的元氏縣,“許多村莊仍是一族占統治地位”。
第二,維系家族情感和活動的實體仍舊普遍地保存著。
具體來講,一是族田在各地普遍存在。據陳翰笙在20世紀30年代的調查研究,在江蘇的無錫縣,族田約占耕地的8%。在廣東的惠陽縣,則約有1/2的土地屬于宗族。廣東“全省的太公田約占全部耕地的30%,總數約1260萬畝。”另據美國學者莫里斯·弗里德曼的研究統計,在廣東東江流域,有的地區族田所占比例甚至高達74%之多。毛澤東1930年在江西“尋烏調查”中也提到該地區土地中“公田”多達40%。在華北平原雖因人多地少和土地分散等緣故而族田相對較小些,但據“滿鐵”的調查統計顯示,其大宗族也有族田很多的,如山東青島孫氏宗族鼎盛時就有族田3000余畝,到30年代仍有1000余畝。二是祠堂在各地大量存留。如在福建莆田地區,“該縣城中諸世族有大宗祠、小宗祠,歲時宴饗,無貴賤皆行齒列,凡城中之地,祠居五之一”。另據陳禮頌1934年在廣東潮州斗門鄉的調查,全村有祠堂11個,其中陳氏宗族有祖祠10個,外姓林氏有1個。陳氏祠堂中有宗祠2個,其他各支、房祖祠8個。三是族規傳統在各地均有保留。族規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仍以潮州斗門鄉為例,該鄉各姓宗族均無成文族規,卻均有各自不成文的習慣規定。如陳氏宗族習俗,規定不許贅婿,孀婦不得另招姘婿,而夫死再嫁則不加限制,這在其他各族中則無此種規定。但在瀆犯長者、奸淫、偷盜等方面,均是各族所嚴禁的。在各地存留的成文族規中,大都對本姓宗族和家庭活動的各個方面有著嚴格而細致的規定。如灄水吳氏1948年纂修的《吳氏族譜》,其內容涉及宗族和家庭活動的奉法、敦本、追遠(祭祀)、服教、立品、務業、尚學、內教、立嗣、戒賭、息訟、御侮、慎終(喪葬)、蒙養、睦族、往來、保家、事上等各個方面。其根本指導思想仍是以封建的倫理道德為基礎,糅合封建法律的部分內容,以宗族的倫常名教、價值觀念、族群意識,約束管理族眾。四是族學在各地亦有保留。雖然該時各地鄉村均廢除了私塾和義塾而改為學校,但學校大多設在宗祠內,且多由宗族控制。如潮州斗門鄉小學校即“由陳氏宗族辦成,雖采新學制但宗族色彩仍濃”,“陳氏子弟入學,富者交學費8元,貧者可交5元,確無能力的并可減免,而外鄉雜姓均得交7或8元,無減免之說”。
第三,維持家族團結的祭祖、拜會等活動仍舊綿延不斷。
據史料記載,無論是江南還是華北等其他地方,族民祭祀祖宗活動香火相傳,從未間斷。其或是在宗祠中進行,謂之祭祀,亦稱祭祖,此種活動多在春節進行;或是在墳墓邊進行,稱之為祭墓,亦稱掃墓,此種活動多在清明節進行。有的地方還有“做忌”之舉,即每逢共祀的始祖考妣的生死忌日,也要到宗祠里行祭。各支派、房派的近親祖考亦是如此。祭祀完之后,常有全族或全族男性的宴會。祭祀和宴會的費用,出之于族田的收入,族田過少者則由族內各家湊出。除清明節外,其他年節族人也常常舉行相互性的拜訪活動。另“在紅白喜事之時,族人也進行聚會”,以追先念祖,聯絡親情,增強家族團結。
此外,村民的精神娛樂也往往是通過家族活動來獲得滿足,“鄉村中的廟會、燈會、社火、社戲等等娛樂活動,幾乎均以家族出面組織,或各個家族聯合組織”。
第四。族長的權力仍得到族眾以及官方的承認。
族長不僅在祭祀禮儀和日常族務中起著重要作用,而且在分家析產、收養義子、土地買賣中擔任重要角色,“收養契約、分書、地契上均需有族長的簽字畫押”,“族長的權威并得到官方承認,在審理涉及家族成員的案件時,往往向族長征求意見”。黃宗智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中指出:在冀—魯西北平原上,村莊的權力結構仍然“根植于自然村的宗族組織。族內的紛爭,例如分家時的爭執,通常由族中威望高的人出面調解。在理論上,那些族長是族中輩分和年
齡最高的人。但實際上,他們常是族中最富裕和最能干的人。無法在族內解決的事項,例如異族間的紛爭,或村莊與外界(特別是有關賦稅方面)的交涉,則由各族的領袖組成的‘董事協商處理”。社會學家林耀華1933~1934年間在對福建義序地區的調查時也發現:“宗族的族長和鄉長,乃全族的領袖,兩人同心合力,共掌族權。族長的任務稍為偏重祠堂祭祀與族內事宜,鄉長的任務則偏重于官府往來,在外代表本鄉。地保任務在于奔波,報告并庶務事宜,臨時案件發生,由地保請命于族長或鄉長。官府派差來鄉,先見地保,由地保引見族長鄉長。”
由上述可見,民國時期家族文化無論從組織結構上還是從功能作用上講,其在政治、經濟、教育、司法等方面仍具有較強的生命力。族權與政權交融在一起,成為調節和疏導鄉村社會的重要力量。
三、民國時期家族文化未曾發生根本性變革的主要原因
究其傳統家族文化在民國時期未曾發生根本性變革的主要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延續數千年的中國傳統家族文化的根深蒂固。從兩千多年前孔子為起始,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的正統文化即脈承了中國家族文化。孔子所主張的“克己復禮”,就是要依照比他更古老的周禮來恢復當時的社會秩序。而周禮則起源于原始氏族的血緣生活方式,其核心是尊敬和祭祀祖先。以血緣父家長制為基礎的“等級制度是周禮法規的脊梁,分封、世襲、井田、宗法等政治經濟體制則是它的延伸擴展”。“儒家學說起的作用就是放大原始群體中家族主義的血緣秩序,并由此引出其他觀念”。儒家學說的核心概念之一“仁”,就是“從血緣的孝悌中發凡而來”,即《論語·學而》所云:“弟子人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儒家學說的另一核心概念“禮”,亦充分體現著“宗法血緣關系的紐帶作用”,即《禮記·哀公問》所云:“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至于儒家學說突出強調的三綱五常,則“更大程度上保留了血緣社會的成分。血緣社會的秩序關系劃定,尊卑長幼男女之序實為家族文化之大義”。兩千多年來,儒家學說盡管曾經受到多次沖擊,但其“作為傳統社會的正統文化將村落家族文化理論化、規范化和普遍化,使其適應于傳統社會治理的需要,這個過程本身又鞏固和強化了村落家族文化的內在邏輯”。同時,在封建社會中,“王權止于縣政”的社會體制雖無能力滲透到村落家族,但它往往通過與村落家族體制的接軌來實現其統治和調控,即利用血緣秩序服務于社會政治秩序,“以血緣親屬關系為主導的社會關系,使得習慣機制成為社會及法律調整的基本規則和手段”。由此可見,這種延續數千年的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家族文化決非一時所能夠撼動的。
其次,物質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制約。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村落家族共同體一直處于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狀態之中,時至民國時期依然如此。“由于傳統的生產方式和落后的交通工具的限制,人們之間的聯系只能是建立在自然血緣關系和狹隘地域統治,服從宗族關系基礎上的地方性聯系”。社會資源總量的匱乏意味著社會不能從宏觀上為其社會成員提供必需的生存資源,村落家族共同體也就必然成為承擔這一責任的群體。美籍學者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中曾對此進行過較為具體的描述:同族之間,無論有無共同的財產,宗族成員之間的經濟協作作用十分明顯。家族成員在告急時往往求助于同族成員。在承租土地及借貸銀錢中,同族之人往往充當中人和保人,一無所有的債(佃)戶也往往求救于自己所在的宗族,后者也盡其所能幫助他維持生存,如動用族倉或義倉存糧等。也有將族田族內較貧者,由他象征性地交一些地租或僅為祭祖時提供一點祭品和香火。族內田地多者也應首先租于本族人耕種。在土地買賣中,族人往往有優先購買權。”不難看出,民國時期物質生產力的發展還遠遠沒有積累起足夠的能量,以沖垮家族文化這一牢固的社會生活體制。
再次,歷屆政府對家族制度的保護和利用。民國年間,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南京國民政府,均對家族制度采取的偏向于保護和利用的態度,以穩固其封建專制統治的社會基礎。北洋政府在1912年頒布的《暫行新刑律補充條例》中明確規定,尊親屬可以任意毆打幼卑,而幼卑不得抵抗。即使尊親屬傷害了幼卑,只要“僅致輕微”,亦可視其情節“免除其刑”。其在民法方面規定,“家政應統于尊長”。對于財產權“尊長當然代表卑幼”,如果卑幼對財產擅自處理,“其處分乃無權行為,依法非經尊長追認不生效力”;對于婚姻“現行律裁,婚娶應由祖父母、父母主婚”,“是婚姻不備此條件者,當然在可以撤銷之列”。南京國民政府更是希望利用家族這一固有的社會組織基礎,實行保甲制度,推行縣政、地方自治和社會建設,以輔助其政權統治。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強調:“要知道中國古來建設國家的程序,自身而家而族,則系之于血統。由族而保甲而鄉社,則合之以互助。由鄉社以至縣與省,以構成我們國家的大一統的組織。故國家建設的基層實在鄉社。”“由于個人日常生活的箴規,推而至于家,則有家禮、家訓,推而至于族,則有族譜、族規。在保甲,則有保約,在鄉社則有鄉約和社規,其自治的精神,可舉修齊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在20世紀30年代推行新生活運動中所提倡的“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四維八德”,即是以家族倫理的核心“忠孝”為其自治的根本,推崇“為國家盡全忠,為民族盡大孝,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實為我們中國教忠教孝的極則”。在南京國民政府推行的保甲制中,總是“盡量地把同姓編在一起”,由宗族組織發揮其保甲“相鄰連坐、互相監督”的功能,保甲的首腦“幾乎全是宗族的首領所擔任”。“官方的權力除非與宗族組織結合,否則難以在農村中發揮作用”。在所推行的鄉村自治中,“區長、鄉長、村長、里長等,都由宗族當權者所薦之人充任,有許多族長干脆就自己兼任這些職務”。顯而易見,家族文化正是有了這種政權的支持與保護,才得以在動蕩的社會中保持了較為超然的自治狀態,在與鄉村政權形成的互補關系中得以延續。
責任編輯:侯林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