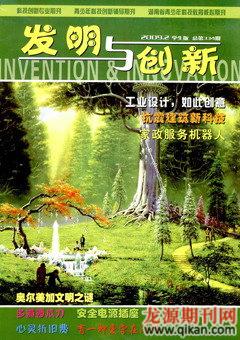用心追尋遺失的文明
劉麗珠
我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筆卻比過去寫的任何文章都顯蒼老。
——余秋雨
剛讀完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我的心仿佛被那種精魂招了去,情不能已地也跟著“苦”了一程。從巍巍敦煌,一鞭殘陽里,策馬來到江南小鎮。祖國的大江南北,到處都是古老民族厚重的呻吟。江南小鎮的淺渚、波光、云影、小橋、流水、江村,唐代天柱山上的漫漫艷情和浩浩狼煙,久久不能揮去。西湖舊日的美夢已逝,南京城邊的殷殷血火似乎還在那里燃燒。
天柱山,多少文人墨客、游子騷人的向往之所。李白、蘇軾、王安石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向往著能在天柱山歸隱,安度晚年,把去天柱山說長成是“歸來”。濃厚的宗教氣息、爭富的歷史底蘊,給人有了居家的感覺。但不斷的戰火幾乎燒毀了每一座寺院、樓臺,留下一條挺像樣子卻又無處歇腳的山路,在寂靜中蜿蜒。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是游人集聚最多之所,西湖美夢是很多人都想重溫的。可這里,除了雷鋒塔下白娘子凄美的故事,便什么也沒有了。或許是為了那位淚濕青衫的落魄詩人吧,要不就是和那享盡山間明月、永不消褪的蘇子有關。
而今,白堤依舊,蘇堤惟柳。不過,自命清高的林和清可有些悲涼。春去秋來,梅凋鶴老,只剩下那片片梅瓣、鶴羽,像書簽一樣,夾在民族精神的史書里。其實,他們都有些悲涼。西湖成了景點,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_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風舞的楹聯;再也找不到慷慨的遺恨,只剩下既可憑吊又可休息的亭臺。修繕,修繕再修繕,但無論怎樣修繕,這里總是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著的苔藻似乎也已千年。
南京,六朝金粉,這足能使它名垂千古,何況它還有明、清兩代的政治大朝,走近它,仿佛能從刀光劍影中嗅出一縷粉香。其實,它是把歷史溶解于自然。玄武湖邊上的古城,明故宮的遺址,雞鳴寺的鐘聲,明孝陵的石人,秦淮河的流水、漿聲、燈影,夫子廟的店鋪。棲霞山的秋葉,靈谷寺的林蔭道永遠那樣令人心醉。王者之氣與神州最佳的風水交匯一處。在陣陣京華煙云里,我們遙望到的卻是血流成河、橫尸遍野,它再也不能安靜地陶冶自己的情操,滾滾紅塵中,它少了那份閑情。
一路走來,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看到了故都昔日的繁華與興盛。又怎能不心潮澎湃、豪氣滿懷?但是它還是經不起時間的淘洗。開卷那位“錯步上前的小丑”總是那樣討厭地出現在眼前:西天凄艷的晚霞里。斯坦因臉上的猙獰,大清帝國道臺的貪婪,小丑的深深鞠躬,一同上演著那簡單的童話。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車,又一大車……洞就這樣空了,窟就這樣殘了,沒有人攔下那些車隊。可那時,真要攔下了,車隊又將駛向何方?
野蠻的戰火,無邊的愚昧,焚燒著脆弱的古跡,吞噬著易碎的智慧,只剩下殘垣斷壁,殘書敗頁;只剩下那令人可笑的儺祭、儺戲,完全失去了古老的韻味。這又怎能不讓我們憤怒呢?厚重、深沉一起襲來,我們中國人到底做了些什么?那些精髓和精華為什么會毀于一旦呢?那些文明的過去不能留存至今,這是多么可悲。
空寂無人的山巒,凜然躺臥的萬古湖水。沉默不語的閣樓,見證歷史的強蠻,映照著我們的過去,但此時還有什么值得我們驕傲的呢?余先生似乎在用筆慢慢剝去那層遮羞的面紗,赤裸得讓人后怕。所有的一切都歸于安寂與平靜,任何歇斯底里的呼喊。都無法穿透歲月的痕跡。歷史的塵墻。也無法喚醒那些無知愚昧的靈魂。
掩上書卷,痛徹心扉、撕心裂肺恐怕都無法形容。只有讓不爭氣的淚滴成冰冷的血,化成歷史前進的動力、今日奮斗的源泉,然后振臂一呼,現在的永遠也不能失去。從今天起。華夏的文化之路,不再是一程苦旅。
點評:讀一本好書,是能扣動心弦的,習作者似乎為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所牽引,和作者一道為燦爛的中華文化而歌、而泣,懷揣對民族文化漾深的愛而成就了此文,更“成就”了一線希望:“從今天起,華夏的文化之路,不再是一程苦旅”。
(指導老師:謝墨海)
- 發明與創新·中學生的其它文章
- 比星星小等
- 搞笑一族
- 追求的真諦
- 機會,只是舉手之勞!等
- 感謝兩棵樹等
- 隱忍是成功的最好階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