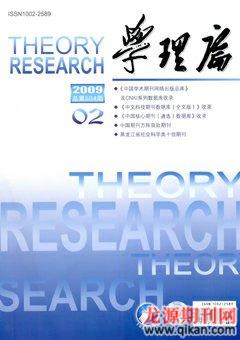公民權利發展與國家的階級性
盧 軼
摘要:通過研究當前我國的民主形式,文章提出需要建立保障公民權利平等的人民民主憲政框架,以推動中國政治發展與保障國家的階級性。
關鍵詞:公民權利;階級性;人民民主
中圖分類號:D03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2589(2009)02—12—02
一、公民權利與國家的階級性
T.H.馬歇爾1949年在倫敦經濟學院發表演講,內容后來被收錄在他的《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一書,并于1950年出版。書中探討了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權利關系的變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正由階級權利社會向公民權利社會變化,他的研究與分析,對思考當今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下,怎樣保障政權穩定、推動民主發展具有啟發意義。
馬歇爾認為階級社會建立在人的財產與身份不平等的基礎之上,相應的制度安排表現為一個階級統治與壓迫其它階級,但到了18世紀以后,西方公民權利的發展使這種狀況發生了改變。馬歇爾認為,源于市場經濟、形成與發展于18世紀、19世紀、20世紀的公民基本權利、公民政治權利與社會權利,導致了憲政、平等的選舉與被選舉權,包括教育平等在內的國家福利制度的產生。如憲政保障公民個人享有平等的自由;公民享有平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能夠通過投票選舉與被選舉,進行平等的對話,表達政治意愿與實現個人利益,改變了以往必須通過革命才能消除的階級利益沖突;國家通過福利制度建立了社會教育、經濟及其它方面的平等,使公民獲得平等參與競爭的機會,并由此使國家獲得了統轄社會的地位,能夠利用這個地位進一步消除階級沖突。馬歇爾認為,以上制度形成一套整體的制度,體現為階級壓迫與階級特權消失,最終將把西方國家由階級社會轉變成了公民權利社會,“它不再僅僅試圖減少社會最底層階級的貧困所帶來的明顯痛苦,而開始采取行動以改變整個社會的不平等模式。它不再像從前一樣只滿足于提高作為社會大廈之根基的底層結構,而對上層結構原封不動;它開始重建整個大廈,哪怕這樣做可能會以摩天大樓變成平房的結局告終也在所不惜。”[1]“現代形態的社會權利恰恰意味著地位對契約的入侵,市場價格對社會正義的服從,權利宣言對自由議價的替代。”[2]
仔細分析會發現,進入當代社會后,資本主義權利關系較之早期確實有了很大的變化。資本主義國家公民普遍獲得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使他們能夠自由投票;使他們表達利益要求與政治意愿不再需要直接訴諸政治暴力;福利國家制度、反壟斷法等大大提高了普通人的生存與教育機會,為他們加入自由競爭隊伍提供了基本物質條件。但是,由于權利的實現要受到客觀物質與社會條件的制約,因此,規定于憲政中的公民權利遠不是平等的,在這一點上西方國家沒有改變它的階級性。構成西方制度框架中的各項制度間的邏輯關系明白無誤地說明了這一點,比如西方憲法規定了人的各項基本權利,但同時規定私有制與市場競爭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樣人的自由不過是擁有財產與進行個人競爭的自由。個人利益市場競爭必然導致貧富分化,西方的政治制度保護這個結果,如西方憲法規定其民主形式是多黨競爭與三權分離,同時法律允許政治獻金存在,這造成了財產權與政治權的聯系,既只有在龐大的政治捐款的支持下,公民的愿望才能轉變為政治影響力。
二、我國公民權利發展與國家的階級性
馬歇爾的公民權利理論抹殺不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性,但卻在另一角度給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在如何保證政權的階級性與建設民主方面以一定的啟示作用。
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民主革命,到1949年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我國人民的民主權利從無到有。制度上,到建國前夕,形成了一套適應革命條件需要的具體的制度,如民主集中制,干部選撥制、任命制,黨與政府領導的提名制與協商制。從當時的歷史條件看,這樣的制度安排有它的合理性,它與人民的解放事業相一致,代表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方向,反映著黨、政府、官員與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與鞏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
1954年我國制定了第一部人民憲法,憲法規定人民享有各種民主權利,包括言論、結社、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同時指出人民范圍內一切權利平等。經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對資產階級的改造,1956年我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公有制。由于階級斗爭范圍大大縮小,人民民主范圍不斷擴大,革命條件下形成的制度不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1956年中共八大指出,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已經建立,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在國家范圍內消失,階級斗爭不再是主要任務,末來要特別發展民主,要以法律為標準進行社會管理。這實際上開啟了我國由階級斗爭社會向公民權利社會發展的大門。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并再次探索社會主義民主發展道路。中共十六大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法制國家民主建設思想的提出,實際上再次打開了向社會主義公民權利社會發展的歷程。但是,與五四憲法實施的時期所不同的是,五四憲法實施的條件是公有制與計劃經濟。人們的經濟利益一致,容易達成政治上的一致,在此條件下實施公民地位平等的投票與選舉權不易造成國家性質的變化。改革開放后情況卻有所變化,我國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從而把公民權利實現置于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
中國市場經濟不是西方經濟式的個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與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公有制在其中起著主導作用。但是由于公有程度有限,由于國家與社會管理中還存在很多漏洞,當前社會已經出現明顯的分層與利益分化,這些問題完全有可能反映在公民參與、進行利益訴求的政治活動中。例如在選舉上,實行一人一票的“票決”制來決定政治事務,可能產生兩個方向,即個人、集團利益的方向與公共利益的方向,如果個人利益或集團利益方向的規模足夠大,完全有可能危及公共利益,繼而危及人民民主政治基體。所以,多一點民主當然好,但如果傷及民主的基體,那就是在走彎路,未來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能挽回錯誤。
出于這樣的考慮,有人認為不應該用“公民權利”,而應該繼續沿用“人民民主權利”來指稱社會主義條件下個人的民主權利,但實際上,在國家確定了自己的階級屬性之后,公民權利有著更為具體的內容,比如它強調在人民與“非人民”的邊界劃清以后,要怎樣切實保障權利平等;它也意味著,“非公民”的身份是要由法律來界定。可見,只有推動公民權利建設才能真正建立起法制國家。
三、人民民主憲政框架
在以上構成因素中,黨的領導居于重要地位。在現代化與政治發展過程中,制度、法律、經濟發展與公有制形式與程度、政策與政府工作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要對變化進行方向上的把握,必須依賴黨的領導這個變量中較少變化的因素。由于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堅定性、組織結構上的穩定性、歷史地位上的穩固與合理性、人民利益的方向性,使得向社會主義公民權利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必須保持黨的領導。
當前執政黨能夠起到這樣的作用,其一與它與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分不開。西方有人說中國與印度不同,印度實行多黨選舉,但卻發展緩慢,原因是執政者在選民的推動下被動做事;中國只有一個執政黨,沒有成熟的中間組織,但中國卻飛速發展,原因是中國共產黨愿意主動為民做事。實際上,今天中國的改革都是執政黨與政府從上至下推動的,沒有黨的領導很難有中國的政治發展。其二與它的意識形態對社會的領導作用分不開。提出政治官員是“經濟人”假設、在經濟人條件下集體行動不可能的經濟學家諾斯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節約機制,在意識形態的指導下,經濟人會放棄成本——收益計算,朝著意識形態的方向作出集體行動。實際上,今天中國的很多改革措施,不是靠滿足利益要求,而是靠執政黨對黨員的意識形態約束與號召推動的。其三與執政黨主導公共政治理性的形成分不開。社會轉型與發展時期,各項工作處于變化當中,特別是公民權利擴大,客觀上賦予人們更多的選擇與獨立判斷的權利,這時公共理性就非常重要。前蘇聯在進行公民選舉與投票之后,蘇共黨在一瞬之間跨臺,直接原因是蘇共黨放棄了意識形態領導權,放棄了對指導個人判斷的個人公共政治理性的引導。有了成熟、正確的公共理性,社會才會眼光高遠,才能正確認識長遠與暫時利益,才能站在正確的政治判斷基礎上進行政治投票,制度的合法性才不需要建立在經濟的高速發展上,國家與政府才有機會進行結構調整,并在遇到重大挫折時獲得社會的理解。而培植與建構正確的社會公共理性的工作,需要由執政黨與政府通過恰當的意識形態宣傳,具體、公平、正確的政策獲得廣大人民的認同與理解來完成。
在保障公民民主權利方面,目前特別要做的是保障公民在發表意見與批評方面的權利。在言論自由問題上,西方有西方的標準,社會主義中國有中國的標準。資本主義也不是完全言論自由的,公民思想受著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資本主義通過消費娛樂工具消解公共政治空間,使公眾沉溺于消費、娛樂與個人奮斗的夢境中。由于財力與政治影響力的作用,資本主義精英掌握著對思想與言論的領導權。但顯然,中國這方面的制度也是不完善的,中國公民對社會存在的不良或特權現象所進行的監督與揭露,常常因為缺少有力的法律保護而流產。
選舉方面也一樣。選舉可以有不同形式,某些范圍內要直接選舉,更大范圍上要間接選舉,這才有利于穩定。可以做到的必須嚴格推行,比如提名可以“醞釀”,但過程要透明,被選舉人的決心、財產狀況、受獎懲情況應該為選舉人所知道,這才有利于選民監督與做出正確的判斷。在有條件進行直接選舉的范圍內要進行直接選舉,比如在單位內部推行民主選舉,這才能在社會養成民主習慣,讓民主理念與精神在中國社會扎下根來。
總之,和平年代加強政權建設,不取決于外在手段的激烈性,而取決于整套制度對社會的包容與整合作用,一般來說,越柔耐的制度越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參考文獻:
[1][2]T·H.馬歇爾,安東尼·吉登斯.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M].郭忠華,劉訓練,編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24-33.
(責任編輯/石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