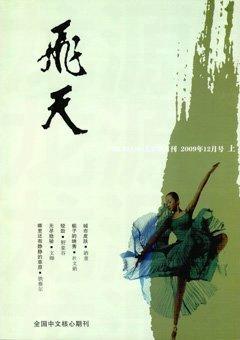當代文學與大眾文化市場
一、大眾文化市場背景下當代文學的特征
大眾文化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眾文化以港臺流行歌曲、通俗小說、電視劇為先導,拉開了它的序幕。這時,大眾文化在中國尚未形成較大的規模和氣候,并不足以構成對當時的文化格局的嚴峻挑戰。人們對這種文化的反應是持懷疑態度的。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大眾文化徹底擺脫了傳統的體制渠道,進入市場化的階段。它在中國的發展速度之快,范圍之廣,對文化精英極力營造的嚴肅正統的藝術格局沖擊之大,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僅形成了獨立的‘話語圈,而且隨著政治理性與單純啟蒙語境的轉換,在世俗化所設定的框架內與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合流了。”[2]文化界對大眾文化的態度由懷疑轉向認可,盡管有時是迫不得已和無可奈何的認可。這時,人們爭論的焦點是如何發展和引導大眾文化。20世紀90年代以后,大眾文化迅猛擴張,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登上霸主的寶座。伴隨著大眾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信息化、商業化、產業化,中國當代文學呈現出世俗化、喜劇化的特征。
20世紀末的文學世俗化已經成為當代文學中重要的文學和文化現象,是文學研究不可忽視的存在。文學世俗化體現了轉型期的種種價值矛盾,包含著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美學、心理學等層面的復雜內容。世俗化對文學的影響是相當廣泛的,涉及到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多種體裁領域,其中,又以小說、詩歌、散文領域最為明顯。在小說領域中,王朔的出現是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現象,他的消解崇高、解構權威、調侃神圣的“痞子文學”對后來的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王朔現象”。而且,王朔的出現還直接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從此,世俗化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學和文化現象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與王朔差不多同時期出現的新寫實小說也從烏托邦的幻滅中回到現實生活,投身于日常生活的書寫中。在這種世俗化潮流的影響下,一向以形式實驗著稱的先鋒作家也逐漸放棄了先鋒理想,在20世紀90年代完成了世俗化轉型。在20世紀80年代表精英文化的主流作家如王蒙、劉心武等在世俗化的潮流中也主動調整姿態,公開宣稱“躲避崇高”和“面向俗世”,表現出對世俗化的肯定,而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和出生于80年代的晚生代作家等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在詩歌領域,繼20世紀80年代朦朧詩之后,日常生活成為詩歌的重要表現對象。以日常生活書寫著稱的第三代詩人提出詩歌應與世俗生活相連接,之后出現的“下半身詩歌”等,則將目光直接對準感性身體。在散文領域,一方面是現代名家張愛玲、蘇青、梁實秋、林語堂等現代散文精品的結集出版,并迅速在市面上流通;另一方面是文學實踐中閑適散文、小女子散文等的大量出現。由此可以看出,文學世俗化已經成為市場經濟語境下非常重要的文學和文化現象,要真正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必須認真研究文學世俗化。
二、大眾文化市場背景下的文學生產機制變化
首先,《文化苦旅》的出世,得益于圖書出版體制的改革和大眾傳媒的迅猛發展。《文化苦旅》于1992年分別在大陸和臺灣出版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反響,贏得一片贊揚,大陸媒體紛紛關注并組織書評,海外重要報刊也紛紛加以評介,這對于《文化苦旅》造成洛陽紙貴的盛況功不可沒。當初部分篇目在《收獲》上連載時,雖也獲得了一定關注,但僅限于文壇內部。而《文化苦旅》出版后,大量的評論出現在報刊上,除了《中華讀書報》《文匯讀書周報》《文學報》《文藝報》《文論報》這些文學性比較強的報紙,以及《黃河》《美文》《當代作家評論》《中外作品研究》《中國圖書評論》等純文學或學術性刊物,還有《新民晚報》《新華每日電訊》《大眾日報》《深圳商報》《廣州日報》等這些非文學性卻很有影響力或者地方上發行量很大的報紙, 而且幾乎都有“范例”、“突破”“里程碑”、“高峰”、“標志”等贊譽極高之詞。
第二,《文化苦旅》在復雜的文化市場中,得益于既循“文以載道”而又“去政治化”的立場。《文化苦旅》的成功不僅是憑借其藝術成就,其藝術本身之外的東西也是起到相當作用的。市場經濟的逐步成熟使市場、物質的地位和力量變得空前突出,而文化、文學、知識分子在精神領域的地位則發生了動搖,失落感彌漫在知識分子的心間,痞子文化的出現,正是知識階層分化后一部分知識分子市俗化傾向的體現。而在《文化苦旅》中,那種啟蒙主義的、“文以載道”的姿態又回來了,可以說《文化苦旅》之“苦”正體現在對歷史、文化以及當代的憂患意識。
第三,文本迎合了現代都市文化的消費性特征。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的轉型使城市化進程加快,在城市生活中,勞動時間與閑暇時間有明確的分離,當人們獲得更多的閑暇時間后,在緊張、枯燥的勞動時間之外人們越來越有意識地追求輕松和娛樂。于是,與城市閑暇生活方式相應和的城市文化也隨之興起, 并以休閑為基本的旨趣。而文學在經歷了80年代的“黃金時代”,在90年代已經趨向邊緣化,但商品的本質要求它創造更廣大的市場,如果僅靠文學本身那是不可能創造這樣的奇跡的。在這種背景下,一些文學讀物就開始向文化讀物/休閑讀物轉化,以求更好地切合城市讀者的閱讀期待,從而成為人們度過閑暇時間的消費品。
三、大眾文化市場中作家的責任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世俗化、喜劇化、大眾化已經成為市場經濟語境下文學的重要發展趨勢。對待市場經濟語境下的文學的這一變化,采取極端的否定和極端的肯定態度都是不正確的,理性的做法應該是,既承認文學世俗化、喜劇化、大眾化的合理性和優長,更重視它的缺陷和弊端。
保持物質和精神的統一。由于中國長期以來一直處于物質匱乏的狀態,物質欲望一旦獲得生長的環境,就開始瘋狂地增長、膨脹,20世紀八九十年代剛剛擺脫了禁欲主義的人們又一頭扎進物質追逐的大潮中。追逐物質、占有物質成為許多人的生活目標和人生理想,人們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攫取物質財富,放棄尊嚴、丟掉精神、扔下理想,剛剛擺脫物質匱乏境況的人們又陷入物欲的深淵。隨著中國社會文化的轉型,在大眾文化市場環境中,作家逐漸從政治中心滑向社會邊緣,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都聲稱自己是在為市場寫作,將寫作作為謀生的工具,為追求市場效益,主動放棄精英立場,對世俗普遍采取認同的態度。不少作家在處理具體作品時,不是沉浸在物欲的滿足中,就是對現實擺出無可奈何的姿態,而對欲望的負面因素缺少應有的批判。當然,真實地書寫物化時代欲望的狂歡與身體的沉醉并沒有錯,但是如果完全放棄應有的價值立場,完全認同世俗的價值觀念,就會導致文學陷入庸俗化、粗鄙化的境地。在當前語境下,許多作家喪失了應有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作家對生活、對文學不再堅持批判和審視的立場,而是采取玩世不恭的態度。
為維護當代文學健康有序的發展作家有責任調整物欲與精神的種種失衡,維護精英文化,優化大眾文化,最終求得人文精神之現代價值重建的實質性收獲。我們相信,隨著大眾化的逐步深入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大眾化文學將會逐漸擺脫稚嫩、走向成熟。雖然文學大眾化還存在諸多缺點,但大多是發展當中的問題,我們期待大眾化文學為中國當代文學奉獻更多的精品。
【參考文獻】
[1]董之林.當代文學與“大眾文化市場”研討會側記[J].文學評論,2003(1).
[2]吳秀明.轉型時期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1.
[3]王曉明.面對新的文學生產機制[J].文藝理論研究,2003(2).
(作者簡介:索邦理,河池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