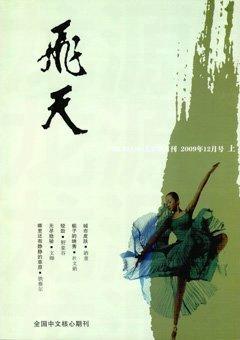對我國法制文學的思考
張 鵬
2009年有兩件事在法制文學發展史上頗具影響:一是我國第一屆中國法制文學原創作品大賽正式拉開帷幕;二是中國法制文學研究會在北京成立。這標志著中國當代法制文學創作的成熟、地位的提高。因此,重新認識、深入探索法制文學的本質和價值是現實和未來發展的迫切需求。
一、法制文學的概念
法制文學是以法治建設為題材,反映人們的法律生活,宣傳推廣法治觀念的文學。像日本的推理小說、蘇聯的反特小說、西方的偵探小說、中國的公案小說等自然屬于傳統法制文學的范疇,而托爾斯泰的《復活》、雨果的《悲慘世界》、司湯達的《紅與黑》、盧梭的《教育詩》、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等則堪稱世界法制文學的珍品。[1]中國法制文學源遠流長,成就顯著。它起源于先秦,成熟于明清,繁榮于當代。《詩經》里的《谷風》、漢樂府里的《平陵東》、《陌上桑》、唐詩中的《在獄詠蟬》、《杜陵叟》、元代的《竇娥冤》、明清時期的《包公案》、《拍案驚奇》等作品代表了中國古代法制文學的成果;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等作品反映了中國現代法制文學的面貌;《八十年代離婚案》、《便衣警察》等作品則體現著中國當代法制文學的主流。由此看來,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法制文學的概念內涵已經突破了單純的偵查、推理、斷案,而包容了政治、宗教、道德、人性等多方面綜合因素。托爾斯泰的長篇巨著《復活》,通過敘述瑪斯洛娃案件,深刻地批判了沙皇俄國的法律、法庭、監獄、官吏及整個專制腐朽的政治制度。雨果的代表作《悲慘世界》通過描繪冉·阿讓的悲慘生活史,反映了“貧窮使男子潦倒,饑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的社會現實,揭露了十九世紀前半期法國資本主義政治、道德、法律凌辱人民的本質。因此,法制文學既不能簡單地等同于通俗文學,更不能賤視為地攤文學,而是一種嚴肅文學、高雅文學,是人類進步文化、優秀文明的瑰寶。可見,深刻認識和正確評價“法制文學”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法制文學的誕生,雖然時興不久,但卻是歷史的必然,是時代的要求。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不斷深入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的法制文學也勃然興盛,迅猛發展。人們呼喚法治這種政治武器,呼喚法制文學這種精神食糧,于是專門的法制文學刊物相繼出臺,法制文學作品大量涌現,法制文學創作隊伍不斷壯大。迄今為止,專門的法制文學刊物就有《啄木鳥》、《藍盾》、《中國法制文學》等。而且《民主與法制》、《法律與生活》等綜合性法制刊物也經常登載法制文學作品,電影、電視、廣播、報紙也大量推出法制文學作品。事實證明,中國法制文學經過兩千多年來的曲折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大流派,在文學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
二、法制文學的特征
第一,法制文學取材的真實性。法制文學主要取材于公安、檢察、法院等執法、司法領域和平常百姓的婚姻糾葛、道德沖突、財產分割等法律生活領域。有的側重于反映政法干部秉公辦案,獻身于法,為民解難;有的側重于寫犯罪分子以身試法,禍國殃民、終落法網;有的側重表現法盲意識,害人害己、須警鐘長鳴;有的側重于刻畫民事糾紛、揭示道德、情理、法律之間的聯系。法制文學就是這樣借法治建設、法律生活這一側面來反映社會、反映人生。
第二,法制文學主旨的時代性。法制文學作品的思想意圖有很強的時代色彩。封建專制統治下的法制文學作品,往往將平民百姓的反抗當作犯罪行徑來寫,而將社會的安寧、揚善懲惡的愿望寄寓在統治者身上,頂多是將“清官”神化、理想化。即使象《包公案》里的包拯,也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這是時代的局限。資本主義世界的法制文學作品往往極力渲染兇殺、搶劫、淫亂、販毒等血腥與淫污情節,以便刺激感官,招徠讀者,甚至教唆犯罪。我國的法制文學毫無疑問是為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建設服務的,必須掌握描寫分寸,注意內容的健康與合法,保證社會效果。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作品應予取締。我國社會主義法制文學絕大多數作品是健康的,為完善社會主義法治,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繁榮社會主義文學藝術作出了積極貢獻。
第三,法制文學情節的曲折性。法制文學作品大都以其情節的曲折、驚險而引人入勝。往往有一個完整、新鮮、迷人的故事。事態由發端、發展到高潮與結局,常常變化多端,出人意料,刺激感很強。描寫偵探、審判、反特、犯罪、監獄等內容的作品就明顯地具有這種特點。譬如《尼羅河上的慘案》、《福爾摩斯探案全集》、《便衣警察》等,都是線索復雜、場面驚險、情節迂回而又較為合乎客觀真實與藝術真實的作品。從中可以悟出一個道理,真正優秀的法制文學作品,不僅要有吸引人的故事情節,而更重要的是要挖掘故事的本質內涵,表達出深刻而豐富的社會性、歷史性思想,決不可單純追求故事的離奇與驚險,而忽視社會哲理、人生哲理的探求。
第四,法制文學寫作手法的奇特性。法制文學作品,尤其是法制小說、法制劇本,在藝術手法方面,將高潮或結局提前,并且又不斷地制造一個又一個的懸念,然后通過回憶、推理,步步推進,層層剝開,直至真相大白或事態終結。同時,還處處運用穿插、閃回、迭映、巧合、點染,巧妙地使用場面描寫,氣氛渲染,從而增強藝術的感染力。線索安排時隱時現,結構布局往往跳躍多變。偵探小說、推理小說、偵探片劇本等大都特別講究這些藝術手法的綜合運用,以便創造出一種奇特瑰麗的藝術氛圍。即使象《悲慘世界》這樣的大作,也不忽略運用藝術手法精雕細刻,譬如冉·阿讓攀上阿利雍號戰艦的極高的橫杠去救一個水手而自己投入海中,冉·讓抱著珂賽特被警察追捕得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爬高墻進入修道院,而碰到的人恰恰是受過他恩惠的割風爺爺;又如冉·阿讓躺在棺材里被抬出修道院;他從街壘上救出馬里于斯,在巴黎的下水道中碰到的人恰恰是德納弟等等,都是巧合,都屬奇特。藝術手法的運用,不是為了駭人聽聞,不是為了慫人視聽,而是為了突出主題,塑造形象,深化思想。這是運用奇特藝術手法的一條基本原則。
三、法制文學在普法工作中的特殊意義
法制文學是描寫、反映法制生活領域的文學作品,與其他的文學形式一樣,法制文學從本質上說屬于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而且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審美意識形態,它是社會法制生活的審美反映。法制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質及其自身獨有的特點,使其不僅在法制宣傳教育上具有顯著的優勢,而且進一步延伸和拓展了法制宣傳的維度。
第一,優秀的法制文學作品在潛移默化中給人以深刻的啟迪和教益,發揮著突出的法制宣傳作用。文學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塑造鮮明生動的形象,就如別林斯基所說,文學作品的形象性,讀者深深地沉浸于文字所營造出的人物與景象之中,甚至進入如醉如癡的忘我狀態,同時,伴隨著好惡、喜怒、肯定與否定等情感活動,集中體現了文學以情動人的特征。而法制文學的意識形態屬性決定了文學的形象性并不排除理性與認識,它是將情感直覺引入到一個更高的理想境界。縱觀法制文學的發展歷史,其形象化地反映社會生活,宣傳法制觀念,確實功不可沒。法制文學作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 ,其本身的目的是無功利的,在這一點上它不同于法學宣傳材料和法律文書要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所需遵守的法律條文,法制文學以再現現實的法律生活為己任,它不是簡單地敘述事實過程,而是調動各種文學手段,塑造人物形象,設置情節沖突,描繪各種場景,展現一幅生動可感的現實生活圖景,以滿足讀者的審美需求。人們閱讀法制文學作品也往往是從非功利和審美開始的,他們并不需求直接的實際利益的滿足。比如:我們閱讀《十面埋伏》是出于對腐敗的深惡痛絕,是被小說中錯綜復雜、驚心動魄的曲折案情所吸引,而并非抱持學習法制知識的目的。我們就可以在一種輕松愉快的心境下進入閱讀狀態,摒棄了學習法制條文時的枯燥、惰怠心理,從而獲得理想的接受效果。另一方面,法制文學審美性的背后又確確實實存在著功利性,文學的審美始終與意識形態交織在一起,后者所包含的功利、概念、判斷、認識等性質時時在影響著法制文學的無功利性質 ,無論是作家、作品還是讀者在文學活動中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深刻的社會功利性。中國文學歷來有“文以載道”的傳統在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中作家的政治傾向、法制觀念、思想認識、道德信念、價值標準等都自覺不自覺地體現于作品中 ,而讀者的人生閱歷、知識背景、閱讀期待也使閱讀活動隱含著功利因素。
第二,法制文學獨特的取材與表現手法使其展現出與眾不同的審美趨向,并且因此而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相對于一般文學樣式來說,法制文學所擁有的讀者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層次也較寬泛,這主要是由它取材的著眼點所決定的。法制文學廣泛取材于涉及法律規范的各種社會領域的現實生活,反映的是人與人之間、人與國家之間、人與法之間的規范化關系和這種關系在成為一種沖突狀態時所導致的消極社會后果及其法律規范化解決形式和解決效果,大多數屬于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緊扣時代脈搏,具有較強的社會性。法制文學作品不是追求和編造離奇的故事,而是通過涉及法制的一系列事件來揭示出社會扶正祛邪、揚善懲惡的思想主旨,著力描寫人物的命運、內心與性格,在揭露社會陰暗面,暴露丑的同時更展示正面人物的心靈美與道德美,弘揚社會正義,賦予人物和事件以鮮明的現代法制意識,符合人們對真、善、美的向往與追求。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不斷躍進和大眾文化的興起,文學消費日益成為人們生活必需的精神養料。而法制文學由于其取材的特點,使作品整體上呈現出情節緊張、過程曲折、節奏迅速、動作性強懸念迭起和最終釋疑的特點,這些特點恰恰滿足了頗為龐大的讀者群體的某種閱讀需求,為社會主義法律的廣泛普及奠定了基礎。
第三,法制文學的道德教化作用使其遠比法律條文本身具有更為廣泛和形象的普法意義。道德是維持人與人、人與社會正常關系的規范體系。法律和道德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都是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在根本目的和價值取向上是一致的,它們互相聯系、相互作用、互為補充。法制文學在進行道德教化從而強化人們法律意識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法制文學因其涉及領域的獨特性,同時包容了道德范疇的內容。法制文學所贊美的,既為社會主義道德所崇尚,也為社會主義法律所肯定;法制文學所鞭笞的既為社會主義道德所不齒,也為社會主義法律所否定。[2]因而,法制文學可以強化人們的道德觀念,能夠凈化人們的精神世界,在傳播過程中對人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有著極大的導向作用,而與此同時,人們的法律意識也在無形中得到了增強。
四、我國法制文學的創作前景
回顧中國當代法制文學的創作歷史,在充分肯定成績主流的同時,也不難得出一個明顯的結論:即法制文學的創作方向應著重注意解決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必須注意主題的深化。法制文學作品不能只做表面文章,不能一味追求故事情節的離奇怪誕,不能為寫故事而寫故事,應該讓故事與社會、與時代緊密結合起來,即開掘出故事中蘊含的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時代精神,并且還要注意開掘人物的內心世界,使形象具有較大的概括力。
第二,必須注意手法的創新。法制文學的寫作方法應該有所講究,要多樣化,不要公式化。作品的結構也不能老是搞“發案——偵查——破案——審判”的程式化,要力求有所突破,有所創新。
第三,必須注意典型形象的塑造。法制文學創作的重點應落在典型形象的塑造方面,所寫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不能搞“臉譜化”、概念化,若“千人一面”就太乏味。目前,我國文藝舞臺上似乎還缺乏政法工作者的新時代典型形象,這是值得探索的課題。
第四,必須注意內容的社會效果。法制文學作品讀者面很廣,產生的社會效果很強烈,必須注意思想內容的積極性、有益性。
概而言之,我國法制文學的發展方向應該是努力克服這四大通病,毫無疑問,深化主題、革新手法、塑造典型、提高效果是我國法制文學的輝煌前景。只有這樣,才能按照胡錦濤同志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使法制文學成長為優秀的、先進的文學之花、文化之花、文明之花。
【參考文獻】
[1]冀冰.法制文學初探[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2):81-83.
[2]吳坤炳.論法制文學[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3,(3):61-67.
(作者:張鵬,第三軍醫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