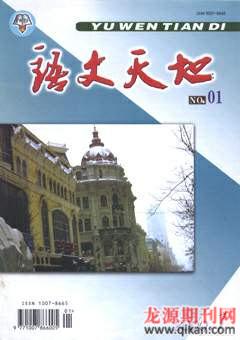卡夫卡和吳承恩一樣高明
徐逢春
吳祖湘先生在《我國古代小說的發(fā)展及其規(guī)律》一文中指出:“任何神話都產(chǎn)生于現(xiàn)實(shí),由于現(xiàn)實(shí)問題的觸發(fā)而幻想出來的。……吳承恩在他的志怪小說《禹鼎志》序中說:‘雖然吾書名為志怪,蓋不專明鬼,時(shí)紀(jì)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正是因?yàn)椤段饔斡洝愤@樣立足于現(xiàn)實(shí),才引起當(dāng)時(shí)的轟動(dòng)并得到廣泛流傳。”無獨(dú)有偶,2004年2月21日《人民日?qǐng)?bào)·<西游記>隨想》一文也說:“任何文學(xué)作品都是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反映。其對(duì)現(xiàn)實(shí)腐朽和邪惡的揭露和批判,因作者的才學(xué)和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領(lǐng)悟程度不同,也因?qū)懽魇址ǖ牟煌陀辛孙@與隱、曲與直、雅與俗之別。吳承恩是用隱曲的手法,用引人入勝的離奇怪幻而又荒誕的故事,引領(lǐng)讀者漸入他那被妖魔鬼怪、仙佛神道、琪花瑤草籠罩著的現(xiàn)實(shí)批判的思想佳境。”
這些話,可以作為我們解讀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見人教版高中五冊(cè)《語文》)的一把鑰匙。小說寫主人公格里高爾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看似荒誕至極,然而只要我們把這荒誕的外衣——記敘、描寫、議論格里高爾似甲蟲的文字剝?nèi)ィ湍芊浅G宄乜吹礁窭锔郀栕鳛楫?dāng)時(shí)的一個(gè)有家庭的人的生存狀態(tài)及其性格的方方面面。
小說共有三部分,這里以第一部分為例。剝?nèi)ネ庖拢尸F(xiàn)在我們面前的格里高爾,是一個(gè)卑微的“旅行推銷員”,他“長年累月到處奔波”,要“這么早起床”,“因?yàn)榛疖囄妩c(diǎn)鐘開”;否則“立刻就會(huì)被解雇”。“他是老板的一條走狗”,不能請(qǐng)病假。頂頭上司秘書主任為他沒有上班找上門來,后來因“腳跟灼傷”“大聲‘哦了一聲”,他就嚇得“向后退去”,母親也“倒在地上”,父親“雙手捂著眼睛哭了起來”。格里高爾“馬上”向秘書主任道歉,說自己“并不是冥頑不化”,“不出差我就沒法活”,請(qǐng)秘書主任“如實(shí)報(bào)告”給“經(jīng)理先生”,“在公司幫我美言兩句”。可是秘書主任對(duì)格里高爾的請(qǐng)求置若罔聞,笑著要離去。格里高爾只得千方百計(jì)“挽留、安慰、說服”秘書主任,以“博得他的好感”,因?yàn)椤案窭锔郀柡退患胰说那巴救翟谶@上面”。為此,格里高爾甚至想讓他的妹妹出面去“駕馭”愛好女人的秘書主任。不料這時(shí)發(fā)生了不幸:格里高爾在樓道上“跌倒下來”。母親見了大喊“救命!”,“魂不守舍”地“撲進(jìn)向她迎面奔來的父親的懷里”。然而格里高爾反而“高興”,覺得“最終擺脫一切苦難的時(shí)刻已經(jīng)為期不遠(yuǎn)了”。為了“盡快追上”秘書主任,格里高爾無暇顧及他的父母,但是“秘書主任似乎有所覺察,他一個(gè)大步跳下好幾級(jí)樓梯,轉(zhuǎn)眼不見了”,“這一逃跑似乎使迄今一直比較鎮(zhèn)靜的父親也慌亂起來”,他“要把格里高爾趕到他的房間里去”,同時(shí)“只是一個(gè)勁兒拼命跺腳”;為了觀察秘書主任的去向,“母親不顧天氣涼爽打開了一扇窗戶,身子探在了窗外,她把手伸到窗外面捂住了自己的臉”。結(jié)果引來了“一陣強(qiáng)勁的穿堂風(fēng)”,把“窗簾掀起來”,“桌子上的報(bào)紙”被“吹在地面上翻滾”。父親見了“簡直發(fā)了狂”,“大聲嚷嚷要把格里高爾往前趕”,不顧格里高爾處境尷尬,“從后面使勁推了他一把”,使“他當(dāng)即血流如注,遠(yuǎn)遠(yuǎn)跌進(jìn)了自己的房間里”。
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這些情節(jié),哪里還有什么荒誕呢?有的都是生活的真實(shí)。公司老板居高把持,嚴(yán)密統(tǒng)治;秘書主任時(shí)刻監(jiān)督,冷漠無情;雇員迫于生計(jì)勞碌奔波,雖安分守紀(jì)但厄運(yùn)不斷,終日在惶恐、痛苦、憂郁中煎熬。聯(lián)系小說的寫作發(fā)表年代,我們就能深刻認(rèn)識(shí)到這種真實(shí)的必然性。
《變形記》寫于1912年,發(fā)表于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的第二年。當(dāng)時(shí)的奧地利是什么樣子呢?作為高教文科教材的《世界近代史》有這樣一段話:“廣大群眾生活上日益貧困,政治上也被剝奪了自由。各交戰(zhàn)國家中,除了上千萬的勞動(dòng)人民被征入伍,到前線充當(dāng)炮灰外,其他群眾,包括老年人、婦女、兒童,都被迫從事各種繁重的勞動(dòng),勞動(dòng)時(shí)間長達(dá)十二至十六個(gè)小時(shí)。勞動(dòng)人民喪失了起碼的政治權(quán)利,罷工、集會(huì)、遷居的自由均被剝奪,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后方,都變成了囚禁勞動(dòng)人民的軍事苦工監(jiān)獄。”由此可以想見弱勢家庭的處境該會(huì)多么艱難。卡夫卡筆下的格里高爾一家為求生而掙扎的情態(tài),不就是當(dāng)時(shí)弱勢家庭生存狀況的寫照嗎?卡夫卡自己曾說:“不斷運(yùn)動(dòng)的生活紐帶把我們拖到某個(gè)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們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們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外國文學(xué)參考資料》,地質(zhì)出版社出版)。這就是說,在小說家看來,當(dāng)時(shí)的普通人群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yùn),隨時(shí)都可能異化為“物”。就是在這種“異化”的思想指導(dǎo)下,卡夫卡讓格里高爾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只可憐的甲蟲,借藝術(shù)手段形象地表現(xiàn)出他的社會(huì)見解:現(xiàn)實(shí)嚴(yán)酷,普通人群生存艱難,處在隨時(shí)都可能被統(tǒng)治者宰割的悲慘境地。這種現(xiàn)實(shí)批判還見諸他的其他作品中,例如“他的長篇小說《審判》(1914)對(duì)奧匈帝國時(shí)期人民生命、權(quán)利的毫無保障以及官僚制度的腐朽作了深刻的暴露”(2000年4月19日《教師報(bào)·表現(xiàn)主義文學(xué)》一文)。
《<西游記>隨想》一文還說:“《西游記》第九十八回,寫唐僧師徒到西天雷音寺大雄寶殿見如來佛祖,佛祖見面的第一句話就很厲害:‘你那東土乃南贍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廣人稠,多貪多殺,多淫多誑:……不忠不孝,不義不仁,瞞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殺牲。造下無邊之孽,罪盈惡滿,致有地獄之災(zāi)……雖有孔丘在彼立下仁義禮智之教,帝王相繼,治有徒流絞斬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縱無忌之輩何耶!這可以看作是吳承恩對(duì)他生活的那個(gè)時(shí)代的揭露和聲討。這樣的話,要不是通過佛祖之口說出,要不是在那個(gè)特定的場景說出,他一定要倒霉的。但他畢竟是才子,把明王朝、把皇帝老兒痛快地罵了一回,還博得了一片喝彩,這是吳承恩的高明之處。”《20世紀(jì)歐美文學(xué)史》(張玉書主編)指出:卡夫卡的作品曾“遭到納粹的明令查禁”。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小說家為什么給格里高爾披上荒誕的外衣——避免陷入文字獄。因此,我們可以講,卡夫卡和吳承恩一樣高明。
湖北省咸寧鄂南市高級(jí)中學(xué)(43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