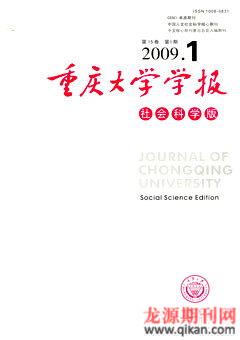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的典型形態論
黎躍進
摘要:20世紀初至20世紀60年代是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發展最為成熟和典型的階段。東方各民族文學都產生了一批在文學史上占據顯著地位的民族主義詩人、作家和理論家,他們的創作和理論活動,充分展現了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共同原則和特征:反對殖民統治,高揚民族意識,要求民族獨立的主題思想;功利性、現實性的審美追求;民族傳統的弘揚與民族靈魂的呼喚。
關鍵詞:東方;民族主義;民族意識;審美追求
中圖分類號:I109.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8-5831(2009)01-0121-06
20世紀初至20世紀60年代是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發展最為成熟和典型的階段。兩次世界大戰和殖民體系瓦解,東方民族解放運動此起彼伏,東方各具特色的民族主義思想體系形成。這期間東方各民族在完成傳統文學向新的民族文學轉型的過程中,民族主義文學思潮達到了自覺性、普遍性、實踐性和統一性的程度,各國文學都產生了一批在文學史上占據顯著地位的民族主義作家、詩人和理論家,他們的創作和理論活動,充分展現了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共同原則和特征,是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的典型形態。
一、反對殖民統治,高揚民族意識。要求民族獨立的主題思想
西方的殖民統治給東方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這成為東方民族要求政治獨立、自由平等的邏輯起點。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全面展示了殖民統治帶給東方的動蕩、戰亂、屈辱和貧困。東方現代民族主義作家對殖民統治者帶給民族的種種災難和痛苦有生動具體的表現。
印度尼西亞詩人魯斯丹·埃芬迪在題為《祖國》的詩中寫道:“啊,我的祖國,苦難無比/哀嘆和呼喊著命運的悲凄/低頭彎腰雙手擎著恥辱/任人踐踏讓苦難折磨自己/汗水灑滿地,鮮血流成河/啊,我的祖國,苦難無比。”
印度英語作家安納德1937年的小說《兩葉一芽》以阿薩密一個茶葉種植園為英國殖民統治的縮影,以契約勞工甘鼓一家的遭遇表現印度農民的悲慘命運。小說真實生動地描述了英國殖民統治對印度民眾的殘酷壓迫和剝削。甘鼓,這個勤勞淳樸、篤信宗教、忍辱負重、寬以待人的印度農民,就是象征意義上的殖民統治下的印度。
喀麥隆的著名作家費丁南,奧約諾(1929-)的作品,描寫了黑人遭受的專橫殘暴統治。長篇小說《童仆的一生》(1956),用自傳體和日記的形式,敘述主人公敦吉的經歷和體驗,從一個黑人奴仆的視角,撩開殖民者文明、道德、善良的面紗,表現非洲人民的苦難與民族意識的覺醒。
伊克巴爾的長詩《痛苦的畫卷》(1904)以悲憤的筆致,真實地展示了他耳聞目睹殖民主義對印度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描繪了當時社會滿目瘡痍,農村凋敝、手工業破產,災荒不斷的悲慘境地。
從整體看,東方現代作家對殖民統治罪惡的揭露,主要不是在生活事像的描寫上,更多的是從政治獨立和精神自由方面加以表達。
阿爾達夫·侯賽因·哈利有一首《英國人的自由和印度的被奴役》:“據說只要呼吸一下英國的空氣,奴隸們就可以獲得自由,/這就是英國的奇跡。/只要一踏上英國的國土/奴隸們的腳鐐就會自動斷裂脫離。/如果說英國是個奇妙的煉金術士,/那印度也毫不遜色不比它低。/自由的人到了這里馬上變得不自由,/一接觸這里的空氣,就會立刻變成奴隸。”詩作將英國與印度鮮明對比,揭示英國殖民主義對印度的奴役。
印尼作家馬爾戈的《放牛娃》以象征手法,從放牛娃的視角表達反抗荷蘭殖民統治的決心,放牛娃祖輩相傳的牧地被一“女神”率領的一群猛獸占領,放牛娃準備奪回牧地,“女神”施以小恩小惠從中阻擾,放牛娃清楚殖民主義的本質:“你的承諾全是謊言/把我們的全體民族/推進了苦難的深淵/你們卻有無盡財源。”
在現代東方詩人看來,殖民統治真正的危害,還不是殖民地人們生活的貧困和戰爭的創傷之類,而是對殖民地人們的精神奴役,它使其喪失斗志和反抗的能力,成為“籠中鳥”郁悶而死。
印度烏爾都語詩人杰格伯斯德寫道:“周圍彌漫著一片不滿的氣氛,/只聽到整個花園如訴如泣。/窩里的鳥兒如今被關在籠中,/獨立變成了一股香氣消失在花園里。/在這樣的環境中花兒怎能開放?/花兒笑不出聲,充滿了憂郁。”對殖民統治精神奴役的表現,都是對外來者侵略本性的揭露,都是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看取西方列強的未來,以“同仇敵愾”的書寫,喚起同胞的民族意識。
怎樣才能獲得民族的獨立?東方現代民族主義詩人和作家在文學世界中進行民族解放道路的種種探討,在他們看來,團結奮斗、保持尊嚴、不怕犧牲、堅定勝利的信心是民族獨立的基本保障。
(一)團結奮斗
“‘民族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民族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相同”。從早期的血緣宗族,到基于血緣的部落聯盟,再到一定地理單元的利益共同體,發展到具有共同文化傳統的社會群體。“民族”的范圍、規模不斷擴大。東方民族的構成非常復雜。由不同的種族、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的宗教信仰所構成的文化民族與政治民族彼此聯系,又彼此沖突。面對西方殖民統治,這些矛盾和沖突是民族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內部矛盾和沖突。東方現代民族主義作家和詩人敏銳地意識到:大敵當前,只有放棄內部沖突,大家團結一致、齊心協力,才能趕走侵略者;只有建立起獨立統一的民族國家,才能尋求建設和發展,才有與西方平等對話的資本。
伊克巴爾早期的愛國主義詩作認為印度各民族之間的團結,是國家統一和振興的重要條件。他早期的詩作深刻地表達了在殖民統治下人民的心聲,充滿了印度穆斯林傳統的印度情感和自豪感以及對伊斯蘭過去歷史功績的頌揚。《喜馬拉雅山》這首祖國頌詩,便體現了詩人的這種情感。他主張建立統一的印度民族國家,把“印度斯坦”當作印度人的祖國,這在他的長詩《印度之歌》中得到體現。埃及詩人邵基在1927年的一首詩中號召整個阿拉伯世界聯合團結:“真主使我們同病相憐,/同樣的遭遇,同樣的悲慘。/每當伊拉克受傷發出呻吟,/東邊的阿曼也同樣會有痛感。/我們與你們都身戴鎖鏈,/如同雄獅掙扎在鐵籠間。/我們在這樣的世界上同樣貧困,/又同樣地熱愛自己的家園……”
1962年亞非作家會議召開,大會形成的《總決議》中有這樣的表述:“人民的覺醒和警惕加強了我們的團結——兩大洲的人民正在重新團結起來。殖民地成為獨立國家這個本質的變化,民族解放運動的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在各方面的擴大和鞏固,這一切都是力量對比有利于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
(二)保持尊嚴
尊嚴,是人之為人的根本,也是民族之為民族的根本。面對外辱,只有民族成員都以民族尊嚴為首務,為民族尊嚴而奮斗,才有獨立解放的希望。相反,如果民族成員都甘心屈辱,茍且偷安,何來獨立與解放?
印度烏爾都語詩人穆罕默德·侯賽因·阿扎德
深感在印度現實中,當國家面臨生死攸關的嚴峻時刻卻缺少為民族尊嚴而奮斗的英雄,于是,在他195行的長詩《愛國者》中,他滿懷激情地頌揚了印度歷史上為祖國尊嚴而犧牲的英雄:“喂,愛國的太陽,你在哪里?/為什么如今見不到你?/沒有你,祖國家家戶戶一片漆黑,/沒有你的光輝,我們心中的積郁重新泛起。”摩洛哥詩人阿卜杜拉·卡嫩也表達了同樣的憂慮:“異鄉人不是遠離故土,/而在自己的祖國卻受虐待。/異鄉人會有消愁解悶時,/我這樣的人卻無法忘掉悲哀。/我憂心忡忡,卻得不到幫助,/于是終身都是憂傷滿懷。/我為這個國家哭泣。這里愚昧橫行,/一伙笨蛋驅趕著人民,任意胡來……”印度尼西尼詩人馬爾戈在《獨立自由》中就是將“人格尊嚴”與獨立自由相提并論:“我等追求的獨立自由/是我民族的人格尊嚴/讓我的民族也能擁有/與其他民族同樣體面”。
為了民族尊嚴,即使面對敵人的屠刀與監禁,也能從容鎮定,慷慨高歌。也門詩人、民族主義政治家祖白里有一首《出獄》:“我們昂首挺胸走出牢門,/如同一群雄獅沖出莽林。/我們在槍間刀鋒上走過,/穿過鬼門關,面對過死神。/我們不愿茍且偷生,受人蹂躪/暴君的威嚇、壓迫豈能容忍?!/天塌地陷,我們不怕/千難萬險難不住我們。/我們要讓我們的民族知道,/我們愿赴湯蹈火為他獻身。/我們若是取得了順利/說明困難嚇不倒勇敢的人;/我們若是犧牲了,/則會面不改色,笑傲死神……”
(三)不怕犧牲
民族解放是血與火的洗禮,難免犧牲。但這是以小我的犧牲換取整個民族的新生,是雖死猶生的大業。
焦希·莫利哈巴迪被稱為“爭取印巴次大陸解放的旗手”。他在詩集《火焰與露珠》中有一首詩:“歡笑吧!亞洲,金光閃閃的大地,/印度覺醒的時刻已經來到。/歡樂吧!印度,這人間的樂園。/流血在眼前,敵人劍出鞘。/鐵石心腸的瘋子準備血染你的旗幟,/印度教徒穆斯林要保衛你的每一寸土地。/祖國人民的希望之花含苞欲放,/兩大民族的鮮血將合流于祖國大地。”詩作洋溢著為祖國不惜流血犧牲的豪情。
緬甸作家貌廷的長篇小說《鄂巴》(1946)在抗日戰爭的背景中刻畫了愛國民族英雄德欽謬紐,面對敵人的屠殺,滿懷“為祖國而獻身”的氣概,視死如歸,昂首挺胸,在響徹山谷的“緬甸萬歲”的呼喊中英勇就義。
馬格里布地區復興運動先驅、突尼斯民族主義詩人塔希爾·哈達德(1899-1935年)一首題為《祖國》的詩作,始終寫道:“祖國,我為你愿將生命、財產獻上,/使我們一起擺脫凌辱,獲得解放。/我愿為你犧牲,我的祖國,我的故鄉,/你是我的驕傲,你是我的希望。”
東方現代民族主義詩人和作家之所以能為民族、為祖國不怕流血犧牲,是因為他們滿懷祖國自由獨立的理想和信念。在祖國自由獨立的理想和信念中展開想象的翅膀,描繪未來前景,激勵人民斗志。烏爾都語詩人恰克伯斯特(1882-1926年)的詩集《祖國的黎明》呼喚祖國獨立自由,抒發為祖國捐軀的激情。奧利薩語的高伯本圖·達斯(1877-1928年)在獄中寫了《獄中詩抄》、《囚徒的獨自》和《印度母親》等詩集,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情緒、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情懷和為國獻身的激情。巴拉蒂有《向祖國致敬》、《祖國》、《我的母親》、《婆羅多國之歌》、《自由的渴望》和《歌唱自由之偉大》等。在《向祖國致敬》中,巴拉蒂把祖國比作母親,他說:“不管我們是勝利、失敗或者死亡'/我們始終團結一致,/發出一個聲音:/向母親致敬!”
(四)堅定勝利的信心
東方現代民族主義作家、詩人以極大的熱情憧憬民族獨立的未來,描繪一個嶄新的民族自我。被稱為“阿爾及利亞詩王”的穆罕默德·伊德以極大的熱情抒寫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反帝愛國斗爭。他在題為《解放軍之歌》的詩中寫道:“我們解放大軍是戰斗的力量/南征北戰,好像猛虎雄獅一樣。/戰鼓咚咚,軍號吹響,/我們分歧,使祖國大地震蕩。/我們將高山當作堡壘,/我們的贊歌在山中回響。/廣播把我們勝利的消息告訴人們,/捷報頻傳。喜訊飛向四方。/我們勇敢,我們頑強,我們曾樹立起多少光輝的榜樣。/我們像熊熊烈火奔赴戰場/千難萬險都不放在心上。/我們轉動戰磨,取得勝利,/嚴懲敵人,讓他們把苦頭嘗。/我們要把殖民主義徹底埋葬,/讓我們的人民掙脫枷鎖,求得解放。”詩作洋溢著必勝的豪情。蘇丹詩人法圖里有一首《非洲之歌》:“啊,我在東方各地的兄弟,/啊,我在世界各地的兄弟,/是我在呼喚你,你可認識我?/啊,我的兄弟,我的患難知己!/我已經扯破了黑暗的尸衣,/我已經摧毀了軟弱的墻壁;/我不再是講述腐朽的基地,/我不再是哭泣垃圾的小溪;/我不再是自己鎖鏈的奴隸'/我不再崇拜偶像和衰老的過去;/不怕死亡,我將永遠長存,/不受時間所限,我將永遠是自由之軀……”
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從各個層面表達了反帝反殖民、追求民族獨立的主題。
二、功用性、現實性的審美追求
文學思潮是特定時代精神在文學領域的群體性反映。但一個時代的作家、文學理論家對時代精神是否具有自覺的意識,是文學思潮是否形成的一個標志。在民族解放運動此起彼伏的20世紀前60年,東方民族主義作家自覺地追求文學的功用性和現實性,具有明確的目的意識,反對“為藝術而藝術”,主張真實地表現現實中普通人民的情感和生活。
(一)服務于民族獨立的文學目的論
在民族解放運動轟轟烈烈展開的歲月里,不少作家以各種方式積極參與運動,文學成為他們手中的武器,因而他們的創作傾向明顯。緬甸作家、文學批評家吳登佩敏在《吳龍傳》的序言中說:“當淪為奴隸的緬甸人民產生民族意識,要求獨立的時候,當貧苦的農民要求生存權利的時候,一個不傾向于任何一方的人,會全力以赴支持淪為奴隸的緬甸人民嗎?會積極支持貧苦農民嗎?”作為一個“進步作家”,就應該為“民族的獨立,貧苦人的幸福”而寫作。埃及作家阿卜杜·拉赫曼·哈米西(1920-1987年)在一篇《文學為人民》的文章中寫道:“人民所要讀的作家是逃脫出隱居禪房,探求人生經歷的人;是描繪民族斗爭維護人民及其自由的人;是隨時準備為大家的生存犧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而損害公眾利益的人。人民要讀的文學是與人們密切相關的。它啟迪人們為幸福的未來而斗爭,它反對人剝削人,它知道憎惡那些壓迫者,并能煽動起被壓迫者的仇恨。人民要讀的文學是時代的畫卷,是反對暴虐斗爭的鏡子,并激勵人們反對帝國主義與剝削制度的斗志。”反帝反殖,維護民族和人民的獨立自由是民族主義文學追求的目標。
印度現代文壇巨擘普列姆昌德也主張目的明確的文學論。1930年他在《大印度》刊載文章表明:“我的意愿是非常有限的,現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們在獨立斗爭中取得勝利。我不追求金錢,因為不
追求名譽,有吃的就行,我不渴望小轎車和別墅。無疑,我一定想留下幾部第一流的作品,但是其目的還是為了獨立。”普列姆昌德的意識很明確,希望創作幾部傳世之作,但根本目的“還是為了獨立”。當然,這種獨立的含義是多方面的,蘇丹詩人穆罕默德·艾哈邁德·邁哈朱布曾說:“這是我們的理想:維護我們的伊斯蘭教,掌握我們阿拉伯的遺產,同時對廣闊的思想天地采取完全寬容的態度,要有宏圖大志去研究、學習別人的文化。這一切都是為了我們民族文學的復興,激發我們的愛國意識,直至形成一個政治運動,實現我們政治、社會、思想的獨立。”
正是將文學當作反帝反殖的武器,民族主義作家要求創作出催人奮發、昂揚向上、堅強有力的文學,而不是傷感絕望、軟弱無力、哀愁呻吟的文學。旅美派作家、文學批評家哈雷尼斯倡導“行動文學”和“強力文學”,反對“哭泣的文學”和“軟弱的文學”。他說:“我們,說真的,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最愛哭泣和嚎啕的民族,我們好像是用淚水和悲哀造成的,好像是痛苦的氣息吹成的……這是一種比我們身上的任何病都普遍的疾病,對我們民族的完全幸福具有最大的危險。它是最丑惡的流行病,因為他對思想和心靈起著黑暗統治和專職法律所起不了的作用。”他甚至認為,“哭泣文學”是殖民主義的一個方面軍,是為統治者服務的。他號召把祖國、民族從哭泣文學中拯救出來,把哭泣文學變換為民族主義需要的“強力文學”。印度的烏爾都語文學批評家阿扎德也認為:詩人可以改變民族和國家的命運。他尤其談到戰爭題材的詩作,如戰斗中的鼓動詩和戰斗歌曲,它們使戰士心中產生一種新的激情和熱情,從而增強他們的決心和勇氣,并由此改變戰場的形勢。如此對文學功用的強調,也許有些夸張或偏頗,但卻體現了東方現代民族主義作家的文學觀念。
(二)文學必須表達時代的脈搏和民眾的現實愿望
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是在民族解放的時代要求中動員民眾、鼓動民眾的文學,它以普通民眾為讀者對象。埃及現代著名的文學評論家薩拉邁·穆薩(1888-1958年)于1914年創辦《未來》雜志,參與十多種報刊雜志的編輯工作,積極參加文學論爭,分別在1926年、1927年、1930年寫下了《薩拉邁·穆薩文選》、《今天與明天》、《論生活與文學》等文論著作。在論著中就埃及文學的現代轉型提出了許多見解和看法,他強調文學與社會現實的聯系,認為阿拉伯古代文學多為“國王的文學”和“消遣的文學”,現代文學則應是千百萬人的文學、人民的文學、斗爭的文學。應該建立反對殖民主義壓迫、用人民語言書寫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文學。他指出:“人民是一切,人民是始與終。”文學家對此是負有責任的,在他們所寫的一切作品中都應體現這一責任。他提出埃及文學應建立在“意義和目標”之上,而不是像阿拉伯人過去那樣,建立在“詞藻”之上。他還認為:“文學的目標是人道主義,而不是藝術美。人道主義比美更具有永恒性。文學是從整體上,而不是從局部去觀照人類的藝術。”他的一些觀點和主張,在20世紀上半葉,曾引起埃及乃至阿拉伯思想文化界的激烈爭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敘利亞詩人舍菲格·杰卜里說:“詩人必須同大眾的情感一致,這種情感就是民族主義感情。”他還說:“無疑,我專門寫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詩篇,使我未能涉足其他的天地。但我是適應環境,服從最大的題旨的。我覺得我必須照顧全國的感情。如果說詩人是民族的代言人,那我就是試圖用一切機會表達這個民族的感情。”巴勒斯坦詩人邁哈穆德·德爾維什強調詩作于人民的關系:“如果我們的詩歌,/不能像明燈高漲照,/不能傳遍千家萬戶,/讓人人知曉,/那它就不是詩,只是無聲無息/既沒有顏色,也沒有味道。//如果我們的詩歌/普通百姓根本不懂,/那就應當把它撕碎/讓風吹得干干凈凈,/然后閉緊嘴巴,/別再作聲!”
在民族運動高漲的時期,印度的民族主義作家都強調創作與時代和人民大眾的聯系。泰戈爾號召作家“不要與周圍世界隔絕”。烏爾都語作家伊克巴爾認為“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就在于必須反映生活”,號召作家“熟悉民族的脈搏”。孟加拉語作家伊斯拉姆認為,文學應成為“打動億萬人民之心的人民文學”。文學應為祖國獨立事業服務,發出“世上受壓迫靈魂的痛苦吶喊”。泰米爾語作家巴拉蒂(1882-1921年)主張,文學應給“被壓迫人民以新生活的信息”。在文學是工具、是吶喊、是號角的藝術主張之下,許多文學家自覺地以文學服務于當時的民族解放斗爭,掀起了空前未有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
(三)投身現實,反對“為藝術而藝術”
參加第二次亞非作家會議的一位喀麥隆代表說:“今天,殖民制度在人民武裝的痛擊下,正在傾塌之中,帝國主義的惡魔正在血泊里掙扎顫抖,哪一個亞非作家能夠接受‘為藝術而藝術或是‘文學應該和政治分家的理論?尤其是在今天,任何一個接受‘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家,事實上就是出賣自己的才能,做了殺害我們的人民和文化的同謀罪犯!”現在看來,這樣的表述有些太濃的火藥味,但確實真實地說出了當時東方民族主義作家的心聲。
不僅民族解放的現實要求作家、詩人關注現實,積極投身民族運動的實際斗爭,有些文學批評家還結合文學史上的事例來論證文學與現實的密切聯系。烏爾都語文學評論家毛拉那·希伯利·努瑪尼在《波斯詩歌》中認為:“寫出來的詩歌如果只是為了欣賞,那么可以運用夸張的手段。但是作為一種可以對民族的命運產生影響的有力量的詩,可以使國家發生巨變。可以喚起阿拉伯民族覺醒的詩,如果不是正確地反映了客觀現實的話,那它將發揮不了任何作用。在伊斯蘭教產生以前的蒙昧時期,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寫了一首詩,就可以在整個阿拉伯世界揚名。與此相反,伊朗的許多詩人寫了無數頌揚帝王將相的頌詩,他們仍然名不見經傳,原因在于伊斯蘭教產生以前的蒙昧時期,詩歌是真實的,所以它具有影響力,伊朗詩人只追求文字的華麗,這種詩只能有一絲的娛樂效果。至于其他,那就根本不值得一談。”換句話說,只有真實地表現現實,詩人的情感與民眾的情感有著內在的一致,詩作才能擁有生命力。遠離現實的歌功頌德之作,即使有艷麗華美的文字,也價值不大。而喚起民族覺醒、促進國家變革的民族主義文學,必須是真實的、現實的創作,而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字游戲。
曾任突尼斯作家協會主席的當代批評家穆罕默德·姆扎利(1925-)在1969年發表的文論著作《思想啟示錄》中,集中表達了他對文化和文學的見解。其主要觀點是:“建立真正的民族文化和突尼斯文學,此文學應從民族自身深處產生。文學是影響和被影響,是給與取,是和時代、環境、現實的對話、交流和辯論。文學具有崇高使命,關心人類事務,不應怕政治參與,但應區分文學與政治,反對奴隸主義和空洞虛偽……對文學的總的要求:體驗的真確,觀
點的新穎,表達的地道,目的的真誠。”
在東方現代民族主義作家中,有些作家并不簡單地否定文學的藝術性。印度的泰戈爾、埃及的陶菲格·哈基姆都是例子。陶菲格·哈基姆是埃及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現代文壇最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他從思想家的立場探討了文藝的美學本質問題。在《文學藝術》的開篇他就指出:“只有文學才會發現和保存人類和民族永恒的價值,只有文學才會帶有并傳承民族性和人性覺悟的鑰匙……而藝術則是馱著文學在時間與空間馳騁的活躍而有力的駿馬。”他甚至提出了“象牙之塔”論。在《來自象牙之塔》一書中說:“我不要求作家把自己囚禁起來,與世無交,以成為一個思想家,或離群索居,生活在思考的禪房里,而是要求他們與那些他欲與之交流的各色人等進行交往……作家經常生活在人們中間,但他又置身于高聳的‘象牙之塔中,這象牙之塔不是別的什么,只是那顆超越踐踏的純潔的心。他和人們在一起,在泥土中,是以他的身體,而不是他的心。他和他們分享一切,但不分享他們的道德虛弱、思想貧乏。他和人們在一起,為的是了解他們,愛護他們,描摹他們,之后卻要引導他們,以使他們有一個榜樣。”陶菲格·哈基姆從作家的角度。指出文學與生活的本質關系問題。這里的“象牙之塔”,實際是指文學源于生活,又指導生活;文學源于現實,又引導現實的辯證關系。
三、民族傳統的弘揚與民族靈魂的呼喚
民族主義文學在東方現代民族運動中承擔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以情動人,喚起民族成員的民族認同意識。民族認同意識必須以經驗世界為依托,以民族語言和文化為認同媒介。若沒有認同媒介,民族認同意識無從表達,無以寄存。因而,民族的歷史、傳說、神話,真實的或臆想的民族始祖以及各種民族習俗,祖國的名山大川,都可作為民族認同媒介而發揮重要作用。這一階段的民族主義作家,以各種方式從已有的民族資源中發掘文學意象,弘揚民族傳統,呼喚民族靈魂。
埃及詩人邵基290聯的著名長詩《尼羅河谷的巨大事件》,描繪埃及的巨幅歷史畫卷和祖先的光榮業績,追溯偉大的法老時代和古老埃及的歷史文化,為民族久遠輝煌的歷史傳統而自豪。馬哈福茲早期創作歷史小說的熱情很高,花大力氣研究民族歷史,意在從民族文化中發掘顯示民族解放需要的能量。他曾計劃寫40部歷史小說,都擬定了創作的題目。雖然后來沒有按計劃寫作,但他談到目的已經達到:“通過歷史,我已經說出了我要說的主題:廢黜國王,夢想一場人民革命,實現獨立。”埃及最典型的呼喚民族靈魂的作品是哈基姆·陶菲格的長篇小說《靈魂歸來》。
印度不僅有雄偉的山脈、浩瀚的海洋和奔騰的江河,更有久遠的歷史和豐富的人文遺產。印度的民族主義詩人、作家當然引以自豪。伊克巴爾在他的著名詩作《印度人之歌》中將古老的印度文明與其他文明比較:“希臘、埃及、羅馬都已從大地上消逝,/但我們的名字和標志依然留存至今。/我們的標識不滅自有其原因,/盡管時代變遷,我們多少次抵御過入侵的敵人。”謝利特爾·巴特格的代表詩作是歌頌印度的光榮歷史《印度之歌》。邁提里謝崳·古伯德的《印度之聲》2500行,其中的《往事篇》以極大的熱情“歌頌了印度古代文明和文化,她謳歌古代的高亢調子很能激勵起青年人的熱情”。古伯德在《自思》中把祖國說成是“升起太陽的地方”,她可以發出“哈奴曼一樣的力量”。瓦拉托爾在《母親的頌歌》中說:“母親的語言是具體的吠陀,/為她服務是我們神圣的職責/我們的生命為母親奉獻,/兄弟們,比母親偉大的神還有哪個?”詩中對吠陀的推崇、對祖國母親的評價是很虔誠的。伊斯拉姆是位穆斯林詩人,但他深受印度傳統文化的影響,在《叛逆者》這首著名長詩中,說自己“是因陀羅的兒子”,“是‘青頸”,“吞下了從苦海里攪出的毒藥”。
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詩人耶明非常重視民族語言的民族認同功能,它第一個運用“高級馬來語”寫詩,在1921年寫作了詩作《語言與民族》:“生于自己的民族,是用自己的語言/左鄰右舍都是一家的成員/馬來土地把我們撫養成高尚的人/在歡樂的時刻,還是在悲痛之中/手足之情把我們緊密相連/從語言中聽到了情誼綿綿/……從孩提時代和青年時期/直到死后埋入黃土里/自己的語言從不忘記/青年們要牢記,苦難的蘇門答臘啊/沒有了語言,民族也就絕跡。”
民族認同有不同方式,古老民族以血源、語言、宗教、文化傳統和習俗認同。這里就伊朗作家赫達亞特的長篇游記《伊斯法罕半天下》稍作展開。游記描述作者在一次假期中四天遠游伊斯法罕的見聞和感受。文中詳細敘述他啟程赴伊斯法罕途中的經歷。在伊斯法罕游覽恰哈爾巴格林蔭道、肖塞卻什米大橋、契赫爾蘇通宮殿、梅達尼沙赫廣場、阿里·卡波宮、甲米清真寺、伊瑪姆·扎杰·伊斯曼爾陵墓、擺晃塔、襖教徒之山等15處名勝的情景,交織穿插歷史傳說、現實場景和自然風光的描繪,敘述、描寫、抒情熔于一爐,展示了伊斯法罕這座文化名城的歷史厚重與滄桑,作品滲透著作者的民族自豪感。文中滿懷深情地寫道:“伊斯法罕的清真寺、大橋、園屋頂、高塔、瓷磚、卡拉姆卡爾布,直到今日還沒有失去他們的雄姿和光彩。這座工藝大師輩出的城市,在賽菲維特王朝時期,曾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如今依然享有歷史上的盛名。”作家是在對民族藝術傳統的贊美中,鞭撻和批判現實社會,追尋民族文化之根。
民族獨有的特征,往往成為民族精神和民族靈魂的象征。在民族主義詩人、作家筆下,這些特征被賦予了許多的文化內涵而受到贊美與呼喚。桑戈爾的《黑色的婦女》很有代表性,其中:“裸著身子的婦女,皮膚黝黑的婦女!/像熟透的飽滿的果實,像醉人的黑色的美酒,/你的雙唇呀,使我的雙唇神往;/透明的遠方草原呀,/在東風熱烈的撫愛下微微顫動。/雕刻精美的板鼓,繃得緊緊地板鼓,/戰士的手指敲得你達達響。/你的聲音深邃而低沉—_/你是崇高的愛情的歌聲。”這里的“黑女人”,不是性別意義上的黑膚色的女人,而是詩人心靈中的非洲、非洲精神、非洲靈魂。
在20世紀前六十余年里,東方民族主義文學思潮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深入而逐漸成熟,達到高潮。東方各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家形成了各自的民族主義思想體系,同時,東方主要國家的文學都完成了民族傳統文學向現代文學的轉型。蘊含各自民族文化精神的民族主義文學成為主流思潮,它以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現實生活作肥沃土壤,表達了東方人民的思想、情感和審美追求。
(責任編輯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