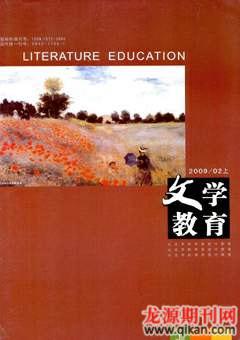女扮男裝與底層關懷
劉慶邦的小說《遠山》講述了一個女扮男裝的故事。但這不是對傳統敘事俗套的簡單模仿,而是真實地再現了一個當代底層婦女到小煤窯當礦工的的辛酸遭際。劉慶邦的成名作是《走窯漢》,不過,《遠山》里的“走窯漢”卻是一個女人,在這個女扮男裝的“走窯漢”的身上,寄托了作者深沉而激越的底層關懷。
古今中外有許多女扮男裝的故事。就中國而言,最有名的例子莫過于木蘭從軍的故事了。但《木蘭辭》是一個宣揚傳統儒家忠孝文化的故事,花木蘭從軍是因為“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所以她只能代父從軍,為家盡孝,為國盡忠。而美國人改編的電影則帶有文化誤讀的成分,西方視閾中的木蘭從軍變成了一個女權主義的敘事。可見,作為一個敘事模式,女扮男裝在不同的時代語境和文化語境中會有不同的含義。這就如同三角戀模式,三流作家寫三角戀,曹雪芹也寫三角戀,但境界是有天壤之別的,主要是因為三角戀模式中隱含的思想意蘊有著高下雅俗之分。所以,襲用已有的敘事模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既定模式中沒有新的意蘊的灌注。如果有了新意蘊的灌注,即使是老套的敘事模式也會重新煥發藝術的生氣。這篇《遠山》就是如此。
事實上,《遠山》中的女主人公由自己的遭遇想到了花木蘭,但她懷疑花木蘭是否實有其人,因為一個女人在軍營中待了十多年沒有被男人發覺,那簡直不可思議,而她到煤窯里當運煤工不久就露出了破綻。顯然,作者并不想簡單襲用“女扮男裝”這個古老的敘事模式,女主人公對木蘭從軍故事的懷疑,正流露了作者借用老故事寫出新意的動機。古典的木蘭從軍故事帶有強烈的傳奇色彩,甚至帶有神話的影子,其中的敘事破綻是經不起現代寫實主義者的推敲的。然而,《遠山》要講述的是一個現實主義故事,它必須符合現實主義敘事成規,比如所謂環境的真實和細節的真實之類,因為“真實性”是現實主義的核心規范。《遠山》中的敘事對真實性的追求是令人嘆為觀止的。作者對煤礦工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方式的精細刻畫,確實令人有身臨其境之感。煤礦工的生存狀態獰厲粗糙,充滿了原始野性,如小說中寫到的打眼工、放炮工、支護工、裝煤工,還有車倌兒,他們裸露著粗糲的身軀在漆黑的窯洞里揮汗如雨,他們黑乎乎的沾滿煤灰的雙手就是他們的“毛巾”,他們是一群生活在地洞里的“黑人”。為了生活,他們離鄉背井,從事著一種必須“習慣死亡”的勞作,而唯一的生趣就是工友間開著下流的玩笑,以及小說中講到的“斗雞”、“斗尿”,還有“吃涮鍋子”之類與性有關的本能行為。用當今的流行語來說,作者是寫出了煤礦工生存的“原生態”。但這種原生態的真實得益于作者的直接的生活經驗,而不是間接的道聽途說,或者是所謂深入生活的產物。劉慶邦在河南當過快十年的煤礦工人,他是真正從底層中生長出來的作家。他不需要什么“深入生活”,其實人生就是一個被生活深入的過程,而不是我們想象中的深入生活。
總的來看,《遠山》這篇小說具有現實主義的真實品格,它是寫實性的,同時也是傳奇性的,但傳奇性是內在于寫實性的,而不是簡單的外在附著物。讀《遠山》讓人想到中國古典的白話短篇小說傳統,想到“三言二拍”,在這個意義上,《遠山》可謂一篇當今中國底層社會的“拍案驚奇”。《遠山》的敘述節奏是張弛有度、緩急相間、雅俗交錯的,深得中國古典敘事傳統的精髓。劉慶邦的小說沒有刻意模仿現代派技法的西化痕跡,他的敘事是從容樸厚的中國作派。《遠山》也不例外。作者先用較長的篇幅對煤礦工的生存環境、生存狀態乃至生產工序做了精細的描摹,眾多陌生化的生活細節和場景撲面而來,炫人眼目;接著寫裝煤工“楊海平”下班回家,寫她對家鄉的回憶和思念,寫她的一雙小兒女的孝順,敘述的節奏一下子由開篇的緊張繁密轉入了舒緩溫情,而就在這種敘述的轉換中,讀者明白了女主人公女扮男裝的身份,知道了“楊海平”原來是她丈夫的名字,丈夫出車禍死了,她只好女扮男裝,像男人一樣依靠出賣苦力掙錢養家。接下來寫車倌對“楊海平”的挑釁,敘述又緊張起來,但放炮工的干預為她及時解圍,尤其是下班后的路上,放炮工對她的理解和同情,又把敘述節奏引向了迂徐有致。及至最后所有礦工都對“楊海平”表示了人格的尊重,這其實是對一個堅守人格的底層婦女的尊重,小說也就在這看似平淡而不平靜的敘述中結束了,留給讀者不盡的思索。
李遇春,評論家,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新文學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