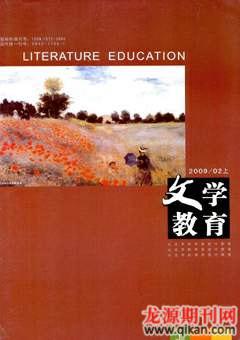論霍爾頓拒絕成長的另一種解讀
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是一部公認的具有自傳性質(zhì)的成長小說。小說截取主人公霍爾頓成長過程中關(guān)鍵階段具有特殊意義的幾天,著力描述、刻畫其經(jīng)歷、感受、回顧和期盼,折射其成長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及其挫折、煩惱、彷徨、感悟、選擇,進而反映一代人、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乃至整個人類成長過程中的動蕩、變遷,等等。霍爾頓的成長經(jīng)歷在眾多青少年讀者中引起了共鳴,很多戰(zhàn)后青年都能從主人公霍爾頓的身上或多或少看到自己的影子。在霍爾頓的成長個案中,他是拒絕成長的。一些學(xué)者從社會歷史環(huán)境的影響等方面來考察霍爾頓拒絕成長的原因。比如Curnutt 教授就認為二戰(zhàn)后的異化青年小說(Alienated-Youth Fiction)中的異化青年(其實就是反成長青年——筆者注)拒絕和社會妥協(xié),拒絕成長就是因為受戰(zhàn)后物欲橫流、虛偽冷酷的社會現(xiàn)實以及科技進步物取代人而成為中心的變化等等影響青年成長而使得他們變得孤僻異化(Curnutt,P5-8)。一些學(xué)者采用心理社會學(xué)者Erik H. Erikson 的“身份危機說”(identity crisis)從社會心理方面對霍爾頓的反成長進行研究(Curnutt,P68),還有一些人從教育制度及霍爾頓本人的膽小軟弱的個性特征等方面探討霍爾頓拒絕成長的悲劇成因。[1]本文擬從文學(xué)原型及西方傳統(tǒng)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對霍爾頓的影響等方面對他成長過程中表現(xiàn)出來的反成長的根源進行探索。
一
在歐洲文學(xué)的傳統(tǒng)中,成長主題有很多原型,比如荷馬史詩中的大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成長故事;古希臘經(jīng)典悲劇《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的道德成長,等等。以《圣經(jīng)》中關(guān)于亞當(dāng)和夏娃的失去純真的成長故事最為經(jīng)典。亞當(dāng)和夏娃在撒旦的誘惑下,偷吃智慧果而被趕出伊甸園。在亞當(dāng)和夏娃的成長中,他們屈服于誘惑,從而受到懲罰。自由自在的伊甸園生活隱喻了無憂無慮的童年。失去純真就意味著要受懲罰。此外,西方傳統(tǒng)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如單純優(yōu)于復(fù)雜、天真優(yōu)于老練等也在這個故事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
亞當(dāng)和夏娃失去純真的原型故事及其體現(xiàn)出來的西方傳統(tǒng)思想對歐洲文學(xué)和西方人的價值觀影響很深。浪漫主義時期的一些作家,如歌德、盧梭、華茲華斯等,就以消極的觀點看待成長。他們認為青年人應(yīng)避免亞當(dāng)和夏娃的墮落,保持純真,因為童年是人生中與自然最為和諧的一個時期。而大自然是人生歡樂和智慧的源泉。在他們看來,成熟會影響人類從大自然中獲取智慧。隨著年齡的增長,人變得越來越社會化,離智慧的源泉──自然越來越遠。華茲華斯在《怦然我心動》(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這首詩中寫到“孩子乃人父”(The Child is the father of the Man),[2]由此可以看出,華茲華斯對兒童及純真是多么的熱愛和崇拜。
亞當(dāng)和夏娃失去純真的故事原型對美國文學(xué)影響也頗深。亞當(dāng)和夏娃失去純真的故事“作為小說人物戲劇化的突然意識到對美國夢的期待與現(xiàn)實之間的差異的母題”,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創(chuàng)作提供了可能(Curnutt,P65)。R·W·B·路易斯在他的《美國亞當(dāng):純真,悲劇和十九世紀(jì)傳統(tǒng)》一書中提出亞當(dāng)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隱喻了美國(人)勢必要褪去純真,才能得以成長,重返伊甸園是不可能的。美國小說中的“人物代表了‘墮落后的亞當(dāng),他們必需要面對自己的人性墮落”(Curnutt,P65)。在最后一章中,路易斯明確指出了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具有這種亞當(dāng)?shù)膫鹘y(tǒng)。[3]
二
《麥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爾頓正處于從童年到成人過渡的關(guān)鍵的青春期。從《圣經(jīng)》中亞當(dāng)和夏娃的成長原型來看,霍爾頓正受到知識的誘惑:即對自己和周圍世界的認知。在這一關(guān)鍵時期,霍爾頓面臨人生中一次重要的選擇:是迎合社會現(xiàn)實、同流合污還是堅持美好理想、堅守孩童世界的純真?霍爾頓就是在這種現(xiàn)實與理想、變與不變之間游走,備受折磨,痛苦不堪。盡管霍爾頓試圖逆西方傳統(tǒng)價值觀而動,然而他始終不能擺脫西方傳統(tǒng)思想的影響。如德里達批判的那樣,西方的思想傳統(tǒng)(包括哲學(xué),文化和語言等)是建構(gòu)在一種二元對立范式的基礎(chǔ)上,如理性/感性、真實/謊言、無邪/墮落、文明/野蠻、男性/女性、美/丑、善/惡、等等。并且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傳統(tǒng)認為每一組的前者優(yōu)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來的“他者”(Other)(程錫麟,117)。受這種西方傳統(tǒng)思想的影響,霍爾頓認為純潔的兒童世界遠遠優(yōu)于丑陋的成人世界,純真優(yōu)于成熟,這也是他一直拒絕進入成人社會,拒絕長大的原因之一。從他對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思考可以看出,霍爾頓懼怕變化,易被復(fù)雜性壓倒。他希望每件事都像博物館里的愛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的塑像一樣容易理解,有著不變的外表。
在霍爾頓的心目中兒童世界是純潔、美好的;成人世界則是復(fù)雜、虛偽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成長就是意味著要離開兒童世界,進入成人世界。然而純潔優(yōu)于復(fù)雜、天真優(yōu)于老練的這種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限制了其他的可能性,阻礙了他對復(fù)雜生活本質(zhì)的認識。在霍爾頓狹隘的理解里,成長就意味著失去純真變得世故圓滑,變得和成人一樣庸俗、墮落、虛偽。顯然霍爾頓不想和他痛斥的成人同流合污。這表現(xiàn)在他對兒童世界的偏愛和依戀以及對成人世界的痛恨上。在霍爾頓的眼里,成人世界都是像愛爾敦·希爾斯(Elkton Hills)學(xué)校校長那樣,是他“生平見到的最最假仁假義的雜種”(塞林格,12;以下只標(biāo)頁碼);像斯塔德萊特和阿克萊(Ackley)一樣,庸俗無聊;像他的律師父親一樣,爭名為利。整本小說中,霍爾頓都是孤獨郁悶的,只有在想到與兒童世界的純真有關(guān)的一些東西時或與兒童接觸時,他才有稍許的開心和安慰。比如,當(dāng)霍爾頓在路上遇到那個唱“你要是在麥田里捉到我”的小男孩時,他的“心情舒暢了不少,心里不像先前那么沮喪了”(107)。即使是同樣的事情,在孩子和成人做來卻有截然不同的效果。同樣是撒謊,由孩子做來就覺得只是好笑。比如在公園里碰到的溜冰小女孩,霍爾頓“喜歡”她,覺得她“很好,很懂禮貌”,就連她托辭“找她的朋友”來拒絕霍爾頓的邀請一起去喝熱巧克力的舉動在他看來也是讓他“笑疼肚皮”的(111)。在博物館里等菲比遇到的兩個小男孩,盡管霍爾頓能確定“十拿九穩(wěn)他在撒謊”,但是他們的舉止讓他“笑疼肚皮”(188)。還有,同樣的睡覺姿勢:“她(菲比)的臉側(cè)向枕頭的一邊。她的嘴還張得挺大。說來好笑。那些成年人要是睡著了把嘴張得挺大,那簡直難看極了,可孩子就不一樣。孩子張大了嘴睡,看上去仍挺不錯。他們甚至可以把口水流滿枕頭,可他們的樣子看上去仍挺不錯。”(147)由此可以看出,霍爾頓對兒童世界的偏愛。
然而現(xiàn)實中的兒童世界并不是霍爾頓想象中那么純潔美好。現(xiàn)實世界中的孩子們也不是他認為的那般單純﹑幼稚﹑誠實。比如霍爾頓在博物館門前遇到的兩個小男孩明顯的就是在為自己逃學(xué)而撒謊;還有霍爾頓在公園幫助溜冰的小女孩系好冰鞋帶后邀她喝東西,小女孩回答“她得去找她的朋友”來委婉地拒絕了霍爾頓。小男孩的不誠實和小女孩在與人交往中的世故與圓滑無不消解了霍爾頓對現(xiàn)實世界中的兒童世界純真的幻想。在霍爾頓的眼里,他的妹妹菲比最能代表兒童世界的純真,然而,盡管菲比比霍爾頓小,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說,菲比比霍爾頓成熟。菲比能夠理解成長是一個必要的過程;她知道霍爾頓拒絕成長更多的是揭示了他的自我而不是外部世界。盡管菲比從未明確說明,但她似乎意識到霍爾頓對世界上其他人所表現(xiàn)的憤懣實際上是對他自己的憤懣(Natchez,32-34)。換句話說,霍爾頓認為純真的兒童世界并不是如他想的那般單純。年齡的大小與成熟與否并不一定成正比。他最喜愛的妹妹菲比就是最好的一個例證。現(xiàn)實中的兒童世界顛覆了霍爾頓理想中的樂園,于是他虛構(gòu)了一個美好的兒童世界:他把童年幻想成一個田園詩般的麥田(伊甸園),孩子們在那里盡情地嬉戲、玩耍。而自己就是那些孩子們的守望者,守住他們不讓他們跌下懸崖——進入成人世界。其實他的守望是希望孩子們永遠活在幻想中,不進入現(xiàn)實生活,包括不進入現(xiàn)實中的兒童世界。
三
盡管霍爾頓消極面對成長,努力保持純真,遠離腐敗的成人世界,但是,受知識的誘惑,他有時又非常渴望長大,早點認識那個注定要帶給他痛苦的現(xiàn)實世界。由于受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影響,在他的潛意識中,作為美好無邪的兒童世界的對立面,成人世界自然是虛偽、墮落的。由于他對成人世界錯誤的定位和狹隘的理解,導(dǎo)致了他在成人世界的受挫。他認定成人世界是虛偽、墮落的,因而在成人世界中也只能虛偽。他也確實這樣做了。從故事一開始,他就撒謊。比如他為了不聽斯賓塞喋喋不休的教誨,撒謊說“要到體育館收拾東西”(15);在去紐約的火車上,不管出于什么樣的目的,他對同學(xué)的母親撒謊;為了在酒吧能喝上酒,他謊報年齡;為了酒吧里的三個女人調(diào)情,他謊報年齡;他在菲比的學(xué)校里為了讓學(xué)校的老太太為他遞紙條而謊稱“母親病了”(187)等等,霍爾頓一系列的謊言證明霍爾頓如自己承認的那樣:“你這一輩子大概都沒見過比我更會撒謊的人”(15)。除了撒謊以外,霍爾頓還喝酒、召妓、甚至發(fā)展到有偷窺旅店里的人的變態(tài)行為的嗜好,等等。然而現(xiàn)實生活并不是他的膚淺認識那般簡單,因而在復(fù)雜的現(xiàn)實世界里,他屢屢受挫,遭到拒絕,無法與成人世界溝通。就像他承認無法跟斯賓塞溝通一樣,因為他們倆“一個在南極一個在北極,相距太遠,就是那么回事”(13)。盡管霍爾頓偶爾有想要長大的沖動,但是他對失去純真的不能釋懷讓他在潛意識中拒絕成人世界;與周圍人交流中的所表現(xiàn)出來的無能更是讓他有一種被人拒絕的感覺,因而他變得異化起來,不愿積極面對成長。正如Jon Natchez和Brian Phillips在《〈麥田里的守望者〉導(dǎo)讀》一書中指出,“霍爾頓的異化是自我保護的途徑”(Natchez,2003,37)。他那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獨阻礙了他與周圍人的交流。他用那種卑微的優(yōu)越感來進行自我保護。因此,“霍爾頓的異化是他生活中僅有的穩(wěn)定因素的來源”(Natchez,2003,37)。與霍爾頓不同,斯塔德萊特能成功地融入他周圍的成人世界。從某種意義上講,霍爾頓對他室友的厭惡也反映了霍爾頓沒有能力融入成人世界。因此,在被成人世界拒絕后,霍爾頓自然而然只有回到他所熟悉的兒童世界。因為在被拒絕后,他發(fā)現(xiàn)兒童世界要容易得多,安全得多。因而他不想離開他的伊甸園。
在霍爾頓眼里,菲比、琴·迦拉格來(Jane Gallagher)、艾里(Allie)和詹姆斯·凱瑟爾(James Castle)代表了的兒童世界的純真。菲比比霍爾頓小六歲,正處于美好的童年時期。在霍爾頓看來,菲比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包括她那難看的睡姿,包括他對菲比學(xué)習(xí)打嗝的無聊游戲的包容。從某種意義上說,霍爾頓對菲比的依戀,與其說是他對菲比本人的依戀,還不如說是他對童年的依戀。琴是霍爾頓的夢中情人,盡管他多次提到,但讀者與她從未謀面。單純的琴只存在霍爾頓過去的回憶里。而現(xiàn)實中的琴與“變態(tài)之王”(58)——斯塔德萊特的約會證明如今的琴早已改變,純真已不復(fù)存在。霍爾頓對過去那個單純的琴的愛戀其實也只是霍爾頓對逝去的純真的懷念而已。另外,代表純真的弟弟艾里和校友凱瑟爾死了。艾里和凱瑟爾之死暗示了純真只有以死這種方式才能得以保留。因而在霍爾頓的成長中,面對失去純真的痛苦和恐懼時,霍爾頓表現(xiàn)出了一種明顯的死亡傾向。由此看來,霍爾頓要成長而又不失去純真是不可能的,重返兒童世界更是不可能。正如亞當(dāng)和夏娃不能重返伊甸園一樣,霍爾頓不可能永遠活在對逝去的童年的緬懷里。因而他的成長是不可避免的,失去純真也是勢在必行的。《圣經(jīng)》中的故事告訴我們,亞當(dāng)和夏娃偷吃禁果后,雖然獲得了知識,但是必須為此付出代價。他們被逐出了伊甸園,上帝懲罰亞當(dāng)要受勞役之苦,夏娃則要承受生育之苦。人類要成長就必須離開懵懂幸福的童年(伊甸園),要發(fā)展明辨是非的能力就必須接受失去純真獲取經(jīng)驗的事實。
注釋:
[1]黃保超,“《麥田里的守望者》的悲劇成因”,《井岡山醫(yī)專學(xué)報》[J], 2005年7月,p163-164.
[2]William Wordsworth,“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http://www.bartleby.com/145/ww194.html
[3]R.W.B.Lewis,The American Adam:Innocence, Tragedy,and Tradi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 p.127-128,pp.197-198.
黃雪飛,西南科技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