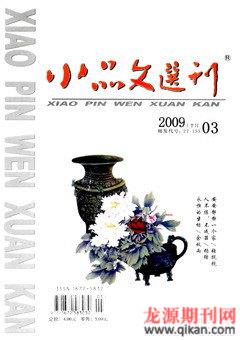尋根《易經》
楊東明
周易大熱的那些年,也跟著讀了幾本關于《易經》的書。被人稱作所謂的文化人,沒啃過四書五經,總覺得像是蓋房沒有奠基打樁。然而,幾本書啃下來,卻仍舊是霧水一頭,要領不得。
去了一趟湯陰縣,拜謁了周文王姬昌演《周易》的羑(音有)里城,頓然覺得好像讓醍醐灌了一回頂。當初讀“易”之時,每每會對著那些長長短短的“—”和“——”生出疑惑,不知文王緣何會想出用這樣的圖形作為卦象的標記?及至看了囚臺邊旺長的蓍草,方才大悟,那些長短不一的卦形,不過是蓍草的枯莖罷了。身為囚徒,手邊并無長物,也只能扯些蓍草把玩解悶了。
一個死囚,不知何時紂王就會將他“辟尸”,將他“炮烙”,想必精神壓力極大,惶惶然不可終日。用蓍草棍棍推演八卦。讓自己陷在變幻難測的玄想之中,不失為一種排遣和消解壓力的方式。
姬昌被囚前,已經做了“西伯”,統領著西方周姓一族。忽然間由爵爺而為階下之囚。那變易是很大的。世事無常,運數不定。“易”(變)應當是他心中最深的感慨了。他無疑是企盼再度變易的,他必會冥想各種咸魚翻身的可能,如此一來,用八卦推演變易就成了精神的和實用的雙重需求。
一個天才的死囚窮盡所能專注和投入地推演先人伏羲的八卦,必有所得必有不滿。八種排列八種組合對于他來說就顯得過于簡單,由八而生出六十四就成了某種必然。其實,八能生出六十四,六十四又何嘗不能生出四零九六,四零九六再生出……只是如此一來就過于繁復,讓人難以把握。這樣一想就明白了,《易經》是在講變與不變的,它包含了偶然性、或然性、必然性,這就有了哲學的味道,有了辯證法。易是用數的變化來表示的,也就有了數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那些卦辭與爻辭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倫道德,森羅萬象無所不包,也就匯聚了先人們博大的知識和智慧。
周文王是善于機謀權變的,紂王殺了他的長子伯邑考燉成肉湯,周文王心知肚明卻裝傻充呆,硬是將肉湯喝下去,然后趁人不注意再吐到荒地里,讓羑里城多出了一個“吐兒冢”。周文王的部下是諳于行賄的,他們用寶馬和美女討得紂王的歡心,竟然使周文王得釋。復出之后的周文王先后滅了黎、邗(音含)、崇等國,最后由他的兒子周武王滅掉了殷商。如此尉烈的變易是紂王所始料不及的,亦不知是否是周文王曾經推演過的結局?
世事變幻無窮,人生的機緣際遇,難以逆料。或許正因為如此,人類才力求做出預測的吧。把握變化推測未來,是人類永遠的心理需要。人類已經在預測天氣了,人類已經在預測地震了,人類還想要預測更多更多的東西。做官的人想預測自己的官運,經商的人想預測自己的財運,貪污受賄的人想預測會不會敗露,作奸犯科的人想預測能不能逃脫……心惶惶而無解,也就想到要向卦中來索求了。
其實,事物的變化和結局還是有跡可循的。比如下雨吧,氣壓、濕度、溫度、風力……一項項條件都湊齊了,想不讓它落水都難。條件就是卦,條件就是爻,等那些條件排列組合到了,結局也就難以避免。
每個人都是最清楚自己的。不必去求別人,只需自己在心里給自己打一卦就行了。你把你做下的那些事都一一排列起來,都一一組合起來,等它們備足了,結果必然會出現。種了瓜的得瓜,種了豆的得豆,種了臭狗屎的人就等著收獲臭狗屎吧。
眼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競爭就有變易,不易的應該是我們自己的心態。隨緣自適,從容淡定,以不變應萬變,以不易應對萬易,這才是做人的根本。
選自《今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