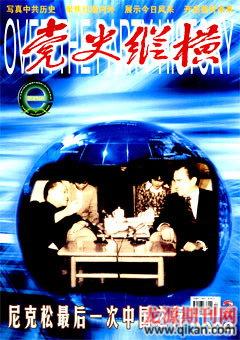改革開放以來的中美關系及展望
王克群
2009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
30年來,中美關系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從1979年建交到1989年,在鄧小平主持工作的十年里,中美關系得到了比較好的發展,特點是“初步發展,打下基礎”。第二個階段是1989年到1999年,中美關系經歷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和危機,幾場危機沖擊了中美關系——“八九”風波、李登輝訪美、駐南使館遭襲,但中美關系并沒有倒退,度過危機后又繼續向前發展,特點是“曲折發展,趨于成熟”。第三個階段是本世紀的頭三年,“調整發展,保持勢頭”。第四個階段是2003年至今,“平穩發展,互利合作”。中美關系30年盡管起伏跌宕、曲曲折折,但發展是主潮流。
中美建交,雙邊關系全面發展
在尼克松訪華和中美“上海公報”發表近7年之后,卡特政府接受了中國提出的建交三原則,即在臺灣問題上“斷交、撤軍、廢約”,中美建交的障礙得以排除。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兩國建交公報指出: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圍內,美國人民同臺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系。緊接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訪問美國。中美建交和鄧小平成功訪美,揭開了中美關系的新篇章。
在里根總統執政初期,中美在臺灣問題上有過激烈交鋒。經過艱苦談判,兩國政府于1982年發表了著名的《八一七公報》,就分步解決售臺武器問題達成協議。美方表示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政策;美國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將逐步減少售臺武器,并經過一段時間最后解決這一問題。
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和八一七公報,共同構成了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值得一提的是,中美關系正常化是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啟動的,而中國的改革開放為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增添了強大動力。上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擴大,中美兩國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交流日益活躍,兩國關系得到全面發展。
蘇東劇變,中美關系曲折前行
1989年前蘇聯解體后,依照美國的思維邏輯,“聯中制蘇”即已成為歷史,而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與美國對立并迅速發展的中國,日漸對美國的國際地位甚至安全構成威脅。于是,“中國威脅論”的聲浪及政策主張成為美國對華政策制定的核心。這是上世紀90年代中美關系迂回曲折、大起大落、錯綜復雜的根本原因。如1989年到1992年對中國施行的全面制裁、1993年至1994年對華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掛鉤的高壓、1995年到1996年的臺海危機,雖然1997年和1998年中美兩國領導人實現互訪,中美朝著“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的方向發展,雙邊關系有較大幅度的實質性改善,但1997年“政治獻金案”、1999年“考克斯報告”及“李文和案”,特別是1999年5月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大使館與2001年4月南海撞機等事件,仍然干擾著中美關系的發展。之所以上世紀90年代中美關系并未退回到冷戰時期的那種對抗狀態,完全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改革開放在推動著中美關系的發展。因此,與冷淡、緊張、大起大落的政治安全關系相反,經貿關系成為冷戰后中美關系發展最快、合作最有成效的領域。
上世紀90年代中美關系出現新突破的原因,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中共十四大召開,明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找到了在經濟發展中相似的一種運行體制。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為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提供了制度保證。90年代以來,中美雙邊貿易、投資、技術等方面的合作規模增長在10倍左右。美國已成為中國的第一大出口貿易國,對美出口占我國出口總額的20%;中國成為美國第四大貿易伙伴國。美國對華直接投資額的協議金額也居各國對華投資首位。以市場為渠道進行的經濟交流和文化接觸成為冷戰后中美關系的主要內容,令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產生了“雙軌道”現象,并牽制著政治關系發展,這讓中美關系屢屢在危險時刻能夠及時走向緩和。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只是發展中美關系的重要動力之一,那么到了90年代,改革開放則成了發展中美關系的最主要動力。中國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中美關系史上經濟關系受政治與戰略關系支配與控制的狀態,使經濟關系的獨立性上升并影響甚至決定著政治關系的發展。
21世紀初美國對中國的“遏制”
二戰后,美國不僅是國際反華勢力的總后臺和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惡化的總導演,還是在亞太地區企圖構筑反華屏障的主導國家。長期以來,美國加緊對中國推行“分化”“西化”戰略,使中美兩國的矛盾呈現出明顯激化和上升的趨勢。這種矛盾和沖突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中美兩國在社會制度上存在根本沖突。
根除、扼殺社會主義制度是美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內容和基本目標。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戰略的核心就是要搞垮社會主義,用美國式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一統天下。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美國稱霸世界的欲望急劇膨脹,冷戰思維明顯強化,逐步把封殺社會主義的矛頭轉向中國,企圖通過“分化”“西化”社會主義中國,來實現西方政治家和預言家們所期望的“歷史的終結”。
新世紀初,美國對中國推行“分化”“西化”戰略呈現出新的特點。一是以“分化”帶動“西化”。克林頓執政后期,美國政府就表現出了更多重視對中國“分化”的政策趨向。布什執政后,美國更加突出“分化”戰略,將“西化”融于“分化”之中,以對中國的“分化”來帶動“西化”。美國把臺灣問題、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作為對中國實施“分化”戰略的三大突破口。尤其在臺灣問題上,美國在加緊軍事介入、阻止中國統一大業的背景下,大力宣揚臺灣的“民主”成就,竭力鼓吹美國有責任、有義務保護臺灣的“民主政治”,并以臺灣的“民主政治”對中國實施滲透。二是打著維護人權和宗教信仰的旗號對中國實施“西化”。以維護人權為招牌,以宗教信仰為幌子,是美國對中國實施“西化”戰略的重要形式。美國還通過各種宗教團體和宗教組織對中國進行滲透,縱容和支持“東突厥斯坦”宗教分裂勢力在中國新疆境內進行策反活動。“911”事件后,美國在阿富汗實施的反恐戰爭中搞雙重標準,對中國提出的“將打擊國際恐怖勢力和東突厥斯坦反華勢力相結合”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企圖用“東突厥斯坦”這股極端分裂勢力長期牽制中國。三是利用合法渠道加緊對中國實施“和平演變”。多年來,美國通過經貿關系、科技合作、文化交流等各種正常渠道對中國實施的“西化”滲透從未間斷。布什曾經宣稱,“輸出美國的資本和商品,就是輸出美國的價值觀念”。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幾十萬學子定居美國,許多名牌大學高材生流向外企,美國的價值觀念通過經營理念和生活方式,難以避免地對他們的思想觀念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這種人才的流動,實質上是對中國年輕一代的爭奪。美國也正是把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年輕一代的身上。
其次是中美兩國在戰略利益上存在根本沖突。
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將國家利益與世界人民的基本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把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共同發展作為重要使命。中國的國家戰略和外交政策與美國的國家戰略和安全利益存在著根本沖突。
在政治利益上,雙方存在多極與單極、反霸與稱霸的根本對立。反對霸權主義,建立一個多極化、平等化和民主化的世界是中國外交的基本目標;而美國則大力推行稱霸世界的基本戰略,竭力維護其“一超”地位,企圖建立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單極化世界。因此,美國始終將中國視為推行單極化戰略的最大障礙,把遏制和防止中國發展成為世界和地區性大國作為其安全戰略的長期重要任務。
在安全利益上,雙方存在新舊安全觀的根本對立。中國一貫主張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型安全觀,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力求實現世界的普遍安全和真正和平;而美國卻大力推行“新干涉主義”,打著“為價值觀念而戰”和反恐戰爭的旗號,頻繁推行“炮艦”外交,企圖打出一個“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和平”。美國在舊安全觀驅動下挑起的各種沖突和軍備競賽,都對中國的安全構成了威脅。
在經濟利益上,雙方存在新舊國際秩序觀的根本對立。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實現世界的共同發展和普遍繁榮,是中國外交的奮斗目標;而美國則以超強的經濟實力為后盾,竭力維護國際經濟舊秩序。它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加緊推進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企圖使經濟全球化變成“美國化”;它動輒揮舞經濟“大棒”,不時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眾多國家實施制裁;它大力推行“金融霸權”和“信息霸權”,操縱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影響和制約他國經濟,對世界各國實施“信息侵略”;它利用對國際經濟組織的控制,大力推行“制度化霸權”,企圖用國際規則制約他國。
在民族利益上,雙方存在顛覆與反顛覆、分裂與反分裂的根本對立。維護國家主權,捍衛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是中國堅定不移的外交戰略,也是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而美國卻扮成“世界警察”的模樣,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不是推行顛覆政策,就是推行分裂政策。多年來,美國把顛覆中國政權、分裂中華民族作為其全球戰略的重要內容,不僅在臺灣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上大做文章,就連美國社會本來反對的“法輪功”邪教組織也大加利用。美國對中國的顛覆、分裂活動愈演愈烈。
“911”事件后中美關系的新轉折
上臺伊始,布什政府在臺灣問題上比許多前任美國總統激進得多。但在“911”事件發生后不久,白宮便放出話說,布什總統不希望有關中國的問題分散他解決其它外交政策問題的注意力,自此以后,避免與北京產生任何糾紛成了華盛頓外交班子的一項重要原則。
對中國國力增強的認可是中美關系轉變的重要原因。在國際恐怖主義成為美國最大的敵人之后,布什政府開始努力尋求同日新月異的中國建立一種積極的關系。如今,美國已不言自明地認定中國是“全球幾個主要力量中心”之一,為了對付國際騷亂和不穩定,這些力量中心需要相互配合。無論是反恐,還是防擴散,美國都需要與中國密切合作。對此,設在華盛頓的智囊機構——大西洋理事會的亞洲計劃主任班寧·加內特指出,布什政府在努力打擊恐怖主義和“無賴國家”之際,是沒有心思與中國發生沖突的,本屆政府已經意識到,與中國對抗對自己沒有好處。
在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看來,能否容忍崛起的中國是中美關系走向理性和建設性的關鍵。他既不同意現實主義者的“日漸崛起的中國與維持現狀的美國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的論斷,也不同意理想主義者的“中國與美國會成為最親密的伙伴”的觀點。這位歷史學家認為,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系,是具有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正常關系:有時親密合作,有時吵吵鬧鬧,但是,肯定不會公開地相互敵對。如今,這種中美關系既非“戀人”也非敵人的認識,正在被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所接受。
也正是基于這種認識,美國不愿再過度挑戰大陸的臺灣利益和統一信念,只是偶爾給北京一個信號,使之了解美國對臺立場的底線,即不能容忍大陸在臺灣并未宣布獨立時動用武力;但美國又不希望臺灣挑戰大陸,如果大陸在臺灣宣布獨立時動用武力,美國是否會干涉將是不確定的。換句話說,美國任何一位總統都不會為了保護臺灣獨立而決定卷入與大陸的軍事沖突之中,美國不可能按照臺灣的主觀意愿,公然協助支持“臺灣獨立”目標的實現。
對布什政府來說,在臺灣問題上挑戰中國實在是太過復雜和冒險了,為避免與大陸在臺灣問題上陷入僵局,必須在適當的時候對臺灣施加壓力。因而在陳水扁等人鼓噪要進行修憲和公投之際,美國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特別強調了美國的“與臺灣關系法”,表示美國愿意對臺灣出售武器,但是沒有承諾軍事上的協防。與此同時,美國前國務卿黑格則表示,在當前,美國應該重申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堅決反對臺灣“獨立”。
正如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羅伯特·羅斯所言,美國不能挑戰中國的安全,因為在亞洲大陸,中國是惟一的大國,美國不能挑戰中國在亞洲大陸的地位與作用。中國也無意挑戰美國在亞太的利益。可是中美之間有一個熱點問題,即臺灣問題。這是熱點,是利益沖突。但利益沖突跟大國矛盾不一樣,“大國矛盾很難解決,利益沖突是比較溫和的”。對美國來說,在伊拉克和反恐問題焦頭爛額的關口,在挑戰中國的代價越發巨大面前,在許多方面都有求于中國的時候,是不希望這個熱點演變為爆炸點的。臺海的平靜,既符合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也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奧巴馬上臺后中美關系的展望
展望一:中美關系會繼續穩步發展。
隨著奧巴馬歷史性入駐白宮,美國外交政策的調整將不可避免。以往,在選戰前,我們多多少少都會有些疑惑或者擔心,疑惑的是中美關系何去何從,擔心的是候選人大打“中國牌”可能傷害到中美關系,而新總統上臺后中美關系的大幅“低開”似乎更是成了慣例。所有這些,都將會使中美關系受到影響,而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但此次卻有所不同,其主要原因有四點:一是布什總統在任期內特別是第二任期內還是做了一些積極的努力,對中美關系有很大推動;二是中國國力在增強,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也在上升;三是中國在外交上“不把雞蛋全都放在一個籃子里”,換句話說,就是中國有了更多的“出口”,比如與俄羅斯
的關系,與歐洲的關系,與亞非拉的關系,總體上是越來越好,合作面也大幅拓寬,這有助于平衡跟美國的關系;四是中國入世后,與國際接軌很快,迅速了解和熟悉了國際政治和經濟中的游戲規則,外交上也變得更為自信、直接和有效率。基于此,我們有信心認為中美關系會繼續穩步發展,而奧巴馬政府也不會無視這些因素。
展望二:雙邊貿易是一個重點。
在討論貿易前,要看看奧巴馬對華友好的一面。他在夏威夷出生并長大,與母親在亞洲生活過,有不少亞裔及華裔親友,對華人極為了解和認同。獨特的經歷讓他能以理性的態度看待中美長遠關系。他曾創立“參議院美中工作小組”,主張推進中美關系,促進臺海和平。他曾在美國商會月刊上撰文,闡述其中國政策。其中在臺灣問題上,他說“我們支持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關系的改善。在雙方善意的努力之下,兩岸關系迎來了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好時機”。這與中國政府的立場基本一致。基于這一了解,與奧巴馬打交道,比當初與克林頓和布什剛上臺時或許要容易一些,可以以誠相待,贏得彼此信任,并以此在重要問題上保護自己的利益。
奧巴馬在競選中曾表示,要在匯率和貿易問題上向中國施壓,于是有觀點認為,奧巴馬當選對中國不利。這似乎有點過慮了。不錯,民主黨要求采取一些貿易保護措施維護美國工薪階層的工作機會,不利于中國的對美出口貿易。但是,奧巴馬上臺后,若按照其承諾,將會盡快從伊拉克撤軍,將資金用于經濟領域而不是戰場。這一方面能給美國經濟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奧巴馬在國際關系中的溫和立場,將促進美國和世界各國關系的改善。這有利于增強國際資本投資美國的信心,促進美國經濟復蘇。美國經濟恢復,民眾購買力增強,對維持中國的對美貿易增長無疑是有幫助的。
中美關系的大局已經基本確定,不僅經濟金融相互滲透,即使安全問題也是合作大于分歧,更重要的是,中國一直以來的發展軌跡可以證明,中國是在主動融入的前提下發展自我,比較而言,中國比美國更愿意追求合作,這是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都必須予以正視的客觀現實。
奧巴馬上臺后,雖然中美之間依然會存在分歧,利益沖突和妥協的進程也會一直持續下去,但近年內不會出現大的動蕩。隨著兩國聯系的進一步密切,在經濟、安全、觀念甚至人事上的相互適應都在提高,兩國的沖突都將是有分寸的,相對理性的、可控的。在這一基礎上,領導人的更替對于兩國關系的影響會比過去要少。
至于中美關系中最敏感的臺灣問題,中國越發展,美國為了臺灣而和中國正面沖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奧巴馬上臺首先要解決金融危機問題,還有反恐和防擴散問題,這些都需要中國的協助,在臺灣問題上挑起事端對美國來說并無益處。而隨著海協會、海基會在臺灣簽署直航、通郵等四項協議,兩岸關系有了實質性突破,出現了全新局面,所以雖然不能保證臺灣問題在近幾年內不再生出波折,但應該不會出現激烈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