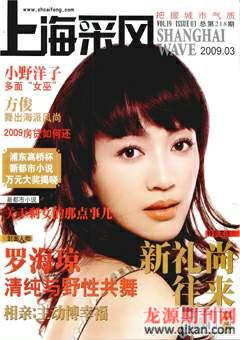牛年伊始談抽象
欄目主持 → 袁龍海
嘉賓 → 王劼音(原上海美協副主席、畫家)
李磊(上海美術館執行館長、畫家)
許德民(《中國抽象藝術》主編、詩人、畫家、藝術評論家)
趙葆康(復旦視覺藝術學院教授、畫家)

抽象藝術是現代主義流派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中國當代抽象藝術,萌芽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到五十年代,由于中國文藝方針的改變,抽象藝術一度被視為不能被大眾接受的頹廢藝術,直到改革開放以后,上海又漸漸成為中國抽象藝術的重鎮,但在整個官方藝術大展中,抽象藝術仍然只占很少的比例,在藝術市場中也是少有問津。但是,這一切都無損抽象藝術的學術價值,反而顯現出一種特立獨行的自由品格。面對這門經歷長久壓抑又充滿前景的藝術,我們看到,通過近年來一系列展覽、出版、研討活動,它正顯示出蓬勃的生命力。牛年伊始,上海采風雜志社假座角度抽象畫院,邀請了部分專家,來談一談抽象藝術在當代的狀況和現實意義。
袁:各位老師好,請大家來談抽象藝術,是想談談在當代藝術高潮過去之后,是否給抽象藝術帶來了新的生機。王劼音老師認為自己的畫不是純抽象的,是在意象與抽象之間,采風雜志社認為他也代表了一種抽象藝術傾向。
許:王老師的畫其實是幾個畫種都結合起來的藝術,有時意象比較強,有時也畫純抽象的畫,總的藝術傾向是偏向抽象藝術的,他是跨界的畫家。
王:我認為一個畫家可以高興怎樣畫就怎樣畫,但從抽象藝術這個話題上講,希望你們找抽象畫方面的代表人物如余友涵等。
袁:我們這個選題,并非要純粹的抽象畫家才能擔當,好比油畫家也可以談中國畫。今天首個問題是抽象藝術的本土化。許德民老師做了很多工作,近年來又連續出版了三期《中國抽象藝術》,他的個人專著《中國抽象藝術學》也已經問世,這本專著填補了中國抽象藝術理論空白。抽象藝術目前還存在著認識誤區,我們先請許老師來談一談。
許:我在“一線”將近十年,觀眾、畫家、市場心態都很熟悉。目前,中國抽象藝術存在六大誤區:一是“看不懂”,二是“抽象畫是亂畫的”,三是“抽象畫太簡單,兒童都會畫”,四是“抽象畫家是畫不好具象畫才去畫抽象畫的”,五是“抽象藝術已經過時了”,六是“抽象藝術分辨不出好壞”。
李:人們對抽象藝術的敬而遠之,其原因也許就在于對藝術形式語言的陌生。其實任何藝術,都有一個從認識到接觸再到理解和欣賞的過程。在突然面對一個陌生的藝術樣式時,觀眾難免會產生誤解。這很正常。
袁;任何藝術都應該有個審美標準,抽象藝術的審美標準已經形成了嗎?
許:每個畫家的心目中都有一個自己的審美標準,甚至觀眾也有。只不過因為文化不同,標準也不同。缺少溝通,也沒有共識。現在對抽象藝術的認識有點像盲人摸象,有的人摸到是象牙,有的人摸到是象腿,有的人摸到是象的尾巴,各說各的。而整體認識抽象藝術卻非常不夠。“抽象藝術的價值標準”是我的重點研究課題,中國抽象藝術首先必須解決歷史淵源、文化認同和教育普及。當今全國有1500所藝術院校,卻沒有一本關于抽象藝術的教材,也沒有一個專門的研究機構和專職人員,如此巨大的文化缺口,僅讓幾個畫家和市場來推進,力量太單薄。必須有強大的文化戰略和理論儲備,讓這個被認為是外來的藝術在本民族歷史和文化中找到根脈,真正解決抽象藝術的“戶口”問題。
趙:在西方美術學院里,學生進入美院后,教師就以抽象作為訓練繪畫的基礎,只有經過訓練之后才能進行抽象畫創作。對一幅山水畫,一個觀眾看到山,可以從文學的角度來描述山的好壞,至于其中的筆墨意境他不懂沒關系,但抽象畫沒有具體的形狀,觀眾感到有壓力,說看不懂。學生也經常會這樣問,我就啟發他,你聽過音樂嗎?看抽象畫好比聽音樂一樣,需要調動自己的感覺。
許:和欣賞音樂一樣去欣賞抽象畫,這是一個經典的解釋,理論是沒有錯。但要讓一個人從聽覺審美轉到視覺審美并不容易,還是要從抽象藝術本體理論來深入淺出地啟發觀眾和學生。事實上,抽象藝術理論完全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袁:還是要講技法,否則就有點“玄”。
王:這樣談好像不可能一下子解決問題,需要一本教材來講清楚。其實畫畫的人眼晴一看就能分清好壞高低,這也是要訓練的,比較復雜,比方說我對這幅畫很欣賞,我要把對這幅畫的審美的快樂說出來給沒有經驗的人聽,有時候也很難,這其實是我們的一種責任。
李:藝術是發掘人內心的內在真實情感的一種需求,這種愿望是基于一個生命個體對世界感知到一部分東西以后,希望傳遞給別人、自我確認。
趙:是的,我有一次陪北方一位朋友看上海滑稽戲,我笑死了,北方人在一旁問他們在說什么,我耐心地解釋給他聽,但他卻沒有反應。
王:對這東西的理解,有一本書要比沒有一本書要好。但藝術不是數理化,有些奧妙是寫不出來的。
許:細微的藝術審美是難以傳達的,但是在審美和技巧方向上,還是可以引導的。比方講標準,其中有創造性、審美性、技巧性。創造性重要的是原創,審美重要的是色彩、空間和點線面結構,技巧重要的是獨特的、不可復制的。抽象藝術必須有標準,如果沒有標準,就可能魚龍混雜。我舉兩個例子:英國男孩弗萊迪·林斯基只有兩歲,但當他用番茄醬和顏料隨手涂抹的“畫作”被母親放在著名的網站上展出后,竟然在英國藝術界引發轟動,一些不知情的評論家甚至將他與大師提香相提并論,而一家柏林畫廊還慕名邀請他舉辦個人畫展!但得知被一名兩歲兒童涮了之后,全都感到無地自容。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就是因為沒有樹立藝術價值標準。我的標準中有藝術家資歷這一欄,就會避免發生以上的誤判。另外動物猩猩也會畫畫,但是猩猩的繪畫是簡單的,偶發的,重復的,但是不要以為猩猩會畫抽象畫,就是抽象畫家了,現在抽象畫領域確實有“猩猩畫派”,需要正本清源。

王:猩猩是不知道好壞的,所以,盡管它也會畫,但是絕不可稱為好的抽象畫。
許:現在許多濫竽充數的抽象畫家也不知道好壞。明明是“猩猩畫派”,還自以為抽象畫就是這樣的。
王:我到金山農民畫家那里去,有的金山農民畫家心里不服氣,說你們一直說我們的畫好,但是我們在藝術上始終沒有地位,不能參加美協、沒有你們藝術家風光。其實很多農民畫家是“不知道好壞”的,是在輔導員、院長在指導要怎樣畫,毛病就在這里。畢加索畫過黑人木雕,是大師,但黑人雕刻者卻成不了大師。
眾:笑。
袁:我們再談另外一個問題,抽象藝術家的功能發生了變化,不是為某個高級社會階層服務,而往往是為了表達自己,這樣的狀態在目前是缺少磁場的,抽象藝術與中國現在社會的發展有什么關系?
許:一個理性社會在它的初級階段,更多的考慮是國計民生,是溫飽。政府要運作,要安定和發展,企業要利潤,老百姓要拿工資,在這個循環體系里重要的是物質財富。對國家文化來說是為這個體系服務的,因此具象藝術容易和社會當前利益掛鉤,因此也會較多得到關注。但是抽象藝術是純粹藝術,在社會初級階段,精神享受這塊是忽略的。中國社會未來走向和諧社會,抽象藝術就會受到重視。
趙:所以我們看到,第一代爆發戶大都是用耳朵來辨別藝術品的好壞,他們關心的不是藝術品的好壞,而是藝術品的保值與增值。是聽畫家名氣和市場名氣決定買賣的。等到第二代——他的后代,通過接受教育,就會自信地用自己的眼光來挑選藝術品,才可能進入到審美和收藏階段。
許:藝術與社會問題比較接近時會比較旺,比如當代藝術,因為關心環保、關心民生、關心腐敗,用藝術的方式反應社會問題,往往老百姓就關心,主流媒體也會重視,國外對中國有企圖的勢力就比較高興,這里反映了一個利益。而抽象藝術基本上與這些沒有關系。它最大的樂趣就是王老師講的,當看到一幅抽象畫非常美時,他只想傳遞這種情緒的目的。
王、李:傳遞美感,傳遞和美感溶為一體的生命精神,也是藝術家的責任。
許:所以我在寫書,做一些文本工作,為自己人生搭一個臺階,盡管抽象藝術的精髓是妙不可言的,但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審美還是可以用語言描繪出來。這就是抽象藝術的知識,需要普及并且成為人們的潛意識,成為人在審美時的條件反射。簡單說,看一張抽象畫你覺得舒適、好看、喜歡就行了。好看卻一定要講出個所以然,就必須懂理論。
王:往往一般人看畫,都有預先設定,比如在山水畫中要看到一棵樹,突然之間這張畫里沒有樹就看不懂了。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一門“外語“,要訓練的。
趙:藝術門類隔行如隔山。看慣了具象藝術的人看抽象藝術是困難的。所以春晚對趙本山很合算,東北話接近普通話,如果孫中山那時以一票之差定廣東話為國語,那北方人要吃大虧了。我覺得抽象藝術有點暗淡。因為太學術、太精英、太小圈子了。
王:我們在這個小眾中間其實也很高興。德民講得對,要有一定時間。現在時間還沒有到。
袁:改革開放三十年,上海抽象藝術發展到現在也有二三十年了。
趙:王老師、周長江、余友涵、李山等文革時都是畫具象畫的。我在85年轉到畫抽象畫,開始學的都是趙無極,覺得這東西太好了,后來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
王:美院出來的,都是從具象開始的,慢慢感覺到抽象的審美。而許德民不是畫畫出生,是怎么一開始就知道抽象畫的好壞的?
許:我從小也畫過素描、寫生,從具象開始進入美術的。90年出來第一本畫冊《現代幻想畫》,也是具象的。認識抽象畫也是直接在國門打開后開始的,受西方抽象畫的影響。
袁:這時候的畫風可能與你寫詩有關。
許:所謂功夫在詩外,畫畫也是這樣。文學與藝術是一樣的。像我這樣不是通過美院而從事繪畫的人,完全是靠自己的愛好和信念支撐的。但是在中國習慣上認為非得經歷美院學習才能成為畫家。而在國外自學成材或者半路出家的畫家比比皆是。因為繪畫是生命體驗,只要需要,隨時可以進入。當代藝術很多新的繪畫觀念和圖式都是我們美院教育無法提供的。昨天讀了一本新媒體藝術的書,看了讓我冒汗。我在思考新媒體出現之后,我們抽象藝術怎樣與新的藝術共存亡,它給我有什么借鑒。所有傳統藝術、架上繪畫在新媒體藝術面前,都要為之冒汗。
袁:裝置、新媒體視覺、行為藝術出現以后,現在慢慢取代了架上繪畫,面對這種現象,我們持什么觀念,這個問題比較重要。
趙:西方藝術講美學的產生,新鮮的時候才有美學。就要求藝術的絕對新鮮異樣,這張畫如果看第二遍就沒有美學了。
許:這個觀念有偏差。確實是的,新鮮就是創新,創新是藝術首要條件。但是不是每一次創新都是成功的。我們看到的創新還有可能就是不成功的,要經受過時間的考驗的藝術才有價值。當代藝術最大的問題就是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錯把實驗當成功,錯把死亡當誕生。
趙:我有一次花了二十分鐘看了一個影像,先是一根毛,然后是一排,漸漸的織成一條毯子,最后毯子飛走了。我想類似這種東西并不新鮮了,但是他讓我冒汗。現在美術已經到了影像時代,把整個視覺當一張畫來看。
許:觀念藝術是速朽的。真正留下的藝術還是要靠經典來維持。這只是文化的一種多樣性,文化的接力和文化的開拓。當代藝術的形式里面一百個創新的觀念,可能只有一個能留下來,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處變不驚。有的當代藝術家,通過模仿原始的民俗民風,甚至帶有血腥的模仿,其實不能稱為藝術。

趙:杜尚講過,我不相信藝術,只相信藝術家。我開始也不懂這句話。后來懂得了,一個當代藝術家的行為不是偶然的做幾次,而是幾十年做下去。偶然的行為、一次性行為的藝術稱不上是藝術行為,藝術家是經受過時間考驗的。澳大利亞有一個行為藝術家,發生過把自己的一只手臂砍下來,成為獨臂大王。這人叫馬爾帕克。
許:他砍下來的手臂在哪里?
趙:放在福爾馬林里面。網上有許多他的新聞出現。他還裝扮成新娘,不斷地吸引人的眼球。而他的回顧展的大廳里,展出的創意構思,是用繩子扎住一捆一捆放著,看了讓人震撼,所以我相信了杜尚這句話。
許:這印證了藝術家的資歷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因素。藝術家就要不斷地變化。而不相信藝術,只相信藝術家,這句話是有矛盾的。應該講我們不相信藝術家的一件作品,要相信藝術家一生的作品。
趙:這個藝術家出生在藝術世家,從小就認為全世界的人都在畫畫。到后來發現不是這樣,對藝術反感了,又不能解決問題。
袁:藝術家產生了叛逆,是在掙扎,又有所覺悟。我覺得藝術就應該是馬拉松,比賽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多個集團,能跑到終點的都是高手。
許:過去畫家是越老越吃香,它講文化的積淀和堅持。現在有一種現象是越新越時尚,它講創新和發展。兩者最好兼容。我對抽象藝術的遺憾,不是對抽象藝術本身,而是抽象藝術如今的困境。如何讓更多的人,盡早地欣賞到抽象藝術的精妙。現在好比是兩萬五千里長征才剛出發,雪山草地還沒有過呢。所以“遵義會議”明確正確路線很重要。
王:遵義會議毛澤東當時確定了光明前景。而抽象畫你對它的前景如何看?架上繪畫都要被新技術取代,我們怎么辦?我覺得有些現象是一種必然,而不是偶然。如果走老路是沒有出路的。抽象畫五十年代在美國形成高潮。我們于現在的環境再去做抽象藝術,意義在哪里?我們都經歷文革,當時畫大批判覺得蠻好,現在再畫大批判氣場就不對了。所以我在考慮抽象藝術不應該重復走西方走過的路,這不是一個時髦的問題,而是社會藝術發展的必然規律。這兩件事要區分開來,也不能抱著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
許:這里講傳承經典與創新,其實是不矛盾的。
袁:藝術傳承經典其實是個流動的過程,這就是我們要學習創新的精神,而不是模仿一種形式。
王、李磊:比方講,我們一幫人搞抽象藝術,應該與原來的人搞抽象藝術不一樣。
趙:這個現象出來以后,是當代抽象或后現代抽象,這個藝術或許不叫抽象藝術而是一個新名詞了。現在高名潞在北京策劃了一個“意派”。從日本的“物派”借鑒而來。
許:我保留對“意派”的說法。盡管他的出發點是想創造一個屬于中國本土意識的抽象藝術流派或者學說,但是在他策劃的畫展上選擇的畫和他的關于意派的理解是矛盾的。葆康從國外回來,看得多,我講的以不變應萬變的意思是講抽象和具象一樣是永恒的藝術形式,不會被淘汰的。當代藝術中既有具象也有抽象的元素。具象和抽象是人類兩種思維方式、審美方式。抽象藝術在文本上已經清晰就不要輕易造名詞。“意派”和“抽象”比較起來,往往沒有解決自己的藝術風格,就換了一個名字。
趙:日本“物派”有幾個藝術家對中文頗有研究,做了幾件有意思的作品。比如在地上取出一方塊泥土,表面上是抽象的,其實是有含義的。還有,把彈性的皮帶尺拉直,用石頭壓住,都是“物派”的代表作。而“意派”沒有新的觀念和作品。還是原來的抽象畫而已。
許:對“意派”看法我在《中國抽象藝術》第三輯上有過專門的文章論述。抽象藝術正處在一個發展的瓶頸,就是要解決中國抽象藝術的根脈,從這點上,我還是同意高名潞的觀點,但是,不是僅僅改一個名字的問題,而是要真正研究中國抽象藝術的本體理論,這個理論必須和中國美術史、審美史、抽象形式創造史相關聯,在理論上正本清源,在實踐中循序漸進,在文化上建立品牌,尋找到真正屬于中國人的抽象藝術的文化根脈和血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