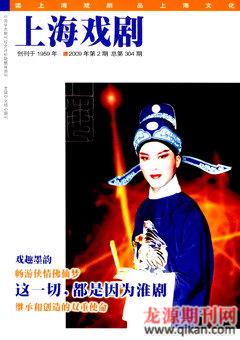戚雅仙與戚小仙
凌 波
越劇表演藝術家戚雅仙的名字,越劇迷無人不知。至于“戚小仙”又是何許人呢?她就是戚雅仙和傅駿的女兒傅幸文。
那是1960年的事了。戚雅仙在北京參加中國文代會時發現有喜,此時的她與其他代表一起受到了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的接見。回滬后,戚雅仙便與傅駿商量,決定給孩子取名傅幸文,意為這個孩子也和母親一起“非常幸福地參加了文代會”。傅幸文從小喜愛戲曲,有人戲稱她是從娘胎里就受到了母親的藝術熏陶。
不過,傅幸文真正女承母業還是以后的事了。母親覺得自己當初學戲實在太苦,為了孩子著想,本不打算讓下一代也吃這份苦。不過最終,戚雅仙還是拗不過愛女——中學畢業后的傅幸文執意報考上海戲曲學校學戲,終于也成了一名專業戲曲演員。
1981年,傅幸文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市虹口越劇團,隨即進入上海戲校越劇班學習。她起初學演的都是越劇骨子老戲,唱腔學的是袁派、傅派等,直到1988年在“戚雅仙表演藝術研討演唱會”中學演戚派折子戲《相思樹·待郎歸》后,才正式改學戚派,并成了戚派藝術的傳人——這也是越劇所有流派創始人的子女當中,唯一一位女承母業者。
傅幸文的表演風范極具母親當年神韻,她扮相秀美、身材勻稱;唱腔婉轉、表演細膩,在觀眾中享有一定聲譽,“戚小仙”之名由此得來。
上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整個戲劇界受到市場大潮的強烈沖擊,開始滑入低谷。在越劇界則掀起了一股出國、轉業的熱潮,此時,傅幸文依然堅守舞臺,先后參加虹口越劇團、靜安越劇團以及上海越劇院的演出,并先后主演越劇電視連續劇《玉蜻蜓》、《金縷曲》,榮獲“飛天獎”、“天安獎”等獎項。2000年,她與母親同赴美國紐約,領取紐約文化局和林肯藝術中心授予戚雅仙的“終生藝術成就獎”。
傅幸文的演藝得到了戚雅仙慈母加嚴師的言傳身教,不僅如此,她在為人處事中得到了母親的良好教益。在長期演出實踐中,她不僅忠實地繼承戚派表演風格,而且注重在保留戚派韻味和內涵的基礎上不斷探索、革新。為讓戚派藝術代代相傳、發揚光大,在其母去世后的六年里,傅幸文多次策劃并參加主演了《雅歌滿江南——戚派演唱會》、《越劇百年·雅歌春韻——戚畢流派演唱會》、《春韻輕音吐芬芳——丁小蛙傳承畢派藝術演唱會》、《雅韻·仙聲——越劇戚派藝術研討暨演出活動》等越劇“戚畢”流派的大型演出;同時參加并主演了《玉堂春》、《王老虎搶親》、《龍鳳花燭》等幾部“戚畢”派保留劇目的音配像的拍攝,還先后出版《玉蜻蜓》、《王老虎搶親》、《金縷曲》、《血緣恩仇》全劇以及《慈母恩師梨園情》、《女承母業——傅幸文傳承戚派藝術專輯》、《劇壇瑰寶——上海優秀傳統表演藝術整理搶救作品精粹》等音像制品,為流派唱腔留下了許多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