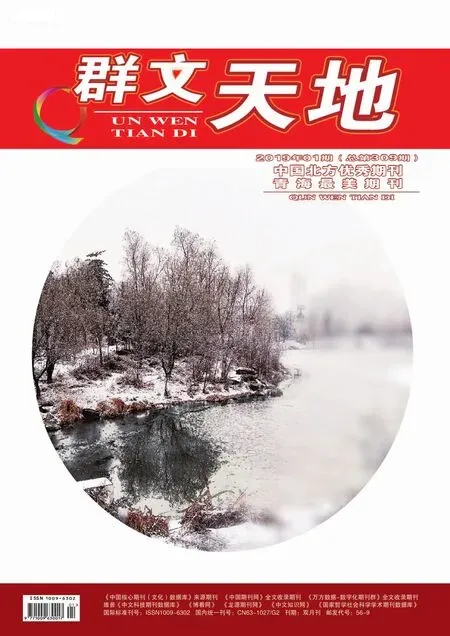清朝對新疆的伯克制度
姚 嵐
十八世紀中葉,清政府統一新疆以后,實行了因俗而治的統治方針,在維吾爾族地區繼續沿用伯克制,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之成為清朝地方官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十九世紀中晚期,隨著社會的發展,伯克制越來越成為維吾爾族地區社會生產發展的桎梏,在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不斷沖擊下,于光緒十三年(1887年)被清朝政府正式廢除。研究清王朝時期的伯克制的產生、發展,直至滅亡的過程,不僅對研究維吾爾族歷史,尤其是研究維吾爾的政治制度史具有必要性,而且對于我們了解清朝政府對維吾爾族地區的民族政策,對于認識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進一步發展、鞏固的歷史進程,也具有重要意義。
一、清政府統一新疆后施行的伯克制度
“伯克制”是我國維吾爾族和中亞一些突厥語系民族歷史上形成的一種官制,伯克一詞是一個古老的突厥詞匯。此字究竟是源于漢語的“伯”,還是源于中古伊朗語bege(神),學者們意見尚不一致。在不同的時期、不同民族中含義不盡相同,在唐代突厥中,“匐”(伯克)一詞主要指特權者或貴族,有時行政長官也用此號,受伊斯蘭教傳播的影響,在中亞地區“伯克”一詞常與阿拉伯語“艾米爾”(Emir)、波斯語“米爾咱”(mirza)混稱,明代以后在新疆及中亞定居民族,如維吾爾族、烏孜別克族中,“伯克”一詞已成為對官吏的泛稱,“回人亦有官職制度,所謂伯克者,即其官也。”“伯克,回語,官長之稱。”“回部官職大小有差伯克統其名也。”十六世紀初,在維吾爾人建立的葉爾羌汗國,伯克是軍事官員的專稱,各地駐軍首領均被統稱為“伯克”,而行政官員則被稱為“阿木奇”。十八世紀時,準噶爾部統治天山南部,伯克和阿奇木逐漸合而為一,出現了“阿奇木伯克”的稱呼,后來,伯克發展為一切官職的泛稱,所有掌職不同的官員,都要在職名后面加上“伯克”二字。伯克制度形成在賽義德王朝時期(即清朝統一新疆之前),伯克制度的形成,“經過十四至十六世紀的發展,至賽義德王朝就基本形成了,十七世紀初臻于完善,伯克制度的形成,主要是蒙古貴族及其后裔的統治,和伊斯蘭教在新疆傳播的結果。至于清朝,只有在業已形成的舊有制度的基礎上才能夠進行改造為其所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平定大小和卓的戰爭開始不久,乾隆即表示:“但擒獲逆裔后,仍令選本處伯克,令其辦事。”清朝政府有選擇地任命一批伯克作為政府官員管理地方行政,按品級給予俸祿,又限制其對土地和燕齊的占有數,其法定數是:三品伯克擁有養廉地1060石籽種地畝,燕齊100人,四品伯克79石籽種地畝,燕齊50人;五品伯克530石籽種地畝,燕齊30人;六品伯克265石籽種地畝,燕齊15人,七品伯克159石籽種地畝,燕齊8人。自乾隆二十四年七月至二十五年十二月清朝政府在調查維吾爾族地區存在的伯克稱名及其職掌的同時,陸續任命了阿克蘇、烏什、庫車、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今莎車)、喀喇沙爾(今焉耆)等三十一個地區大小二百六十余名各級伯克,使其從事當地行政、司法、田賦、稅務、治安等各項民政事務。爾后,清朝政府又以喀什噶爾為參贊大臣駐節之所,節制南疆各城,其余諸城大者又設辦事大臣,小者設領隊大臣,統歸伊犁將軍管轄。至二十七(1762年),清朝政府基本確立了對維吾爾族地區的統治形式。
二、清政府對伯克制度的改革
清王朝對伯克制度并不是完全按照舊有存在形式進行使用,而是在“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基礎上予以改造,使其成為適合清王朝大一統體制下完備官職制度,關于清王朝對伯克制的改造,《回疆志》《西域同文志》《西域圖志》《平定準噶爾方略》諸書記載較多,其主要內容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廢除伯克世襲制度
在葉爾羌汗國時期,由于蒙古貴族主要采用封建采邑制剝削方式,所以伯克制是世襲的,在清朝統一新疆時,南疆地區基本上由幾家豪門望族把持著政權,他們互相勾結,互相支持,共同維護著本階級的利益,地方機構世襲制的存在不利于中央集權的統治。嘉慶十九年清政府頒定的《回疆則例》明確規定伯定不準世襲,以法律的形式對這一禁令作了規定。清王朝對伯克選任標準強調對清政府的效忠態度,在統一過程當中有軍功者,接受清政府分封爵職時將優先予以特別的政治待遇。對伯克世襲制度的廢除,使維吾爾族的伯克在形式上變成了與內地省府州縣相同的流官,消弱了伯克們舊有的權勢,有利于清政府對這一地區統治的加強。
(二)伯克任職實行回避制度
伯克制作為清朝統一新疆前維吾爾族舊有的一種統治制度由來以久,伯克們有著深厚的統治基礎,其轄地往往是他們的世襲領地,清朝統一新疆后,為有效地防止伯克勢力尾大不掉局面的出現,對伯克的任命實行了回避制度。伯克回避分為兩類:一是地區回避。《回疆則例》明確規定:“回避三品至五品伯克缺出,由參贊大臣擬定正陪,奏請補放,凡本城阿奇木伯克及各城莊阿奇木、伊什罕伯克,均令回避本處。六品以下伯克缺出,由各該城大臣報參贊,咨部補放,免其送驗,照例無庸回避本處。”實際上,大小伯克在任時都實行回避制度,只不過大伯克必須回避本地區,而小伯克僅在本地區范圍內易地調補,即如那彥成所說:“大伯克回避本成,小伯克回避本莊。”二是親族回避,乾隆三十年,伊犁將軍明瑞建議:“都官伯克(掌管館驛職責)之補宜公,查刻伯克總辦回人差務,最易射利居奇,且有阿奇木等子弟親戚居為利藪,請嗣后該伯克缺出,必與伊沙噶、噶雜納齊、商伯克公同保舉,其阿奇木族姻俱令回避。”要求禁止阿奇木族姻子弟在其任下擔任下擔任可謂之為肥缺的都官伯克。這一規定后來被寫入《回疆則例》,作為永久制度被保留下來。
(三)制定品級,頒發印記,規定養廉措施
清政府乾隆二十六年頒發了阿奇木伯克的圖記,該圖記承襲了以往慣例,按種類標示品級,規定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和闐為四大城;烏什、英吉沙、庫車、辟展為四中城;沙雅爾、賽里木、拜城、庫爾勒、玉古爾、牌租阿巴特、塔什巴里克、哈喇哈什、克勒底雅、玉隴哈什、齊爾拉、塔克、阿斯騰阿拉圖、阿喇古、玉斯騰阿拉圖什、齊爾拉、塔克、阿斯騰阿拉圖什、阿喇古、玉斯騰阿拉圖什、英額奇盤、巴爾楚克、紗爾呼勒、魯克察克、托克三、喀喇和卓、洋赫、克勒品等為二十三小城。圖記的尺寸,“大城圖記分寸,視內地的佐領,中小等城,依次遞減。”清政府設置的伯克品級自三品到七品不等,為了照顧少數民族上層利益,伯克的品級設置高于內地州縣官員。伯克按品級享受規定數量的養廉地,燕齊農民(種地人)和養廉銀。較為優厚的待遇。伯克的俸祿是按品級高低授予土地和種地人體現的。“自三品至七品,各以授地為差”。除土地和種地人以外,清政府還給種地人各級伯克一定的養廉錢。清政府給伯克們制定口級頒發印記,規定養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伯克們舊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解決了他們
的衣食之源,便于爭取和拉攏維吾爾族上層統治者,對于盡快穩定南疆社會秩序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四)實行年班入覲
年班入覲制度是清王朝籠絡邊疆少數民族上層統治者的一個主要措施,規定少數民族上層人士每逢年節來京,朝見皇帝,瞻仰朝廷威儀,參加朝廷的各種活動,借以堅定其效忠朝廷的決心。伯克人覲一直實行到新疆建省后伯克制度的廢除為止。伯克們在年班入覲時沿途進行商業貿易,即帶動了新疆經濟的發展又促進了中央與邊疆的物品和文化的交流,在一定程度打破了南疆地區相對封閉的局面,有利于各民族之間的進一步融合。伯克年班入覲體現了新疆地方對中央政權隸屬關系,又加強了伯克們的政治地位。
三、結束語
清王朝因俗而治的方針政策,用清代學者李兆洛的話說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新疆被重新統一后鑒于南疆的種族、宗教、語言、風俗習慣與內地不同,依其舊俗設阿奇術伯克。中央派遣的駐扎大臣有權監督、過問及至直接參預民政事務,決定伯克的升遷黜陟,對新疆進行間接統治。將新疆納入中央的管理體系,清政府尊重少數民族習慣,繼續使用了各類舊有名稱來設置官員,這實際上是把少數民族地區舊有的社會制度納入了中原王朝的行政體系當中。出于對舊有伯克的籠絡,道光皇帝對伯克們要求留發以示愛戴之誠,只準許阿奇木以下至四品伯克及盡忠有功伯克之子孫蓄發以示尊榮,其余均不準蓄發。清政府統一新疆后對其原有的伯克制度進行改革,各級伯克仍各留其名,各司其事,添裁升降,定品級奏請賞給頂翎,各按地方大小、繁簡、酌給養廉,禁其橫征,頒其鈐印,專其職守,今已嚴如中國官員秩然矣!表面上看,清朝對南疆維吾爾族地區的統治采取的是間接的形式,而在對伯克的諸項政策的限制下,實際上卻有直接的統治效果。清朝對伯克制的改革,鞏固和加強了國家的統一和清朝政權的統治,促進了南疆社會經濟的發展。在政治上由于保持特殊,易于清廷收復和統治,社會文化上由于保存固有的傳統,易于邊疆少數民族的接受和歸順。當時的伯克制度有利于清朝的統治,和國家邊疆的穩定。但是伯克制度的實施也存在自身的弊端。清朝在新疆地區設立伊犁將軍,實行軍府制度,但對于南疆地區,軍府除了對各級伯克的任免事項以外,只管軍政,不理民事,民政事務都由各級伯克治理,再加上中央的監督不力,出現伯克們魚肉百姓的情形。清政府的改革并不能消除廣大農民與伯克們的階級矛盾、中央與以伯克們為代表的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廢除伯克制實行郡縣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