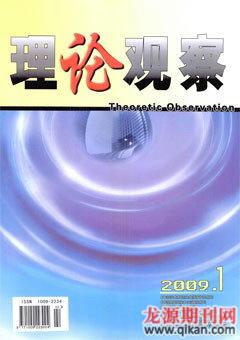現實道德規范與虛擬主體對接的可能
葉豪芳
[摘要]共同的主體決定了現實道德規范與網絡道德溝通的可能,但網絡道德主體獨特的虛擬特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悖謬,要求網絡道德建設的思路從單純的規范論轉向美德論為主、兩者有機結合的方式。
[關鍵詞]現實道德規范;網絡道德規范;虛擬主體;美德
[中圖分類號]B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234(2009)01—0046—02
網絡社會,又稱網絡社區,是指在互聯網構架的網絡空間中產生的一種社會形式,與現實的物理空間相區別。網絡社會實現了人類在現實社會之外尋找另一個棲息之所的愿望。然而,網絡帶給人便利與自由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多道德問題,網絡詐騙、極端言論、侵犯隱私等等。現實社會中的道德問題在網絡社會中非但沒有減少的跡象,反而借助網絡信息技術不斷放大,并且由于網絡的特殊性,其道德問題比現實道德問題更為復雜。
一、網絡道德規范與現實道德規范
當前,將現實道德規范直接移植到網絡社會中之舉動的屢屢失敗表明了網絡社會的特殊性。道德總是與一定的社會結構相適應的,新興的網絡社會呼喚一種新型道德規范的建立和發展。但問題是網絡道德究竟應該新到何種程度?它與現實社會道德規范之間是何種關系?
一些學者認為網絡道德無非是現實道德在互聯網這種技術載體中的具體表現,它和家庭道德、職業道德一樣,不過是不同道德實踐領域之下的道德特殊形態,根本上仍是現實道德的一部分,因而在現實社會中通用的道德原則和價值標準在網絡社會中同樣適用。這種觀點無疑將網絡道德問題簡單化了。職業道德、家庭道德的差別是現實道德主體所承擔的具體角色之間的差別,而網絡道德與現實道德的差別卻是現實與虛擬的差別。網絡社會區別于現實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它的虛擬性,在網絡社會中,性別、年齡、相貌這些在現實社會中用以唯一確定個體的標識統統被隱匿,人們不再是處于具名狀態的“人”。而是借助O、1等數字符號表示的匿名者。虛擬特征使原本屢試不爽的道德運行機制在網絡社會里陷入了自由與秩序的悖謬。
現實社會中,為了共同體的存續,大多數個體都認同秩序的必要性。然而在網絡社會,自由被認為是網絡社會最大的價值,自由與秩序之間的界限應該如何劃分成為一場艱難的拉鋸戰。一方面,網絡的虛擬性提供了自由空間,個體拋卻現實生活中身份、等級、權力等的束縛,暢所欲言,在人人平等的發言中,精英和普羅大眾的界線逐漸消失,普通個體從邊緣回到中心,自由、平等的確得到彰顯。但另一方面,也正因為這種匿名性,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從現實社會的直接狀態變為網絡社會中隨時可以下線的間接狀態,個體擺脫了現實世界中制約性的道德環境,其所需承擔的交往代價、面臨的道德懲罰的風險也就太大降低,從而可以拋卻倫理規范,完全依照意愿行事-進而引起了網絡社會秩序的崩潰。
獨特悖謬的背后是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的道德沖突,它說明網絡道德規范與現實道德規范的差別是客觀存在的,承認這一點是我們構建網絡道德規范的邏輯前提和理論基礎。
與將兩者之差異簡單化相反的是另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網絡社會具有的新特質,例如自由性、虛擬性決定了網絡道德規范和現實道德規范在道德評價標準和獎懲機制方面是截然不同的兩套體系,因而建設網絡倫理要另辟蹊徑。這種觀點無疑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將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割裂開,夸大了兩者的差異。
我們認為,網絡社會和現實社會的差異在于主體,前者虛擬,后者實在,同時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之間聯系的紐帶也在于主體,“虛擬”不是虛無,虛擬背后的支撐者仍然是現實中的人。人——這一現實社會與虛擬社會的共同主體,具有內在的矛盾統一,虛擬與現實的雙重生活正是人自身理想與現實雙重性的外化,而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的統一又是人自我統一的必然要求。
正如沒有脫離現實社會的網絡社會一樣,也沒有脫離既有現實道德規范的網絡道德規范。雖然現實道德規范存在缺陷,但畢竟經過了長期的歷史實踐和檢驗,其價值內核是值得肯定的。因此,網絡道德規范的建設必須在繼承這種合理價值內核的基礎上再結合網絡社會的獨特性而進行,否則將導致道德主體發生分裂和異化。
二、網絡道德主體分析
網絡道德規范與現實道德規范之所以既有差異又能對接的原因在于擁有共同的主體。這是建構網絡道德規范的核心問題,因而有必要對網絡道德主體做進一步的分析。
根據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人格可以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混沌、無意識的,其中充滿生命力和欲望本能,它趨樂避苦,按快樂原則行事,無視社會道德和外在規范。自我是可以意識到的人格部分;平時我們感知到的進行思考、判斷和記憶的部分便是自我,它處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間,遵循現實原則。不斷地調節本我與外部現實之間的矛盾。超我在多數時候也是無意識的,它代表人格中的理想部分,依照道德原則,要求自我對本我欲望的滿足必須限制在現實社會許可的范圍內。
道德主體在現實社會中直接面對的僅是自我,人們在經過從幼年到成人的長期心理積淀后,其自我一般能夠平衡本我與超我的沖突,以現實原則和解道德原則與快樂原則的矛盾,使個體順利地實現社會交往。然而,網絡社會為人們打開了另一個世界,在這里道德規范所指向的對象變成虛擬,個體所需承擔的行為風險降低,于是原本無意識、被壓抑的本我就獲得了松綁,憑借強大的欲望本能在人格各部分的抗衡中占得上風,呈現為越來越顯性的存在。散布謠言、惡意攻擊、窺探隱私就是本我藐視規范,只顧滿足一己私欲所致。悖謬的是,主體在虛擬的網絡社會中追求的不止是原始欲求的滿足,還有英雄或圣人式的理想人格。大量的信息共享、正義的網絡道德聲援正是超我向往道德完美傾向的表現。這樣,現實社會中原本單一,主要表現為自我的個體,在虛擬背景之下呈現出人格的多元化。人格的各個部分從自我顯性在場,本我與超我無意識的狀態成為三者共在的局面,本我與超我的矛盾變得外在化和明顯化。
網絡主體人格的復雜性決定了單純依靠道德規范的增加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道德規范在現實生活中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主要憑借自我溝通個體與外部世界、協調相對無意識的本我與超我。但是,網絡社會不再是自我唱獨角戲的舞臺,本我、超我與自我共在的勢力格局致使道德規范陷入兩難境地:眾多的規范必然會引起本我的強烈反抗,而網絡道德規范即使再完備也不能滿足超我的完美追求。如何破解這種困境?研究者需到規范之外尋求答案。
三、美德論提供的出路
人們習慣于將網絡道德的無序歸咎于網絡道德規范的不足,這其實是現代道德被規范論思維主導的一種反映。無論功利主義、義務論還是正義論,本質上都是某種規范論。規范論背景之下的現代道德強調道德建設的關鍵在于道德規范的設置,它關心“我該如何行動”,以正義、責任作為核
心詞匯,希望通過公平正義的道德規范的設計與人對規范負責任地遵守來維持社會的良好道德秩序。這種道德思維適應了現代社會組織化、制度化的特點,給人們的行為提供了指導,同時底線式的道德要求也給現代人留下一定的自由度。
但是,久而久之,人們發覺自己已被規范論引入了一個陷阱:所謂秩序的獲得是以喪失主體性為代價的,“看似無比自由的個人實際上不過是渾身纏滿規約之網的被動者”。規范論關注的是整體社會秩序而非個體的精神倫理生活,它設想一種“理性人”的道德主體,這些理性人在道德生活中完全按照理性行事,真實獨特的情感、動機等全不在理性人的概念之中。這樣的道德主體無非是理性的代名詞,是一個非人格化、與主體無涉的空概念。在這種學說影響下-主體的主體性逐漸被消解,個體淪為僅為維護社會整體道德秩序而存在的環節,道德也失卻了指向至善和幸福生活的感召力。
規范論的不足在現實社會中已經顯現,網絡社會更是讓這一理論的缺陷暴露無余。道德規范能規定和指導的僅是具體情境之下的道德行動,卻不能指引個體的整體生活方式,在現實生活空間中習慣了接受道德規則約束的個體,一旦進入網絡空間這一規范制定滯后于活動的社會便立刻失去了方向。在那些規范還涉及不到的角落,本我和超我浮出意識的表層與自我共在,爭相向主體提出權力要求,在現實社會中業已十分脆弱的主體性在網絡社會多重“我”之間進一步失落,造成個體人格的混亂。此外,即使在規范覆蓋到的領域,規范的作用也大大降低。規范論倚賴“道德——權力”組合即“違反規范必將面臨懲罰”的方式維護道德的權威。但由于虛擬性,道德規范通常并不能對網絡行為主體進行直接懲戒,道德規范至此又喪失了威懾力。
針對這一困境,近年來復興的美德論不啻為一條出路。規范論對道德機制“規范——權力——個體”的設計遺漏了道德體系中重要的一環即美德,忽視了人的主體性。事實上道德規范只有內化為主體自覺自愿的美德,才能算是完整穩固。在西方倫理學史上。古希臘倫理學的核心就是美德論,這種思想以德性、善、幸福作為關鍵詞,關心“我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問題,認為人生不是一些散亂的行為而是一個整體,在對至善的不懈追求中,美德最終能夠把我們引向幸福。不過自羅馬時期始,律法主義思維風行,再加上中世紀宗教戒律思想占據絕對主導,美德論逐漸被規范論取代。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美德論開始復興,八十年代,麥金太爾進一步豎起了現代美德論的旗幟。
現實社會的道德困境呼喚美德論的復興,網絡社會的出現更是需要美德論這種以主體而為中心的倫理學說的回歸。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中,美德論鼓勵主體依據自己的品格做出主動的道德判斷和選擇,恢復了人作為道德主體的主體性。主體性的重建,還道德立法權于主體,令道德主體從被動服從道德規范變為徹底理解和真誠擁護規范,獲得一種“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內在自由,進而化解了自由與秩序之間的悖謬。此外,美德論還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由主體虛擬帶來的多重人格共在的難題,它以指向幸福的許諾滿足趨樂避苦的本我,以至善的追求撫慰理想的超我,重新統一兩者于自我的平衡之中,保持了個體人格的完整,恢復了這一道德規范與主體對接通道的暢通。
由此可見,實現網絡道德規范與虛擬主體對接的可能,不僅需要規范朝著尊重主體性的方向完善,更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培養道德主體的美德。具體的途徑與方法留待實踐中摸索和總結,但毫無疑問,以美德論思想為主,有機統一規范論與美德論,是現實道德規范合理轉換為網絡道德規范并與虛擬主體對接的合理理論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