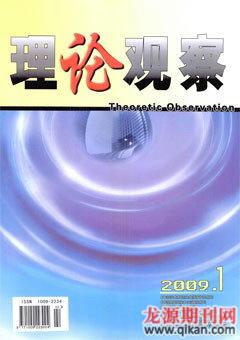嵌入性的符號消費:為消費文化的神話去魅
吳 垠
[摘要]隨著人類社會由匱乏走向豐裕,消費正日益被推向社會經濟活動的中心,并逐漸形成了消費主義化的消費文化。有關消費主義的定義,鮑德里亞和布迪厄的論述各有其被特的視角,也有其不可逾越的缺陷。有格蘭諾維特的嵌入性理論卻給了我們啟發,符號消費往往是嵌入于特定的場域之中的,而不應簡單地將一種消費文化作為階級的標志。
[關鍵詞]結構性生產過剩;符號價值;區隔;嵌入性
[中圖分類號]G1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234(2009)01—0050—02
一、消費時代的到來:一種新的神話
隨著人類社會由匱乏走向豐裕,我們正日益走向一個以消費為中心的時代。曾幾何時,消費還被視為一種“瘋狂、精神錯亂、本能的官能障礙”,因為它使得人們焚毀儲備物資,并通過非理性之舉秧及生存條件。(鮑德里亞,2001,25)。然而,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到工業化大生產的時代,特別是由于福特主義和泰羅制的推行使工業生產的效率迅速提高,商品極大豐富,乃至形成結構性生產過剩,潛在的無限生產力與產品銷售之間的矛盾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這樣,原先浪費損耗、過度鋪張的文化觀念也逐漸為人們所偷換,張揚消費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桑巴特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一書中就曾指出:“在很多情況下,為資本主義打開大門,并使之滲透到各行各業的,恰恰就是消費的增長。奢侈品消費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工業生產的組織:”(桑巴特,2000:212)事實上,生產和消費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雙生子,對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缺一不可的。貝爾筆下“白天是清教徒,晚上是花花公子”的所謂的資本主義的文化悖論實際上正是資本主義生產倫理實現自身封閉回路的必然結果。消費走到歷史的前臺,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另一方面也受到后現代主義文化的影響。由于文藝復興以來具有絕對主題價值的“人”在后現代時期的缺席,于是“個性化”填補了這個缺席的主體“人”的地位,并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在個體的狹窄空間中不斷播撒非主體意識,促成了“跟著欲望走”的消費主義傾向的形成。(王岳川,2004:36)此外,分期付款等新的消費方式的出現進一步刺激了人們的消費欲望,打破了節儉禁欲的消費觀念,而超前消費和一擲萬金成為時代精神的表征。消費社會的運作結構將人們漫無邊際的欲望投射到具體消費上去,將社會身份同消費品結合起來,消費構成一個欲望滿足的對象系統,成為建構商品符碼和符號信仰的過程。消費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新的神話。
二、符號消費:被操縱的意義建構
費瑟斯通指出:“對于事物商品及其生產、交換與消費,需要放在一個文化母體中加以理解。”(費瑟斯通,2000:123)當代消費文化產生的經濟背景決定了消費不再是個人的自發性行為,更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被操縱的行為;同時,當代消費文化產生的文化背景決定了消費已不僅僅是一種物質欲望的滿足,更成為一種承載著意義的符號行為。在這方面,法國后現代思想家鮑德里亞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特別是他關于“商品——符號”理論的闡述。鮑德里亞將消費定義為“一種操縱符號的系統性行為”(鮑德里亞,2001:120),也就是說,消費不僅是物質層面上的實踐活動,還是出于各種目的和需要對符號象征物進行操縱的行為。鮑氏認為“物品要成為消費的對象,就必須成為符號。”他強調消費社會中對商品的消費不能僅理解為對使用價值、實物價值的消費,而應主要看作是對“記號的消費”。制度經濟學大師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提及的“炫耀性消費”就提供了貴族符號消費的一個經典的例子。所謂的“炫耀性消費”,是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些社會“有閑階級”,通過“明顯有阿”和“明顯消費”這兩種都帶有浪費因素的方式,來滿足其自尊心,贏得榮譽和他人的尊敬,進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凡勃倫,2004:23)在這兩種情況下,消費不僅是因為它們有用,反而是在無用之中顯示出其有用性,這種具有體現社會地位等級意義的消費即鮑德里亞所謂的“符號消費”。如果說,在20世紀初凡勃倫所說的“炫耀性消費”還僅僅存在與社會的上層階級中間,那么,在鮑德里亞看來,今天符號價值的消費已構成了社會所有成員之間相互聯系的基礎和紐帶。
鮑德里亞認為:“人類沒有特定的、基本的或實際的需求,所有的需求都是社會制造的。”(盧瑞,2003:63)在消費社會中,人的天性、自然需求被普遍重組為一種符號系統,人的需要也是受到符號區分邏輯支配的。如果將消費社會理解為建立在個人需要的滿足這一基礎上,那么,消費社會對所有人來說都成為一個普遍價值體系,它向人們允諾對商品的追求能帶來最大的幸福。純粹的需要理論以及由此而來的消費理論,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創造出的另一個神話。鮑德里亞反對將需要的滿足自然化,他認為,在“自然需要”的背后,正式運行的恰恰是一種政治秩序和權力系統。消費的過程就是在平等和民主的幻覺下發生的社會身份區分與權力區分的過程。如果每個個體都把具有差別的社會利益當作絕對的利益來體驗,就察覺不到結構的限制,而起決定作用的正是這種相對性的制約,因為參照它,差別的記錄就永遠不會終結。這一點只有放棄個人滿足的邏輯,并注重社會區分的邏輯時才能夠弄清楚,(鮑德里亞,2004:49)
三、文化區隔:消費品位與社會空間
鮑德里亞對消費的符號本質的揭示可謂是入木三分,但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玄想式的哲學思辨,未能對消費的具體社會實踐給予充分的重視。盡管他指出了符號消費是一種社會區分的邏輯,但未能就符號功能與這種社會區分邏輯之間的關系進行具體研究。在這一點上,布迪厄的“文化區隔”理論對鮑德里亞的符號消費理論有很好的補充作用。
布迪厄用具體的社會實踐來作為連接主觀存在與社會結構、連接符號體系與社會空間的重要橋梁。其“區隔理論”所揭示出的一點是人們在日常消費中的文化時間,從飲食、服飾、身體直至音樂、繪畫、文學等的鑒賞趣味,都表現和證明了行動者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和等級。(羅鋼,2003:39)對布迪厄來說,在文化商品中的品位是一種階級標志,置身于社會場域中的行動者的慣習是在文化中獲取的,是培養教育的產物,文化中存在的等級與獲取文化的方式銘刻在消費文化的方式中。所謂的鑒賞趣味的區分體系和社會空間的區分體系在結構上是同源的,在文化符號領域和社會空間之間存在著一種結構性的對應。
時下一本關于生活品位的暢銷書,英文原名為《CLASS,中文版譯作《格調》,書中詳盡描述了消費品位與社會地位之間的微妙關系:“消費選擇、休閑方式都是社會地位的陷阱。你喜歡喝什么飲料。看什么電視節目,抑或根本沒有電視,讀什么雜志,《紐約人》、《國家地理》還是《國民探密者》,怎樣度假休閑,喜歡什么運動,網球還是保齡球。
去哪兒旅行,如何旅行以及家里的小擺設等等,都會確鑿地暴露出人的社會層次。”(福塞爾,2002:3)作者將“格調”作為“精確的社會指南”,簡直是布迪厄“區隔理論”的“通俗版本”。
四、嵌入性的視角:一種更精確的觀察
布迪厄將消費品位、消費傾向與消費者社會地位等級完全相對應是過于絕對的,這一理論中的消費者有“過度社會化”之嫌,它忽略了當下個人所處的具體的社會結構的影響。根據格蘭諾維特的嵌入性理論,人的消費行動并不是脫離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原子式進行的,而是嵌入于具體的、當下的社會結構之中的。在實踐層面上,布迪厄所強調的消費的“地位區隔性”并不是一種外在的事實,而是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用布迪厄的話來講,就是在特定的場域中,人們為尋求群體認同以及場域中的更高地位而互動形成的產物。不同的消費方式并不是簡單地由人的社會地位等級決定的,而更多受到消費者所處的特定場域的游戲規則的影響。同一個社會階層可能包含有不同的場域,比如“中產階級”中就包含有“白領職員”、“經理人員”、“知識分子”等等不同的場域,顯然在這些不同的場域中存在著受不同價值觀和評判標準支配而有所不同的消費方式和消費理念,因而其消費行動的符號意義也不盡相同。所以說,符號消費往往是嵌入于特定的場域之中的,而不應簡單地將一種消費文化作為某一階級的標志。這是嵌入性視角給我們考察消費文化的一點啟發。
五、消費神話的去魅:消費自由的欺騙性
在消費主義主導的消費文化下,更多地占有、更多地消費成為消費社會中虛假的人生指南,甚至消費活動本身也成為人獲得自由的精神假象。費瑟斯通在《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一書中甚至將后現代消費文化視為促使大眾文化與高雅文化分野的消費功能民主化過程。然而。消費真的是自由與民主的嗎?事實上,消費者的選擇更多受到生產者的符號操縱,而“生產和消費是出自同樣一個對生產力進行再生產并對其進行控制的巨大邏輯程式。”(鮑德里亞,2001:74)
消費主義向人們允諾一種幸福的普遍性:幸福生活就是更多地購物與消費,消費成為幸福生活的現世寫照。同時,人們被一種虛假的自我平衡——崇尚同一時裝、觀看同一電視節目、去同一家俱樂部等所迷惑,這本身就已經是用商品消費與符碼標志來替代對真正不平等問題進行邏輯的和社會學的分析。所有商品都有價格的標簽,這些標簽選擇了潛在的消費人群,它們沒有直接決定消費者的最終決策,這些決策是未定的。但是,它們在現實和可能之間劃了一條界限,一條消費者無法逾越的界限。(盧瑞,2003;4)在市場推銷和宣傳的機會平等的外表后面,隱藏著消費者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
在這里,我們無意要對消費主義化的消費文化進行某種道德的批判,而只是通過客觀地揭示消費所嵌入的社會結構,喚醒沉睡在消費神話中的人們,使其至少能認識到結構的存在,實現在消費上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