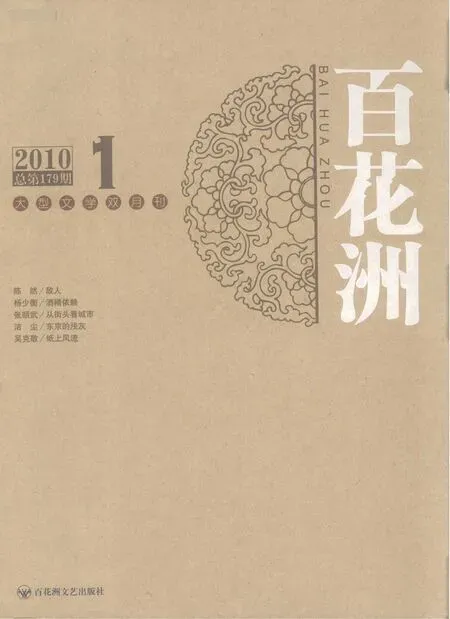零年代
鐘求是
一
那個晚上天空挺調皮,本來好好的,一時興起竟飄起雨絲。飄一陣兒,又不動聲色地收住。趙伏文應對不力,只好夾著一把多余的雨傘,隨同事老克去瞄人。瞄人即相親,即無緣無故去看一張陌生的臉。老克說:“這回瞄的是一位小學教師,教音樂的,一聽就不是粗糙的人兒。”老克又說:“她有一個不錯的名字叫林心。”趙伏文嗯嗯應著,腦子里擋不住地走出一位扎小辮子的白皮膚姑娘。
見面擱在一家茶室的包廂。趙伏文、老克先到,點了綠茶瓜子候著。不很久,一嫩一老兩位女人進來了。嫩的是小學教師,老的是她母親。老克與那母親顯然有些熟,一邊打著招呼,一邊順勢把趙伏文介紹出去。趙伏文想不到女兒母親一塊兒見,腦子有些懵。她們沖他點點頭,他也沖她們點點頭,卻不說話。他只在心里對自己說:她不扎辮子,皮膚也不白,不是想象中的樣子嘛。老克為了托起氣氛,不停地跟母親搭些虛話,內容七曲八拐的。那母親一邊應著話,一邊拿眼睛去瞧趙伏文。趙伏文不愿意接她的目光,就勾了腦袋吃瓜子。吃了一會兒,自己都覺得不好,便抬頭去瞄小學教師。此時小學教師也靜著臉不言語,眼睛蒙蒙眬眬的。不過趙伏文注意到,她的下巴有一顆黑痣,小而生動,把一張臉弄活了。趙伏文想:沖著這顆黑痣,我該與你聊聊話了。趙伏文又想:可你帶著母親來,我只好嚴肅了。
見面持續了二十分鐘,便在半生不熟的氣氛中劇終。母女倆走后,老克要趕一個飯局的尾巴,也匆匆離去。趙伏文一個人坐在那里,慢慢嗑著瓜子,把一壺茶水喝盡。他想:這茶水的口感還可以。
第二天上午趙伏文剛到單位,便被老克堵住,問昨晚上的觀后感。趙伏文說:“沒看明白,只瞧見一顆黑痣呢。”老克說:“不說細節,我要的是綜合評價。”趙伏文嘿嘿一笑說:“你說那么大的人了,還得母親領著。”老克說:“看來你不滿意。”趙伏文說:“這只是初步意見。”老克怒了說:“你小子還想找機會弄進一步意見?”趙伏文淡了臉說:“不用說,在她們眼里我也不及格。”老克說:“那母親遞來話兒,說不喜歡一晚上不說一句話的人。”趙伏文說:“什么一晚上,也就是二十分鐘。”老克說:“你瞧瞧我,二十分鐘里說了多少話。”趙伏文點點頭說:“你的確說了不少廢話。”老克說:“瞄女人嘛就得說廢話。”趙伏文說:“可一下子來了兩個女人,我瞄不準呢。”
趙伏文話說得淡,是因為心里真的無所謂。對他來說,這種見面不是一回兩回了,已勾不起大的興致。當初剛到單位上班,他曾排斥此類瞄人方式,后來經不住別人的攛掇,竟松了口。口子一松,便不容易剎住。隔一些時間,老克或其他什么人就會掏出一個女人讓他去捉拿。他們說:“拿住了是好事,拿不住當一回練習。”他們又說:“別看這些姑娘身子單薄,她們的家底豐滿著呢。”然后,他們還會理直氣壯地說:“你小子在這兒孤零零的像顆釘子,我們不關心你誰關心你!”
趙伏文在這個城市沒有族親,稱得起一顆孤零零的釘子。他的老家在五百公里之外的一個城市,大學畢業后僥幸變成吃官飯的人,被丟到這個城市里。這個城市比老家城市人口多一些,名頭響一些,父母就認為兒子上了臺階,好歹有了出息。但趙伏文知道,自己遠未喜歡上這個城市。日語似的古怪方言,無處不在的商品氣味,華麗而粗俗的民風,都讓他覺得自己是這塊生活地的局外人。
在單位,趙伏文也不歡實。他是學中文的,又喚為伏文,便擺放在辦公室弄文字。單位其實不大,名號也有些冷僻,叫宗教局。局里幾十號人,管著全市寺廟教堂什么的。本來都是些虛靜超脫的事,落到公文上,變成了官臉煩事,加上年頭年尾的八股文字,能把人的身心煮干燥了。許多時候,他弄一份“初步意見”交給老克,老克在他的稿子上添刪幾個字,形成“進一步意見”送領導閱處。開始趙伏文實在些,后來便應景了,甚至耍些冷幽默。一次他把周作人的一段話取來,引為趙樸初的訓言,結果不僅未被領導識破,還收到一句表揚,說引用恰當。
只有周末不一樣。周末上午,趙伏文喜歡賴在自己小屋的小床上。陽光從窗簾上方的空隙跳進來,在他臉上形成一塊光斑。他半瞇眼睛,守著這塊光斑。過了一些時間,等光斑悄悄離開了,他才懶懶地起床,懶懶地洗刷,然后出門去吃推遲的早餐。吃過早餐,一天的時間還太多,就上街去看場電影,或逛逛書店。有時路過街口天橋,他也會上去站一會兒,看街道中間擠來擠去的車輛們,看街道兩旁來來往往的男女們。它們和他們都顯得騷動。似乎為了證明這一點,街頭矗著一塊聲音分貝屏,上面的數字在跳來跳去。趙伏文覺得,這個城市挺鬧的。
一個周六上午,趙伏文閑得沒事做,便去了電影院。電影院放著好幾部片子,趙伏文選擇了一部情愛國產片。進去坐下時,大廳已經暗黑了,銀幕上出現了一個小村,村子很美,有一口水井和一所小學。學生們在男教師的引領下大聲朗讀。后來一位漂亮村姑愛上了男教師,當得知男教師被強行帶走時,她雙手捧了一碗餃子順著山坡追他。山坡上都是花兒,花一樣的村姑跑在滿山的花中,她喘著氣,臉上有焦急,還有水一般的柔情。
電影放完了。片尾音樂還在響著,大廳的燈光已經亮起。也許是早場的原因,偌大的放映廳竟只有兩位看客。趙伏文站起身,另一位看客也站起身。趙伏文一邊扭頭看著銀幕,一邊慢慢往外走。另一位看客也一邊看著銀幕,一邊慢慢往外走。趙伏文不經意瞥一眼那看客,是一位姑娘,還有點眼熟。再定定睛,竟看到下巴的一粒黑痣——那是屬于小學教師的一粒黑痣。趙伏文吃了一驚,心中緊急搜索一個名字。他搜到了,叫林心。他猶豫一下,不知該不該打個招呼。這時電影里的柔情氣息支持了他,他叫了一聲林心。
小學教師扭過頭望他,愣了幾秒鐘,醒悟了。她說:“是你呀。”趙伏文說:“沒想到這兒遇見你,你也喜歡白天看電影?”小學教師說:“電影院里,白天也是晚上。”趙伏文說:“這場電影,原來是咱們倆的專場。”小學教師輕笑一下。
兩個人走出放映廳,眼睛被日光撞得有些晃。趙伏文抬手罩一罩眼,要跟小學教師說話,話未出口猛地打住,因為小學教師已走出去幾米遠。顯然,她沒有與他繼續搭話的打算。趙伏文轉身走向公交車站。他要搭車回去。
公交車來了,趙伏文跳上去。正是繁華路段,車子開得很慢,走走停停的。走的時候,便趕過路邊的行人。停的時候,又被路邊的行人超過。趙伏文突然瞧見,那小學教師走在人行道上。此時他才注意到,她穿一件淡藍色風衣,頭發瀑在肩上,身子稍顯單薄,腳步竟有些閑。車子很快將小學教師甩下,她不見了。過一會兒,車子遇上紅燈,無奈地剎住。小學教師又出現了,她穿過斑馬線時,步子加快,肩上的頭發在微微飄動。趙伏文心里似乎被那飄動的發絲撩了一下。他想:這小學教師其實有點意思。他又想:我得勸勸自己,應該再跟她聊聊話的。
車子駛過一段路,在一個站頭停下。趙伏文下了車,往回走幾步,等在路邊一棵樹下。他看見那只身影遠遠走來,先是小著,漸漸變大,大成了小學教師。小學教師也看見了他,眼睛眨幾下,臉上生出詫異。趙伏文沖小學教師笑一下。小學教師不知怎么辦好,也讓自己笑了一下。趙伏文說:“到午飯的點了,想請你吃個飯。”小學教師說:“你這是在堵截我?”趙伏文說:“算是吧,但堵截不是綁架。”小學教師說:“我不會跟一個不認識的人去吃飯。”趙伏文說:“那天在茶館,我們已經認識了。”小學教師搖搖頭說:“那次不算。”趙伏文說:“那今天呢?今天我們在一個大廳里待了兩個小時。”小學教師說:“這兩個小時你看的不是我,是銀幕上的那個人兒。”趙伏文說:“接下來你給些時間,我會老是看你。”小學教師紅一下臉說:“你挺無賴的!”趙伏文說:“真的真的,那天茶館里沒看明白,今天要補補課。”小學教師盯了他說:“你準備帶我去什么地方?”趙伏文想一想說:“肯德基吧。”小學教師說:“肯德基我喜歡。”趙伏文嘿嘿笑了。小學教師說:“你笑了,你以為你得手了。”趙伏文收住笑。小學教師說:“可是你錯了。”說著身子一晃,繞過趙伏文,形成一只背影。這背影越來越遠,雜在行人中。
趙伏文找老克扯淡,東一榔頭西一棒的。老克說你繞什么道!不就是想讓我供點兒那個林心的情況嗎?趙伏文說你不用供得太多,我就想知道她是哪個學校的。老克說你小子到底盯上她啦?趙伏文咧嘴一笑,不吱聲。老克便不多問,伸長脖子做思考狀,思考了幾秒鐘,說出一個學校的名稱。
下午耗過半截班,趙伏文溜出單位去了林心的學校。學校門口已聚著一幫接孩子的家長,一齊舉了腦袋往里看。趙伏文不準備等在門口,就跟傳達室老頭套近乎,套了沒幾句,老頭扇扇手讓他進去。
趙伏文爬上一幢樓的二樓,找到音樂教室。教室前后兩扇門緊閉著,但有音樂從里邊溢出。趙伏文不敢造次,耐了心候著。
下課鈴聲終于響起,繼而教室的門打開,學生們學著潮水涌出來。趙伏文逆流而進,從后門走入教室。他一眼捉到了林心。林心正站在講臺的鋼琴邊收拾教本,抬頭見著他,愣了一下。趙伏文在椅子上坐下,像一個學生望著講臺上的老師。林心先開了口:“你這人什么意思呀?”趙伏文說:“中午做了個夢,發現把你的臉給忘了,就趕緊過來看看。”林心說:“你這伎倆有點俗。”趙伏文說:“我說的是實話,信不信由你。”林心摸摸自己的臉說:“那你現在好好看一眼吧。”趙伏文點點頭說:“我看著呢。”林心說:“看完了請你離開。”趙伏文把胳臂豎在桌上,說:“我還想舉手問一個問題。”林心說:“你問吧。”趙伏文說:“你教教我,瞄上一個女孩后該怎么追?”林心說:“那得看瞄上怎樣的女孩。”趙伏文說:“我瞄上了眼前的這個女孩。”林心搖搖頭說:“你眼前的女孩還不想混到婚姻里去。”趙伏文:“你說的不對,她已經開始在茶館里物色人了。”林心說:“那是她母親主謀的,不是她的意思。”趙伏文:“她……為什么呀?”林心說:“不為什么,她沒興致。”趙伏文說:“我明白了,這是因為她沒遇上一位恰到好處的人。”林心禁不住笑了:“你以為你是恰到好處的人?”趙伏文說:“我有個預感,兩個喜歡白天看電影的人能夠說到一塊兒。”林心說:“白天看電影,這重要嗎?”趙伏文說:“重要的,看電影也是做夢,愛白日做夢的人,現在已經不多了。”林心說:“我聽你說話,才像是白日做夢哩。”
說過這話,林心拿起教本下了講臺,走到趙伏文跟前。趙伏文望著她,心里忽然有點慌。林心說:“以后不要來了,這教室是學生坐的,你已經不是學生了。”說完徑自出了教室。
但趙伏文沒有聽話。以后每周五上午,他都會去學校一趟,不過不進去,只交給傳達室老頭一只信封。信封里有一張電影票,上面印著第二天上午的放映時間。當然了,還有一張同模樣的電影票裝在他自己兜里。
因為電影票的提醒,周六上午趙伏文不再隨意拖覺了,一到點兒,便緊著腳步出門,坐公交車去電影院。第一次的時候,他不免有些期待,身子擱在座位里,目光卻不知往哪兒擱,一會兒瞧瞧銀幕,一會兒看看左右,把一場電影看得支離破碎。到下一次,他目光仍然渙散,心里已明白形勢。接著往后,他的心思漸漸收住,投放到銀幕上去了。
但趙伏文不準備放棄。每個周五上午,他把送電影票當做一件有趣的事。他覺得有了這張電影票,自己坐在電影院里的心境便不一樣,總存著買下彩票等候開獎的一絲亢奮。伴著這一絲亢奮,他看了一部又一部電影。他對自己說:“在電影院里等人,要比在其他地方等人舒服一些。”
二
趙伏文擬了一份文件交給老克。交完了不走,磨磨蹭蹭的。老克虛看著,不言語,等著他自我抖露。果然趙伏文守不住口,輕著聲音說:“挺難弄的,那小學老師。”頓一頓,又說:“挺冬天的,那小學教師。”老克明白了,說:“想不到你小子真對女孩子動心思了。”趙伏文說:“我遇上一個不好的季節,冬天不是動心思的時候。”老克呵呵笑了,說:“這話凄涼,這話凄涼。”老克用手指捏一捏自己鼻根,說:“這樣吧,下了班你請我,咱們去吃火鍋。”
傍晚下班,倆人去了小四川火鍋城,滿眼是人,根本拿不到座位。撤出來沿著街溜達,找到一家火鍋小店,也是熱氣騰騰,幸好還有一只角落空著。倆人趕緊落座,點了啤酒小菜開吃。吃了幾分鐘,趙伏文要起話頭。老克說:“不忙不忙,先讓我吃一口。”說著取菜蘸了辣料塞進嘴巴,又哈著氣打開。趙伏文懼辣,見他傻傻地挺著嘴巴,忍不住要笑。老克往口中倒進啤酒,把辣氣殺下去,像是舒服了,說:“你不知道,辣透了的嘴巴好說話。”趙伏文說:“這可沒聽說過。”老克說:“你沒聽說過的事多著呢,包括那個林心。”趙伏文說:“你說你說。”老克清清嗓子說:“以前,就是沒混進現在單位之前,我在五交化公司干過。那時我跟王金蘭共事過一段日子……”趙伏文說:“王金蘭是誰呀?”老克說:“就是林心母親。”趙伏文噢了一聲。老克說:“那天一位老同事的兒子婚宴,我去了,恰好跟王金蘭坐在一起。”他頓一頓說:“大概那天婚禮攪動了王金蘭,王金蘭有些傷心,她說養了女兒這么些年,到底沒養熟透。”趙伏文截住話說:“這話什么意思呀?”老克說:“你小子挺警惕的,一句話聽出異樣來了。實話告訴你吧,林心非王金蘭親生,是抱養的。”趙伏文吃了一驚,想一想說:“這也沒什么呀。”老克搖搖頭說:“這就有些不一樣了。”
老克講的不一樣,是指林心的脾性。老克說,林心十多歲時從鄰居碎嘴里得知自己的身世,從此心里就擱上一顆石子。年齡一天天地長著,這石子卻沒法子丟開。其實王金蘭對她挺好,她對王金蘭也不錯,但她對王金蘭掏新名詞,叫單身主義者。王金蘭便不高興,說你怕什么。林心說不是怕是煩。現在談戀愛哪有一次成的,總是介紹來介紹去,她說她煩這個。這話聽起來簡直不算理由,她伸手取來便用了。還有,林心總想知道生父生母是誰,王金蘭哪里肯告訴她。她便跟王金蘭說,我不會離開你,也離不開你,我只見生我的人一面,見過了就畫一個句號。王金蘭說這事早是句號了。林心說,在句號前頭有一個問號,我得跟生我的人要一句話,當初為啥甩下我?這個林心,長得文靜,又教著音樂,該柔順些才對,卻偏偏挺犟。
趙伏文嘆口氣說:“其實林心的想法也不出格,人是有好奇心的,何況對自己的不明來路。”老克說:“那也得看養父養母的顏色。養父養母對你好,又不愿意節外生枝,你應該懂事。”趙伏文說:“那就不動聲色,悄悄去找人。”老克說:“悄悄找了,據說去過巴梨兩次。”趙伏文吃一驚說:“林心的生母在巴黎?”老克說:“不是法國巴黎,是巴梨鎮,嘴巴的巴,梨子的梨。”趙伏文笑了。老克說:“王金蘭知道林心去了巴梨找人,一個勁兒傷心,以后林心就不找了。”老克又說:“其實巴梨不算什么線索,那么大一個鎮子,沒其他提示,找個人簡直是在《新華字典》里找個錯別字。”
老克呷一口酒說:“我知道的都抖出來了,林心也有些栩栩如生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看能不能逮住她。”趙伏文說:“我覺得有趣,她竟是個壓著心事的人。”老克說:“壓著心事說重了,最多一顆小石子。”趙伏文不同意地說:“不小的石子哩。”
趙伏文起了一個念頭,要去一趟巴梨。
巴梨是五十公里外的一個縣城,頗有南方鎮子的姿色。趙伏文公干時去過兩次,只是每次辦完雜事,立即被拽到飯桌上,對鎮子沒攢起太多的印象。
趙伏文抵達巴梨時,已是中午。天陰淡著,輕的風吹過街道。街道兩旁布著許多商店,商店門口走著許多男女。商店們和男女們湊出了喧鬧景象。一切都很尋常,跟其他南方縣城沒啥區別。趙伏文有些茫然。
不過趙伏文的茫然是自取的。他來這兒沒什么目的,只是走走瞧瞧。這走走瞧瞧自然是為著林心。但他到底能為林心做點兒什么?什么也不能。他做不到在《新華字典》里找出錯別字,哪怕發現一點點線索。他只能算是一廂情愿地來嗅嗅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