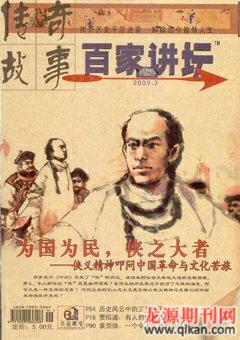獄吏之貴,國家之貴
張 鳴
秦以嚴刑峻法治天下,盡人皆知。但是,怎么個嚴苛法,卻不太清楚。因為秦朝的歷史短,檔案文書又被項羽一把火燒了個干凈,小吏出身的蕭何,也只是將田畝賬冊收了起來。所以,后世人們說秦朝之事,只能含含糊糊,稍一使勁,就說到漢朝了。
漢承秦制,對秦朝的嚴刑峻法,大體上照搬。當年作為亭長的劉邦和縣吏的蕭何,雖然地位卑微,可畢竟屬于法律的執行者,切實操練過。他們被管的時候,固然難受,但是管人之際,也相當威風,相當過癮。當了家之后,昔日的印象還在,“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這種粗疏寬松的約法三章,當然不足以顯帝王之尊、彰帝王之威、過帝王之癮。在叔孫通主持下,秦禮復活了;在蕭何的主持下,秦法也在漢律中復活了。文景之治,推崇黃老,苛法稍懈,但武帝時又勒緊法綱,說是獨尊儒術,其實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直到漢元帝時,儒術才真的在法律中起作用,所以西漢的盛時,盛行的依舊是秦法。
法苛則酷吏多,酷吏多則獄吏牛氣,沒有獄吏的配合,酷吏的威力就要減去一多半。西漢監獄多,僅京城之內,據清末法學家沈家本考證,有案可考的就有26所,名目相當多,犯了哪條,該進哪里,誰也不清楚,托人運動都麻煩。那個年月,按秦法的精神,不管是王公貴族,還是皇親國戚,只要犯了法,或者被人認為犯了法,都得進監獄。原本地位卑微的獄吏,由于時常可以看管這些貴人,自我感覺就無形中被抬高了,難免不威風八面。記得有人曾回憶,說他被打成右派勞教的時候,管教隊長碰到熟人就會把他們中級別最高的人找來無緣無故訓一頓,然后說:看,別看是廳級干部,現在歸我管!古今獄吏,心有靈犀焉。
牛氣的獄吏,對待犯人,肯定要加以折辱。雖說打罵事小,可折辱人事大,那個時候,人,尤其是貴人,對臉皮是很在意的。而獄吏們折辱起來,一來威風,二來過癮,三來可以索賄,要想少受點磨難,拿錢來。管你是誰,進了這里,就歸我管,鐵公雞也得拔毛。絳侯周勃,安劉定漢立過大功,劉邦曾說他死后,安劉氏者必勃也,也確實就是勃也。可就是這種人,一旦被懷疑有謀反之嫌,照樣進監獄,照樣得受獄吏的折磨,出來以后,他感慨道:“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周勃脾氣好,抗折騰,而且見機早,給獄吏塞了錢,不僅免了磨難,而且得以出獄,但有些人則死在獄中。比如周勃的兒子周亞夫、哀帝時的丞相王嘉等,都是在監獄里絕食而死,有些血性漢子為了免受折辱,干脆在下獄之前一死了之。
獄吏折辱這些高官,難道不怕這些人一旦復出,轉過來報復嗎?看來他們不怕。以法治官,以法治民,是當時的“國策”,皇帝喜歡,各級官員也喜歡,個別人就是想報復,在技術上也行不通。因為京城的監獄,都是詔獄,具體管轄的人,直接對皇帝負責,復出后的高官,官再高,也是鐵路警察,管不到這一段。地方的監獄,能管到的,一般都不關押官員,個別關了的,官員出來后也未必會報復。有一個故事很耐人尋味,景帝時梁國內史韓安國坐法抵罪,被關進梁國屬縣蒙縣(今安徽蒙城)的監獄,獄吏田甲按規矩折辱他。韓安國說,死灰就不能復燃了嗎?田甲道:如果復燃,就用尿澆。不久,韓安國果然官復原職,田甲聞風逃走,韓安國對田甲的族人說,如果田甲不來自首,我滅你們宗族。田甲不得已,前來肉袒謝罪,韓安國開了一通尿溺的玩笑之后,卻善遇之,認為田甲可以幫助他治理梁國。看來,獄吏之惡,原本就屬于苛法的一部分,國家通過獄吏對人犯的折磨,強化人們對法的恐懼,哪怕是達官貴人,也需要這種恐懼。就算你負屈含冤,寧可讓人犯受盡折磨,瘐死在監獄里,也不會稍微改善一點監獄的待遇。對于那個時代的司法制度而言,疑犯從有是威懾,監獄的磨難是懲罰,兩者都是讓人恐懼的法寶。過去的法治,就是刑治,有寫在面上的刑,從原來的割鼻子剁腿、五馬分尸、剁成肉醬到打板子、抽荊條、流放、殺頭,還有隱在下面的“刑”,就是獄吏私下來的,據說也是五花八門,《水滸傳》上講的殺威棒、吃黃魚、悶干飯之類的都是。自漢以后,統治無非儒表法里,法家的陰影,從來就沒有從司法中離去,盡管德政喊得山響,為政者操練起來還是想方設法讓人恐懼,確立國家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威嚴。所以,盡管有些朝代,比如明清死刑判決尺度很嚴,非皇帝點頭不行,但在監獄里瘐死者,不知超過判死刑者多少倍。從這個意義上說,獄吏之貴,就是國家之貴。
編輯/吳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