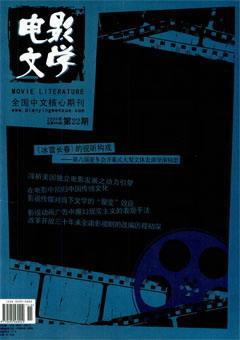論從小說《靈與肉》到電影《牧馬人》的改編藝術
岳小戰
[摘要]眾所周知,世界電影誕生之初,并不存在對文學名著的改編問題。然而,由于后來有聲電影的出現加強了電影的敘事功能和表意功能,使得文學和電影有了共同的敘事單元和表意單元。根據小說《靈與肉》改編的電影《牧馬人》,它既體現了編導者的審美理想,也迎合了觀眾的審美需求;既忠實于原著,又高于原著,充分體現了劇作者高超的改編藝術。
[關鍵詞]小說《靈與內》;電影《牧馬人》;改編藝術
就世界電影100多年的發展來看,電影由最初的街頭雜藝而演變為一種新興的藝術樣式,得益于它對戲劇、文學、美術等眾多傳統藝術的借鑒。在這其中,電影對于文學營養的汲取則是最為突出的,正是由于文學諸多元素的介入,使得電影由原來簡單的情景記錄和影像表現一躍而成為能夠承載復雜的思想蘊涵、展示曲折豐富的人生狀態、表現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等的成熟藝術。
作為世界電影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電影,自“左翼”以來,也都一直在進行著電影對文學名著的改編和轉換。特別是新時期以來,電影對文學的改編更是到了全新的時期,電影劇作家充分汲取了文學的素養,特別是立足于現代和當代的文學作品,從而使電影與文學在這一時期真正做到了優勢互補、相得益彰。文學與電影的這種“親密結合”,使得中國電影開始真正走向世界;同時那些在世界上取得崇高聲譽的影片,又提升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和知名度。新時期以來,那些由小說改編成的電影,像一顆顆璀璨耀眼的明珠,不僅在中國電影史上。而且在世界電影史上也放射出令人奪目的光芒,同時他們在思想和藝術性上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當然,文學和電影始終不是屬于一個藝術范疇里的,它們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美國著名電影理論家普魯斯在《從小說到電影》一書中寫到:“康拉德和格里菲斯所說的‘看見,是兩種不同方式的‘看見。”(康拉德:現代著名小說家,格里菲斯:電影大師)文學作品中的“看見”是通過大腦中的想象來完成的,充滿著可延續性和再創造,在這種“延續”和“創造”中就有了多種可能性。而電影中的“看見”是直接通過視聽感官來完成的,音樂、繪畫和聲音的有機結合使觀眾免去了“想象”,這一過程,它是惟一的和確定的。這種“看見”之間的差別可以說是小說和電影之間最根本的差別。這種差異決定了電影《牧馬人》和《靈與肉》是有區別的,它要求電視劇作家在對小說進行改編時,通過對小說的理解、研究加以詮釋,既來源于原著,又高于原著。
根據著名作家張賢亮的短篇小說《靈與肉》、由著名導演謝晉改編、導演的電影《牧馬人》,令無數觀眾心潮澎湃,熱淚盈眶。從小說到電影的藝術成就充分體現了改編的魅力和導演的精深造詣。影片中鮮明的社會現實背景,曲折的人物性格命運,不倦的人道主義追求,富有哲理的深邃的思想內容,質樸凝重、細膩抒情的獨特影像風格,給觀眾呈現出一部具有浪漫主義情懷的現實主義力作。
在小說《靈與肉》中,作者向讀者講述了一個被錯劃為右派、經歷了二十幾年的磨難后的那份冷靜與良知。人們都說苦難是人生成長的催化劑,但是太多的苦難只能摧毀人作為人的那份最原始的自尊。出身的優越、良好的教育并沒有讓許靈均這個曾經的資產階級少爺擺脫命運的苦難。他被父親遺棄,被錯劃為“右”派,20多年的反復批斗,精神的摧殘,物質的貧乏,讓他竟不敢奢望作為人的人格與尊嚴。他沉默寡言、拼命干活、熱心助人,“老右”的帽子時刻提醒著他,他就要被歷史潭沒了。幸運的是,他的生活中有了“郭子”“老董”“心愛的馬兒”“秀芝”“清清”等,愛讓他又活了過來。幾十年的勞教生活,帶給他的只有歷練,只有不同于一般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所以,在小說中,讀者能體會到的更多的是許靈均對曾經苦難的講述和感悟:對自身感情生活的幸福、對草原的迷戀和鄉親的愛、對明天的美好期待。小說中流暢的敘述充分發揮了文學語言的特長,并且留給讀者巨大的想象空間,傳達給讀者的是一種感覺,一種氣氛,一種淡淡的哀愁、濃濃的深情,一種永不磨滅的堅毅,一種讓人壓抑后的釋然。
作家在小說中向讀者傳達出的是一種浪漫主義情懷。他呈現苦難,但卻不自戀于訴說苦難。他以一個曾經經歷過的過客的身份,以無比開闊的胸襟包容了曾經的苦難,更是以一種難得的浪漫主義豪情笑看苦難,所以他才能夠坦然地放棄家里過億的資產,毅然決然地回到曾經帶給他苦難的大草原。那么在電影改編中,如何做到既要保持原著的精神內核,又要在具體的影像語言中創造出非文學語言所能傳達的嶄新的內容和深刻思想,就成了電影改編的主要任務。
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必須創造出一種能使觀眾共鳴的美感。美感是一部電影頭等重要的,它既體現著編導者的審美理想,也要迎合觀眾的審美欲望。電影《牧馬人》中,這種直觀的情感創造無疑是成功的。
在改編過程中,劇作家運用蒙太奇手法對故事進行新的思考和組織,按照銀幕的美學法則對故事成功地進行了再創造。影片中通過一系列生動感人、充滿生活氣息的畫面和鮮明可見的細節描寫,著力表現了人們對許靈均的關懷、養育之恩和他對祖國、對人民無比深厚的熱愛之情。也正是影片中這些具體可感的生動畫面,才構成了電影的美感。
藝術創作的首要目標是塑造藝術形象。《牧馬人》的創作人員較好地運用了各種造型表現手段,賦予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以美感,愉悅于人。如許靈均那落難知識分子的不修邊幅、不善家務、雖貧苦而不沮喪、越苦難越睿智的形象;秀芝脫土坯子、養雞養鴨養兔、自己給自己家門口栽樹等一系列質樸的行為,充分表現了中國傳統勞動婦女的美好特性和精神面貌。不僅在人物造型和行為上電影給觀眾以直接的美感,而且電影中的人物的語言,也以符合人物身份的語言,準確地展現了人物的內心世界,以達到使人物更飽滿的目的。如影片中父子的對話,一個矜持空虛,一個樸素充實;李秀芝樸實無華的話語與宋慧英白作聰明的看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鄉親們的粗獷真摯與許景由的文雅談吐相映成趣等等,以不同的程度沖擊著觀眾的每根神經,讓電影的美感直觀地動了起來。
電影的美感,不但要直觀,而且還要有情感,從審美的角度講,情感性比直觀性對于一部電影更為重要。在電影《牧馬人》中,編導用真實有力的鏡像語言,給觀眾表達了一份份真摯的情感。許靈均與秀芝的愛情雖不熱烈,但那份相濡以沫的恬淡與幸福是宋慧英這樣的女人永遠不可能想象和擁有的。鄉親們對許靈均的關懷和養育之情,正如影片中那一幅舊門簾,一口舊鋁鍋,兩碗熱干面,對每個觀眾而言,心里都暖洋洋的。這些簡單細節的添加讓當時已經沮喪到極點的許靈均的內心感到了一股溫暖,一種可以慰藉終生的溫暖;還有他結婚時大伙送糧票、布票、飯鍋等等情節,都具體形象地表達了許靈均和鄉親之間的深厚情誼。這種感情不是億萬家產可以比及的。正是在這樣的人民中間,他找到了愛,找到了溫暖,找到了真正的親人,也最終找到了他的人生價值。這些情節的加入也增強了影片的可觀性和說服力。許靈均對祖國的愛、對鄉親
們的愛、對大草原的愛,讓他坦然地放棄億萬資產,重回到大草原,與他的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影片中向人們展示的情感不是單一的,而是豐富多彩的。父子情、夫妻情、鄉鄰情、鄉土情和祖國情,都具有極強的感染力。
一部由小說改編成電影的成功之作,不僅僅要求做到忠實于原著,而且要高于原著。這就要求編導在具體的改編過程中要用具體的影像語言創造出非文學語言所能表達的嶄新內容和深刻思想。影片《牧馬人》在改編過程中,除忠實于原著的情節與場景外,還適當地增加了一些具體的場景,更好地為主題服務。
首先,對許靈均形象的塑造上,為了更突出他高尚的精神情操,并且為了能使觀眾徹底信服他可以拋開億萬資產,而“情愿與他的祖國一道爬這個坡”的價值觀,編導在改編時故意增加了董寬老漢、董大媽、牛鳳英、青年牧工海生等人物形象。小說中,作者只是用抽象的語言說這里的人民給了他很多關心,但是在電影中,最讓人感到溫暖的還是他剛到農場時,作為“右”派的他在政治上受人歧視和排擠的時候,董大媽端來了熱騰騰的面條給他吃,善良質樸的鄉親們并不懂什么“右”派,他們只知道他很可憐,需要幫助。這一簡單細節的添加讓當時已經沮喪到極點的許靈均的內心感到了一股溫暖,一種可以慰藉終生的溫暖。其次,在對許景由的形象塑造上,電影也加入了一些情節,使得這個海外富翁的形象更具人性化。在小說中,他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出現的,如他剛見到兒子時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一切向前看,”“中國人現在也不承認他們是禁欲主義者了”等等,總是給人以盛氣凌人的感覺。在電影中,無論從語言上還是情節上,都做了很多的增加,比如許景由對兒子說:“我這次回來是贖罪的,希望我能夠見見清清,在孩子身上彌補。”還有臨走時送一塊金表給未來的兒媳婦作見面禮,總是感嘆祖國的變化,對故土的深深眷戀和依依不舍,對兒子的無限愧疚和深深歉意,重游母校時偶遇故人的那份由衷的喜悅與感動。電影對這些情節的添加,使人物更加個性化、更加飽滿,也更接近我們正常人的審美心理和審美習慣。另外,電影在對秀芝這個人物的改編上也遵循了編導的人生觀和美學追求,改編者比較注重從各個方面去表現秀芝的樸實、親切、賢惠、勤勞、開朗的性格。同時也增添了一些情節和細節。比如電影中,在許靈均上山牧馬時,秀芝在家里一天天記日記,這個情節形象地揭示了秀芝作為傳統女性對丈夫的那份含蓄的愛。尤其她在日記中寫到“十幾天了,馬兒都想家了,你卻不知道回來”,十分生動地寫出了秀芝想念丈夫又不好意思直說的嬌羞和真摯,既顯示了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也讓觀眾體會到了他們夫妻間的恩愛。還有日記中寫到具體的生活瑣事,也說明了她作為傳統女性的安分守己和對美好生活的熱愛。再者就是她為未見面的公公煮茶葉蛋、買枸杞子的細節也體現了她的溫良和孝順。電影在改編時,注重生活原型和生活細節的合理適當添加。在準確傳達原著的精神內核的同時,又使影片中的人物更加生動、可信、傳神、直觀。此外,小說中寫秀芝的外貌時說道:“她并不漂亮,小小的翹鼻子周圍長著細細的雀斑,一頭黃色的、沒有光澤的頭發……”但在電影改編時,把她寫得很漂亮,通過這樣的改編,更有利于顯示她與許靈均的愛情是純粹的、高尚的,更接近于大眾的觀影期望和審美需求。因為大眾都希望好人有好報,心靈美的人也一定外表美,這也體現了導演和觀眾一致的美好審美理想。
小說《靈與肉》中作家所表達的樂觀浪漫主義情懷其實更客觀有力地襯托出現實生活的苦難帶給他的最終的歷練和力量。電影在改編時“也沒有讓受到創傷的心靈沉湎于過去的痛苦,而是致力于寫人的性格和人的情操,把人物命運與歷史曲折緊密聯系”,讓人感到我們所經歷的苦難是我們祖國的苦難,苦難過后,祖國會更好。從這個意義上講,電影《牧馬人》無疑是一部成功的具有浪漫主義情懷的現實主義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