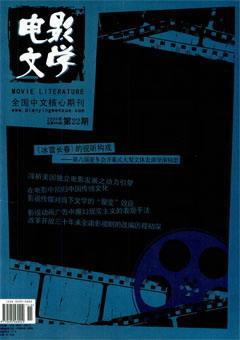試論余華20世紀90年代長篇小說的命運主題
仲滿義
[摘要]不同于其前期小說的冷酷,余華20世紀90年代的兩部長篇小說體現了普通人強烈的生命意識。《活著》中的福貴面對自己親友的逝去,仍然堅定地選擇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中的許三觀以賣血的方式活著,以賣血實現了對家人和人性的責任,以賣血的方式升華了自己的人格。
[關鍵詞]余華;《活著》;生命意識
盡管余華在前期的小說中充分展示了現代人的焦慮感,但他并沒有完全拒絕對人的溫情一面的敘述。無論是懷有良好愿望的十八歲青年(《十八歲出門遠行》)、為救人而死的孫光明(《在細雨中呼喊》),還是故意殺人的馬哲(《河邊的錯誤》)等,都體現了人的良善的一面。對死亡的關注其實只是余華的一種“虛偽的形式”,在這“形式”之下,掩蓋不住的是他對于信仰和價值的渴望,和他對于現實人生的關注和熱愛。
不同于前期小說對死亡的渲染和欣賞,余華后期作品在努力地對抗著死亡的危險。面對死亡,活著是一種最好的進攻,余華小說中的人物讓我們感受到了這一點。這一時期,余華筆下的人物從非人性的幾乎可以說是獸性的殘酷變得有了喜怒哀樂等人生正常的生活狀態,有了愛,有了自尊,有了溫情。而其表現的東西也由人性惡、非理性等轉向了展示人的生存苦難,展示人同命運的略有麻木的生存抗爭,還有一些帶有民間文化氣息的樂觀精神。
一、面對死亡勇敢地活著
對余華創作的關注者來講,相對其前期作品,《活著》的出現令人眼前一亮。這部小說雖同其前期作品一樣也有苦難的敘述,但卻是余華苦難世界中的第一抹樂觀主義曙光。這部小說的關注點是一個人的命運,寫出了“我所了解的一個中國人,也可以說所有的中國人這幾十年是如何‘熬過來的——不是‘活過來的。而是‘熬過來的。”這部小說中,我們雖然直面了與福貴有關的7個人的死亡,但透過小說,我們感覺到的已沒有他前期小說中那種濃烈的死亡氣息,而是作為事件敘述者福貴頑強的生命力。而且他還以自己對活著的特別理解去影響別人,如在“文革”中對春生所講的那番話,雖然春生由于個人的脆弱還是選擇了死亡,但這也更讓我們感覺到福貴對生命的珍視。
余華后期小說與前期小說在形式上有一點相似的是,同樣有關于人物死亡的描述,如《活著》中福貴親人們的死,《許三觀賣血記》中龍根等人的死。但相對于余華前期小說中主人公在面對死亡時所表現出來的冷漠,《活著》更讓我們體會到了人在面對親人死亡時痛苦的情感體驗。老全死時,“我”眼前一黑;有慶慘死,“我”幾乎要和醫生拼命,為怕有病的妻子受不住打擊偷偷地埋了孩子;鳳霞難產而死,“我”“心里疼得蹲在了地上”;聽到二喜出了事,“我馬上就哭了”……歷經苦難,雖然每次面對親人死亡時福貴都表現為極度哀傷,但“死者長已矣,生者長戚戚”,活著的人的路不能為死者所羈絆。于是,在《活著》的結尾我們看到了福貴超然的生活狀態。他福貴自得其樂地想象出幾頭耕牛,并給它們取了自己親人的名字,使自己在假想中和親人們生活在一起,體味到親情的快樂。同時,在和別人講述這一切時,福貴語氣中顯得是那么的波瀾不驚,如那風暴過后的港灣,讓我們感覺到這份平靜內蘊涵的巨大的生命力,這份平靜中體現出的人生的至高境界。
福貴的活著,也許有些孤獨,但他不是一種茍活,借助于耕牛的想象,他讓自己生活于親情之中,實際上這是福貴已經逝去的親人們的生命在他身上的延續。加繆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判斷生活是否值得經歷,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對于“生活是否值得經歷”這個問題的回答,顯然只能夠從情感角度來講。一個人一旦沒有愛心,實際上也就宣布了這個人的死亡。事實上,福貴就生于愛的包圍之中,而他自己更有愛心。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被迫當兵時在槍林彈雨中所想的就可體會出來:
“我是一遍遍想著自己的家,想想風霞抱著有慶坐在門口,想想我娘和家珍。想著想著心思像是被堵住了,都透不過氣來,像被人捂住了嘴和鼻子一樣。”
在親情的感召下,我們只有好好地活著,正如和福貴一起當兵的老全所常講的,“老子死也要活著。”
此外,在作品敘述上,我們可以體會到,余華前期的大部分小說的敘述者仿佛是一個上帝。冥冥中他以冷漠的目光靜觀人世的變遷。而《活著》則采用了第一人稱敘事,讓我直接體驗到生命的殘酷性。余華這種敘述上的變化其實和他創作思想的逐漸變化是一致的,經過一段時間的創作,余華意識到了自己變化的必然性:“一成不變的作家只會快速奔向墳墓,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捉摸不定與喜新厭舊的時代,……作家的不穩定性取決于他的智慧與敏銳的程度,作家是否能夠使自己始終置身于發現之中,這是最重要的。”一個作家是需要不斷跟上潮流的。20世紀80年代先鋒作家所代表的徹底而尖銳的文化批判精神剛出現時令人精神為之一振,但一味批判則總讓人感覺不舒服。再者,先鋒性除了反叛性的特點之外,題中應有之義就是創新性與流動性,這注定了它必須不斷地自我突破,否則就會過時。而中國的先鋒作家多注重形式體驗的晦澀,這顯然與我們傳統的審美觀點有較大的差距,先鋒一旦經時間的沉淀必定會引起許多人的不屑(況且其才出現時就曾因讓人“讀不懂”而引起一些讀者的抱怨與冷落)。在這種情況下,先鋒作家與現實的關系必然處于矛盾之中,而這個矛盾只能由能動性的主體——作家來解決。受福克納等作家的啟發,余華的創作注意寫實性手法的運用,開始走向民間,而《活著》也給他矛盾的解決帶來了契機。
對于命運而言,《活著》標志著余華的思考和探索已有了初步的成功,此時余華筆下的人物已有了人性靈光的一面。而到了《許三觀賣血記》,余華更讓我們體會到人和命運的對抗,為了活下去,許三觀選擇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式,以自己血肉之軀的泉源——鮮血來換取生的權利。這是一個凡夫俗子所能做到的,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所能把握命運的惟一方式。這種活,讓我們感受到一種悲劇性。也不得不承認其現實可能性。
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言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活著即意味著直面死亡,活著即意味著承受苦難。福貴數次親見親人的故去,許三觀幾次走在死神的身前,但他們從未輕言放棄,反而表現出一種安之若素的超然心態。對于人來講,只有活著才可以稱之為“人”,福貴、許三觀們以自己的行為向我們詮釋著“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的深刻含義。
二、面對責任認真地活著
作為人來講,僅僅滿足于活著是遠遠不夠的,人與動物的區別,不止在于直立行走、能勞動,更在于人的社會屬性。我們講一個人活得沒有價值,常講他活得“像狗一樣”。顯然,作為高級動物的人,活著不僅僅是維持生命的存在,更在于對生活的質量的注意,對生活的期望值只有不斷提高,人才會有希望,才會有活著的支撐點。
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基本需要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
求五類,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其中,“生理需求”指“對食物、水、空氣和住房等需求”“安全需求包括對人身安全、生活穩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脅或疾病等的需求”“社交需求包括對友誼、愛情以及隸屬關系的需求”“尊重需求既包括對成就或自我價值的個人感覺,也包括他人對自己的認可與尊重”“自我實現需求的目標是自我實現,或是發揮潛能”。了解了這幾種需求的內容,下面再從這一理論出發,我們來分析一下許三觀的幾次賣血行為。他的第一次賣血雖是出于無意和好奇,但讓我們體會到了他活著的艱辛,因為賣一次血所得的錢和一個農民在地里做半年的活的收入一樣多,而且第一次賣血還和他的婚姻聯系在了一起,如果他沒有賣血,那么或許他想不到婚姻問題,但婚姻又是一個正常人所必須面對的,通過賣血許三觀解決了自己的誕生子嗣的愿望(這也是在維持后代的生存),從這一角度出發,他的第一次賣血應屬滿足“社會需求”。相較于第一次,許三觀的第二次賣血行為進入了更高層次,因為這次他是為非親子的一樂還債,摒棄了世俗觀念,同時也和何小勇的卑下人格相互彰顯,突出了許三觀的人性樸實的一面。或許是飽暖思淫欲,在婚姻的陰影中,許三觀走向了他曾動過心的林芬芳,得到了一份真誠的情感補償,為了這份情感補償他第三次去賣血。如果說,他與許玉蘭的結合只是人的一種必然到來的自然欲求,那么他和林芬芳的結合則是為了一份真實的情感,滿足了他內心真愛的需求。
許三觀以后的歷次賣血,或是為了解決孩子的饑餓,或是為了孩子們的生存,都體現了許三觀的社會屬性,即維護了他為人父的尊嚴,進而達到了人的“自我實現”。通過自己的一次次賣血行為,許三觀不僅獲得了孩子尊重,也得到了讀者的尊重。尤讓人感動的是,他為了籌治一樂的病的錢而一路賣血去上海,一個偉大而堅強的父親向人生的極限挑戰,讓人感受到一種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無疑這是一個庸常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在小說的結尾處。許三觀的最后一次賣血雖沒有成功,但也極大地震撼了我們的心靈,一個為了家和后代耗盡血汗的父親,成功后想的不是坐享其成、頤養天年,而是為以后的路而憂慮,更讓我們感覺到一種執著的生存意識。
如果說在《活著》中死亡還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到了《許三觀賣血記》中我們已很少能直接見到主人公親人的死亡了。在這里,生命頑強的主人公許三觀成功地實現了對自己的子輩(三年困難時期為使三個兒子能活下去而去賣血,尤其讓我們感動的是許為治一樂的病而一路賣血去上海)和妻子(“文革”中造反派貼大字報迫害許玉蘭時,他以自己的狡黠同樣讓孩子們貼大字報以遮蓋,當許玉蘭在街頭罰站時還親自去送飯,并在這里再次耍了個小聰明)的拯救。在這里,我們體會到了許三觀作為一個人所表現出的頑強的生命力,我們感受到了許三觀頭上隱隱地有一圈光環。
也許以上的描述使許三觀的形象在我們心中過于高大。其實小說中更有許多細節體現了許三觀作為一個普通人的自私和見識短淺。例如因一樂不是自己親生的兒子,他在一樂犯錯以后拒絕為之掏錢,還因一碗面條使一樂離家出走。夏天在飯館里他也習慣性地讓伙計溫酒等可笑的場面。但正是這些細節,讓我們感受到了許三觀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真實性。作為普通人的許三觀不僅認真地活著,而且還不斷注意著生活的質量,雖然他的活著是以血作為代價的,但這也是一種最為正常、最為現實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