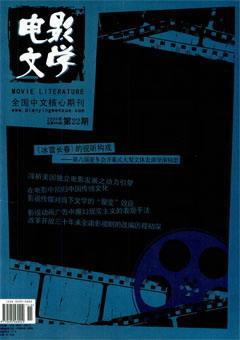論中國電影對書法美學思想的借鑒吸收
[摘要]中國電影植根于中國文化,故與中國書法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電影的意境構成模式、蒙太奇組合技巧以及色彩的選擇搭配都與書法聯系緊密。中國電影應自覺在書法藝術等傳統藝術形式中汲取有益養分。
[關鍵詞]中國電影;中國書法;意境;組合;色彩
1895年年底,法國人盧米埃爾兄弟在巴黎放映他們自拍的《火車進站》等短片,以此為標志,電影宣告誕生。時至今日,世界電影的重心無疑仍在西方。美國好萊塢更成為全球電影人的夢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電影評獎和展覽也在西方。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柏林國際電影節、戛納電影節等享譽世界。
中國電影必須要追趕世界潮流,并要有雄心引領潮流。中國電影要想引領潮流,恐怕不得不立足于自己所在的文化土壤,以此為基礎放眼全球,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找到一條融合之路、適己之路。所以,中國電影要想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來謀求發展,就一定得在傳統文化藝術以及古典文藝美學中汲取養分。作為一門綜合藝術,電影與繪畫、文學、音樂等藝術門類的關系十分密切,所以長期以來學術界不乏對它們之間關系的揭示。比如,文學的各種體裁都曾經直接對電影產生過巨大影響,出現過詩電影、戲劇式電影、散文電影和小說電影。電影亦從繪畫中借鑒了造型藝術的規律和特點,在光線、影調、色彩、線條和形體上有頗多相通之處。而音樂更是電影必不可少的概括主題、抒發情感、渲染氣氛的重要藝術手段。可是,作為傳統藝術精粹的書法,對于電影的意義卻始終鮮為人涉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書法藝術對于中國人的意義,在于它將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以一種具體可感的形式融匯于這個民族的每個個體的生活中。跟其他藝術門類相比較,書法藝術兼具藝術性和實用性,這種特點使它比任何藝術門類都有更為廣泛的群眾基礎。所以書法所折射出的美學觀念,無疑是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對世界的認知方式的一種藝術形式。書法藝術家熊秉明曾說,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中國哲學,而中國哲學的核心是中國書法。這話不是沒有道理。所以中國電影沒辦法不受到中國書法的影響,中國電影應自覺地在書法藝術美學思想中汲取養料。
一
“電影藝術是通過畫面、聲音和蒙太奇等電影語言,在銀幕上創造出感性直觀的形象,再現和表現生活的一門藝術。”所以一般人認為,電影最重要的構成要素是畫面和聲音。人們通過畫面和聲音就能很容易看懂電影,不需要特殊的文化修養。但事實上,很多電影對于不少人來說顯得過于晦澀、索然寡味,不明就里、云遮霧罩。觀眾看不懂電影,原因固然很多,但我們認為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恐怕與電影不全是畫面和聲音的產物有關。人物形象的喜怒哀樂不會完全通過言語來專遞,很多時候是靠人物的一個眼神、一個身體動作來實現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展示的。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對外部世界的關注正逐漸向內心體察過渡。如同恩斯特·卡西爾所說:“人類的文化越往后發展,這種內向觀察就變得越加顯著。”因此,通過人物的眼神、肢體等非言語形式來傳達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成為一種重要的敘事模式。這就不難理解盡管靠人物的眼神和身體動作傳遞信息和情感體驗具有某種程度的抽象性,但卻是頗受電影導演推崇的一種表達方式,主要在于它具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意境美:富于暗示性、啟發性、朦朧美,且虛實結合、境生象外。同時能真實而準確地傳遞言語無法傳遞的復雜多變的情感體驗。電影的這種意境構成模式與書法很相似。書法同樣是以一種相對抽象的方式傳遞意境的。書法雖然與繪畫相比有“書畫同源”之稱,但事實上,以筆墨線條來抒情達意的書法藝術早已經脫離具體的物象之形而發展成為一門抽象的藝術。這種來自抽象線條的審美方式、意境構筑方式必須經過相應的專門藝術訓練才有可能達到透徹的認識和理解。
電影和書法的這一特點告訴電影導演和表演藝術家,要在由抽象到形象的藝術傳達方式上下足工夫,即是要在眼神和身體動作等非言語方式表演技法上努力探索,以無聲勝有聲,準確傳遞人物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使人物性格的塑造更為典型、真實。書法線條常常一波三折、提按變化豐富,即使是最小的一個“點”畫,其傳達方式也決不是簡單的一點了事,也依然要處理出一個含蓄的、耐咀嚼和玩味的“像外之像”“景外之景”來。這就告訴我們的表演藝術家,決不可輕視作為角色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要知道并要努力去追求“舉手投足間皆有戲”。
二
我們知道,電影是對一個個的電影鏡頭或畫面以蒙太奇方式實現一個完整敘事的。這種畫面的疊加與組合方式按照一定的時空順序和審美要求敘述生活事件。而書法是以若干漢字的有序組合完成整幅作品的創作以表現書法家對生活的認知的,同樣存在一個不容顛倒且經過精心謀劃的時空順序和審美主張。從這個角度而言,電影與書法亦表現出密切的相關與相似。
電影中的蒙太奇,本為建筑學用語,意為組裝、構成。用于電影中,指畫面、鏡頭和聲音的組織結構方式。“組合”是蒙太奇最核心的美學內涵。“不但鏡頭與鏡頭、段落與段落,甚至畫面與聲音均可構成蒙太奇組合關系。”書法作品與此類似。在一幅作品中,字與字、字組與字組、段落與段落亦形成相應的有機組合關系,共同服從于作品的大章法,服務于作品意境美的營造。電影鏡頭有景別、焦距、鏡頭運動、角度、光線和色彩的豐富的變化。比如景別即有近景、遠景、全景、中景、特寫等變化,焦距亦有長焦、短焦、變焦等變化,鏡頭運動有推、拉、搖、移、降、升、跟等變化。電影鏡頭的這些豐富的變化的存在,使電影語言顯得異常豐富。同時,這些豐富的鏡頭的變化形態又必須在剪輯時保持連貫與流暢,給人一氣呵成之感。電影的這些美學特征使其避免了藝術行為最為忌諱的單調和呆板,同時又使電影畫面極富感染力和表現力。書法作品尤其是最具藝術審美價值的行草書作品的每一個單字的處理,從總的方面說也是力求變化之美。書法家在處理每個字時,總是自覺地避免雷同;對于一幅作品中的相同的字,更是努力寫出不同的筆法、字勢與結構,以求變化。世人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帖》,一個為人津津樂道的成就即在于作品中二十幾處“之”字的處理無一雷同,嘆為奇觀。此外,行草書作品還追求筆法的中鋒與側鋒之變、藏鋒與露鋒之變、提按與絞轉之變、方筆與圓筆之變;字法上,從線條對空間切割的均勻美與對比美著手實現“計白當黑”“疏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使透風”的美學主張;墨法上,由于古人深信墨分五色,所以作品要體現濃、淡、干、枯、濕的墨色變化;章法上,要求大小、疏密、長短、欹正、緩急的結合,同時還要服從于通篇行氣的貫通、流暢,前后字與字、字組與字組的呼應關系要明確。這些豐富的技法手段的變化、組合的變化,給書法藝術帶來了視覺上強烈的沖擊力和震撼力。
電影和書法的這些共同的美學特征,究其根本來說,正是中國哲學“對立的統一”思想的集中體現。正因此,中國的電影藝術有必要在書法藝術中汲取營養。一些具體
的處理技巧甚至可以一一對應。比如,電影里的長鏡頭,就好比是行草書作品里的一個長豎——飽含激情、不能自己、一泄如注而又曲折委婉、蕩氣回腸。這樣的鏡頭或這樣的線條往往成為整個作品的神來之筆,有畫龍點睛之妙。電影里的特寫鏡頭,好比書法作品中放大的一個字形,不僅字形大,而且用墨厚重,極易吸引人的注意,是書法家重點表現的對象,這與特寫鏡頭的初衷如出一轍。電影里的敘事段落,可看做書法里的字組或字群,這樣的段落或字群往往表現一個相對完整統一的局部敘事或情感體驗。
中國電影要體現民族特色,還必須在色彩選擇與搭配上下足工夫,在色彩上體現民族審美意識。這一點,張藝謀的民俗和民族類電影體現得非常充分。攝影師出身的張藝謀深諳中華民族對色彩的偏好,他的民俗和民族類電影只需透過畫面色彩就能撼人心魄。《紅高粱》中有鋪天蓋地的紅色:紅高粱、紅酒、紅色裝扮的新娘、紅花轎;《大紅燈籠高高掛》中黑色的院、白色的雪、紅色的燈;《秋菊打官司》為了凸顯紅色,將賣豬改成賣紅辣子;《我的父親母親》中年輕的母親身穿紅色大襖、扎著紅頭繩,成為觀眾內心永遠燦爛鮮活的記憶。而《英雄》則以黑紅兩色為主,并融入李慕白的一襲白衣裝扮。顯然,張藝謀電影的色彩選擇在有意識地強調民族性,強調通過色彩來拉攏與觀眾之間的審美距離。他的電影的三大主色調即是紅、黑、白色。而這,亦正是中國書法的三大色調:白紙、黑字和紅印。沈尹默說書法藝術“無聲而具音樂之節奏,無色而具圖畫之燦爛”。書法藝術的黑白二色長期以來并不以它色調的單一而為人輕視,相反,卻能幻化出無窮的魅力而讓人頂禮膜拜,這是一件讓人玩味的事情。事實上,書法中的黑與白,與太極圖黑白兩個陰陽魚有著同樣的哲學內蘊,意涉派生萬物的本源,“一陰一陽之謂道”,表達的是中華民族對陰陽、動靜輪轉,事物相反相成的宇宙觀的體認。《老子》稱:“知其白,守其黑。”這種“計白當黑”的虛實結合、境生象外的美學觀“是中國藝術中最迷人的部分”,而書法無疑是最能體現這種虛實觀的傳統藝術。此外,書法作品中另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印章,則選擇了紅色。一方面,紅色是中華民族傳統的主色調,是喜慶、活力與生氣的體現;另一方面,紅色能起到廁龍點睛之妙用。雖然在作品中它偏置一角,本身并不會鋪天蓋地、隨處出現,但卻因能夠與黑白二色形成鮮明的對比而達到“對立統一”的功效,互相襯托、相得益彰,十分惹眼也非常必要。書法的這種色彩處理,毫無疑問可以為電影在色彩的選用、搭配、組合上提供參照——一方面色彩的選擇與組合要符合民族審美習慣、民族心理,要努力達到相得益彰、互相襯托的功效,另一方面要善于借助色彩來營造一個讓人迷戀、玩味的審美意境,給電影敘事以更多更豐富的意蘊暗示。
總之,中國電影由于植根于中國文化,與中國書法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電影應自覺在書法藝術等傳統藝術形式中汲取養分,為中國電影早日走向世界、贏得世界的尊重與贊譽而努力。
[作者簡介]于軍民(1974—),男,四川廣安人,碩士,內江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藝術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