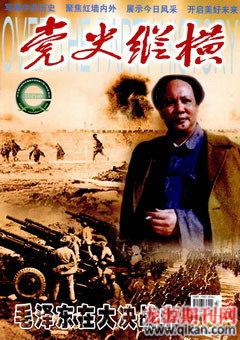彭湃犧牲,悲憤周恩來發(fā)出“絕殺令”
王增勤
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上海市霞飛路附近一處宅院的門前,隨著“砰!砰!砰!”幾聲槍響,—個穿黑色西裝的人當場命歸西天。當大批法國巡捕和偵探趕到時,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裝者在內(nèi)的幾具尸體躺在腥紅的血泊中。
在戒備森嚴的法租界發(fā)生如此刺殺大案,并且部署策劃得如此周密,實施刺殺如此干凈利落與準確無誤,此消息立即轟動了全上海。各報連日都以顯著位置報道了這一重大新聞,有的報紙甚至稱之為“東方第一謀殺案”。
英雄就義,周恩來親令“鋤奸”
那個被打死的穿黑色西裝的人,名叫白鑫。他是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被錄取為黃埔四期學生,后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27年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nóng)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等同志,于次日下午在他家開軍委會議,研究重要軍事問題,并且說,黨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也參加。24日下午,會議按時進行。周恩來因為臨時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辦,就臨時請假未能到會。
彭湃等人萬萬沒有想到,會議還在進行中,大批國民黨特務(wù)已經(jīng)偷偷包圍了會場,不久便沖進屋內(nèi),按他們手中拿的名單抓人。
“伍豪(周恩來化名)?誰是伍豪?”特務(wù)們咆哮著。彭湃他們站在一旁,對特務(wù)們怒目而視。
“彭湃?誰是彭湃……他就是……”特務(wù)們沖過去,一把拉過彭湃,用手拷扣住了他的雙手。奇怪,特務(wù)們?yōu)槭裁茨弥麊?又為什么那么準確地認出了彭湃?這里肯定有問題。
然后,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委員楊殷,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委員顏昌頤,中央軍委委員負責兵運工作的邢士貞等同志,也和彭湃一樣都被拷上手拷,推推搡搡押進了囚車。
事情發(fā)生后,周恩來和負責中央特科的陳賡通過多種渠道了解到,黨內(nèi)出了叛徒。這叛徒不是別人,正是白鑫!大革命失敗后的上海,每天都處于腥風血雨之中,白鑫早已被敵人的白色恐怖嚇破膽,他通過在南京被服廠當廠長的哥哥,聯(lián)系上了國民黨上海黨部情報處長范爭波。為了邀功請賞,他提出能幫助國民黨抓到伍豪、彭湃等共產(chǎn)黨要人。范爭波喜出望外,便與白鑫暗中定計,借中共中央軍委開會的時候,來個一網(wǎng)打盡。所幸周恩來因為臨時有事沒有參加,不然中共中央的損失可能會更為巨大。
周恩來指示陳賡,設(shè)法通過在國民黨內(nèi)部的同志,打聽到彭湃、楊殷等同志關(guān)押的地點、審訊情況,以便營救。陳賡通過敵人內(nèi)部的我黨秘密特工楊登瀛,很快知道了彭湃等同志關(guān)押的地點,并且得知,蔣介石已下令槍決彭湃等同志,執(zhí)行的時間在8月28日清晨。經(jīng)過周密計劃,周恩來他們制定了一個營救方案。
8月28日清晨,從外白渡橋到龍華,一路上戒備森嚴,如臨大敵。裝載彭湃、楊殷等同志的囚車,被夾在10余輛全副武裝軍營的卡車中間。市民們默默地注視著一切,他們知道,又將要有革命者倒在龍華殺人場上!
陳賡指揮的紅色隊員,已經(jīng)在事先計劃好的地段埋伏起來。為了攔劫囚車,他們還專門備好一輛大卡車,里面裝滿了大米。卡車后面,幾十名紅色隊員裝扮成拍外景的電影工作者,只要暗號一響,他們就投入戰(zhàn)斗。因為怕路上有特務(wù)搜查,他們手中暫時還沒有槍支。陳賡另專門安排一輛車裝槍支,將在約定時間開到指定地點。
囚車駛過來了。但是敵人早已經(jīng)做好了防劫法場的準備,這天不僅出動了大批軍警,而且還在沿途實行了戒嚴。相比之下,敵我懸殊很大,加上專門運送槍支的車輛因為敵人的層層盤查,未能及時趕到埋伏現(xiàn)場,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他們只好忍痛放棄原定的計劃。
彭湃是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農(nóng)民運動的主要領(lǐng)導人之一,海陸豐農(nóng)民運動和革命根據(jù)地的創(chuàng)始人,被毛澤東稱之為“中國農(nóng)民運動大王”,在黨內(nèi)有著很高的威望和影響力,他的犧牲無疑是黨的一大損失。彭湃就義后,周恩來悲憤萬分,親筆撰寫了《彭楊顏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jīng)過》,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機關(guān)報《紅旗日報》上發(fā)表。8月31日下午,周恩來含淚起草了《為反抗國民黨屠殺革命領(lǐng)袖告全國勞苦大眾書》,憤怒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殘殺彭湃等同志的罪行。與此同時,他指示陳賡,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蹤,定殺不赦,以絕后患!
“烏龜”露頭,柯醫(yī)生“長線釣魚”
陳賡接到周恩來的指示后,便安排上海地下黨組織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白鑫不是傻瓜,當然明白自己現(xiàn)在的處境,就當起了“縮頭烏龜”,國民黨方面為了在他身上“榨”到更多的“油水”,由上海黨部情報處長范爭波親自給他當“烏龜殼”。因此,地下黨組織盡管四處打探,也一直沒有弄到白鑫的任何訊息。陳賡給同志們打氣說:“白鑫難道會上天入地?他只要還在上海,這只‘烏龜就會有露頭的一天。”
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帶著國民黨特務(wù)突然到上海達生醫(yī)院找柯達文大夫看病。原來,白鑫自因告密殺害了彭湃后,知道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不會放過他,整天處于極度的驚恐之中,不長時間就嚇出了頭疼的毛病。柯達文為他診病后,說:“你坐一坐,有幾種藥在樓下,我去取。”他下樓匆匆到鄰居家給陳賡打電話,不料白鑫這時早已經(jīng)成驚弓之鳥,等他回來時,白鑫已經(jīng)悄然離去。
陳賡指示柯達文說:“他露面了就好,病人有病總會找醫(yī)生的。他要再到你那兒,先設(shè)法穩(wěn)住他,我們的人隨時就到!”
柯達文是中共地下黨員柯麟的化名。那時,他在上海威海衛(wèi)路一條里弄開了一所達生醫(yī)院做掩護,樓下是診所,樓上是地下黨組織的會議室。上海地下黨組織每月在這里開一次會,周恩來有時也在這里接見外地來匯報的人。
而白鑫在黨內(nèi)的職位較低,再加上剛到上海不久,他并不曉得柯達文的真實情況,只知道柯達文醫(yī)術(shù)好,又是廣東人,一副書呆子相貌,不像是共產(chǎn)黨人。果然,過了幾天,白鑫又打來電話,說要再請柯達文看病,不過,狡猾的他不到達生醫(yī)院來了,而是要柯達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飯店給他看病,柯達文問是哪家飯店,白鑫說到了法租界自會有人告訴他。
柯達文將這一新情況及時向陳賡作了匯報,陳賡指示他按約定時間前往,并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療的分寸,既要讓白鑫感到治療后病情明顯減輕,也不能讓他感到已經(jīng)痊愈,這叫“放長線釣大魚”。柯達文自然心領(lǐng)神會。
柯達文按約趕到白鑫所在飯店,這時和自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還有范爭波。一見面,白鑫用懷疑的口氣問:“那天,你說下樓取藥,怎么出去了?”“哦,是這樣。”柯達文鎮(zhèn)定地回答,“我到樓下一找,缺一種藥,我想出門一拐就是藥房,心想快去快回,誰知我趕回來,你怎么走了?連藥也沒拿!”“那天我有急事,看看表時間快到了,等不及拿藥,只好走了。”白鑫也
編了一通假話。
柯達文給他看過病后,白鑫又留他喝杯咖啡,實際上他是對柯達文還不大放心,想多留他—會,讓范爭波觀察一番。
白鑫說:“你那醫(yī)院太小了,應(yīng)該買一棟大樓,設(shè)部分高級病床。”柯達文搖搖頭,說:“我是外鄉(xiāng)人,在上海無親朋好友,誰肯幫忙?”白鑫立即從皮箱里掏出500元錢,遞了過去:“柯大夫,不敢言贈,表示一點小支持!”范爭波也在一旁幫腔說:“收下吧!以后合作的日子還長著哩!”
柯達文本來不想接受叛徒的錢,但他似乎看穿了白鑫和范爭波眼睛后面的東西,稍微推讓了一下后,趕緊把錢放進衣兜中,千恩萬謝一番后起身離去。望著他遠去的背影,白鑫和范爭波相視一笑,都把心放在了肚里。
柯達文出了飯店,坐電車兜了幾個圈子,看看身后沒有特務(wù)盯梢,便趕到陳賡那里匯報,把500元錢也如數(shù)交給了黨組織。陳賡十分高興,說:“好!繼續(xù)偵察,一定盯緊他!”
又過了幾天,白鑫自感吃了柯達文給開的藥后病情減輕許多,再次請柯達文看病。這次,小車載著柯達文停在了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四弄四十三號門口,不幾日后他們又將柯達文請到這里。柯達文估計,這兒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達文將這一重要情報向陳賡做了匯報。
深入“虎穴”,楊登瀛“義結(jié)”叛徒
柯達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陳賡不由大喜過望,但柯達文限于身份,再往后只能做些外圍工作,但要真正打進敵人內(nèi)部去,盯準白鑫,還必須另找一個同志。
于是,陳賡再次想到了楊登瀛。楊登瀛原名鮑君甫,自幼就在日本生活與求學,是一名名符其實的日本通,進入國民黨特務(wù)機關(guān)內(nèi)部后,國民黨特務(wù)頭子陳立夫把他視為知己,任命他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駐上海特派員!到上海不久,楊登瀛因為同情共產(chǎn)黨人,成為中共歷史上第一個不是黨員的特工人員。楊登瀛利用這個關(guān)系,經(jīng)常在上海出入國民黨上層和特務(wù)之中,獲得許多重要情報,在最緊急的關(guān)頭,救過中共上海地下黨許多同志。
這一次,陳賡請楊登瀛弄清楚和全坊四弄四十三號是個什么地方,他很快回復說:“那是大特務(wù)范爭波的公館,白天黑夜都有國民黨特務(wù)看家護院!”
“唔!怪不得白鑫會藏在他那里,原來是個‘老虎穴!”陳賡似有所悟。接著,陳賡將周恩來的“鋤奸”指示告訴了楊登瀛。楊登瀛心領(lǐng)神會:“你放心,我馬上去這個‘虎穴摸清白鑫的情況,并把他定在那里,以便咱們下手。”
次日一大早,楊登瀛就找了個事由,登門到范公館拜訪。楊登瀛這位陳立夫跟前的大紅人親自登門,范爭波自然不敢怠慢,他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位“大員”竟然會“通共”,也就沒有安排白鑫刻意回避。范爭波和楊登瀛正在客廳里閑談時,白鑫下樓到院內(nèi)散步,楊登瀛假裝不認識,問他是誰,范爭波便把白鑫介紹給他。
能夠結(jié)識楊登瀛,白鑫受寵若驚:“楊特派員,乞望今后多多指教!”楊登瀛笑了笑,說:“共匪要犯彭湃能夠落網(wǎng),你可立了一大功!”白鑫搓搓手,說:“不敢!只可惜那次伍豪未能到會,否則他也跑不了。”楊登瀛一語雙關(guān)地說:“我一定向中央組織部報告。中央對你一定會論‘功行‘賞的!”“多謝楊特派員!”白鑫一副媚態(tài)。
此后,楊登瀛多次到范公館找白鑫談話。一次,他故作關(guān)心地對白鑫說:“彭湃案轟動全國,估計共產(chǎn)黨不會輕饒你,你哪里也不要去,住在范公館里,否則會招致禍端。”白鑫聽了,立即出了一頭冷汗,哀求道:“特派員,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請示,要我到南京去吧。”楊登瀛說:“現(xiàn)在不能走!得過一陣,風聲小了再動不遲。”白鑫萬般無奈:“是、是……可是我這心里……”楊登瀛說:“不要怕!有我在,這件事最為保險,你放心好了!”
有一次,他正在和白鑫談話時,正巧柯達文前來診病,楊登瀛假裝不認識,等柯達文走后,他用關(guān)切的口氣問:“這個人可靠嗎?不要把共產(chǎn)黨引進來。”白鑫肯定地說:“他不可能是共產(chǎn)黨。”楊登瀛笑著說:“那就好!這地方可千萬不能叫共產(chǎn)黨偵察到。”他又回頭告訴范爭波:“爭波,不可大意!”范爭波說:“放心好了,登瀛兄,能進我這門的,都是最可靠的人,共產(chǎn)黨絕對找不到這里!”
就這樣,楊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楊登瀛時常前來和白鑫閑談,打麻將,實際目的就是為了把白鑫穩(wěn)住。
里應(yīng)外合,“鋤奸隊”深夜懲奸
白鑫盡管住在國民黨大特務(wù)家里,又有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駐上海特派員楊登瀛的“保護”,仍吃不下,睡不好,一閉上眼睛就夢見彭湃、楊殷等人渾身是血地站在他床頭,雖然不斷找柯達文診治,但頭疼的毛病總是反反復復,不見痊愈。
白鑫知道此地不可久留,就一再請求范爭波向南京方面報告,希望能允許他出國去躲躲風頭,最好是去意大利。他認為在國內(nèi)即使是去南京或者廣州,也不安全,共產(chǎn)黨說不定哪一天就會找到他,替彭湃報仇。
最后,國民黨方面終于同意白鑫逃往意大利。當然,對這么“核心”的機密,范爭波和白鑫是不相瞞“好朋友”楊登瀛的。
陳賡接獲這一重要情況后,立即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準確時間、船次、從何處出發(fā)、坐什么車去碼頭,并指示陳賡組織精悍的“鋤奸”隊員,堅決除掉叛徒,絕不能讓他逃往國外。
白鑫和范爭波、楊登瀛商定,出走時間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時,并且船票已經(jīng)定好。范爭波還特意安排,小汽車就停在公館后門口,讓白鑫夫婦出門就上車。
楊登瀛心想,范爭波這樣的安排,我們的紅色隊員將無法爭取時間展開戰(zhàn)斗,鏟除叛徒的計劃十有八九會付之東流。他急中生智,對范爭波說:“你的方案也許不錯。可是,深更半夜,門口停輛汽車,會惹人注意。萬一走漏點什么消息……”
“不會的!”范爭波說,“這件事,連我的管家也不知道呢!”
“不然!”楊登瀛擺擺手,“自剿滅彭匪以來,共黨恐怕一直在暗中偵察白鑫的蹤影。他們的人向來無孔不入,萬一他們疑心到此處,而門口又停輛小車。豈不是要出問題嗎?”
范爭波也許是認為楊登瀛說的有理,或許是不想因為這點小事駁楊登瀛的面子,終于定下來,小汽車不停在四十三號門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楊登瀛隨后將一切都向陳賡作了匯報,陳賡對他的機智沉著表示了稱贊。
1929年11月11日傍晚,楊登瀛以辭行為名,又特地到范公館偵察一次,并送給白鑫一盒點心,“聊表一點心意”。可笑的是,死到臨頭的白鑫此時還對楊登瀛的“關(guān)懷”萬分感動,分別時竟然還流了幾滴眼淚。楊登瀛看到白鑫仍按原計劃逃跑,才放心離去。
入夜,負責伏擊叛徒的“鋤奸”隊員按計劃分別潛入和全坊,在四弄四十三號的后門布置得十分周密。夜靜更深,周圍人家紛紛熄燈安寢。只有四十三號院里仍然燈光閃亮。11時許,四十三號院后門悄悄啟開一道縫,一個人閃出來站在門口,聽了一會兒動靜后,他見周圍十分安靜,認為沒有任何危險,才向里面招手。大門里很快閃出7個人:白鑫夫婦、范爭波兄弟和3個“護駕”特務(wù)。
他們剛走幾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聲:“白鑫,哪里走!”接著就是“砰、砰”兩槍,一個特務(wù)應(yīng)聲倒地,范爭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話未說完,一顆子彈打死了他。白鑫為了活命,拼命向停在弄堂口的汽車跑,一個“鋤奸”隊員立即追過去。白鑫跑到汽車處剛要鉆進去,后面的槍聲響了……
戰(zhàn)斗很快結(jié)束。白鑫、范爭波弟弟和兩個特務(wù)被打死,范爭波和白鑫的老婆則受了重傷。事件發(fā)生后,中外報紙著力渲染,有的報紙甚至冠以“東方第一謀殺案”,借以駭人聽聞。國民黨方面下令迅速查清事實真相,他們費了老大勁也沒有查出個子丑寅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