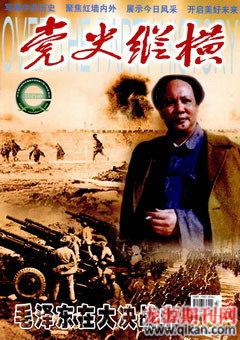潘漢年如何成為黨的文化統(tǒng)戰(zhàn)先鋒
王 焯
1906年1月18日,潘漢年出生在江蘇宜興縣陸平村。世代書香的潘家,由于不去做官,靠務農,做塾師,自然成為“破落戶”。
1911年辛亥革命后,潘漢年的父親潘莘臣一度被選為宜興縣議員,但仍課讀鄉(xiāng)里,教育子女。小漢年秉性聰穎,深得長輩喜愛。1919年夏,潘漢年在宜興縣立第三高小畢業(yè),在林圩祖母吳氏的資助下進彭城中學讀書。
中學期間,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潘漢年十分愛好文學、外語,特別是戲劇,他常扮演窮苦人民的角色,因對生活在社會底層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的表演使觀眾為之動容。1921年他離校投身了革命。1925年初,在大革命洪流的鼓舞下,潘漢年告別了家鄉(xiāng)父老,只身來到大上海,從此開始了新的人生旅途。
投身創(chuàng)造社
到上海不久,潘漢年就被聘為上海中華書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編輯。之后,他參加了創(chuàng)造社,并任《All》周刊主編。同時,他還和葉靈鳳合辦了一個半月刊《幻洲》。在這兩個刊物上,潘漢年發(fā)表了一系列戰(zhàn)斗檄文,如《原來如此內除國賊!》、《幻想中的OAZO》、《街頭閑話》、《對空爐評空話》、《新流氓主義》等。他長于諷刺,善于說理,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他的雜文,一掃當時無聊文人的頹廢之氣,振奮了青年人,為徘徊中的青年指明了方向。
潘漢年還積極投身于洶涌澎湃的政治洪流。不久,他加入了革命的國民黨,為反帝反軍閥斗爭奔走呼號。1925年夏,上海“五卅”慘案后,潘漢年迅速投入聲勢浩大的群眾行列,并寫了許多反帝檄文。在這場運動中,他切身感受到共產(chǎn)黨人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的革命氣概,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在潘漢年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的業(yè)務從1926年春潘漢年加入該部后發(fā)展很快。許多新書刊在該部附設的門市部常銷售一空。顧客天天絡繹不絕,引起了反動軍閥當局的注目。此時,上海政局控制在直系軍閥之手,五省聯(lián)軍總司令孫傳芳兼任淞滬督辦。這位被稱之為“恪威大將軍”的直系“聯(lián)帥”,正面臨國民革命軍在浙、閩、蘇、皖、贛五省的武力威迫,惶惶不安于“赤化”,對其后方基地上海控制極嚴。8月7日,由淞滬警察廳出面,查封了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逮捕了正在工作的葉靈鳳、柯仲平、周毓英、成紹宗四人。這一天,潘漢年不在現(xiàn)場,免遭了一次牢獄之苦。事發(fā)后,潘漢年為營救同伴四處奔走,他想起了自己的入黨介紹人、中國濟難會負責人王弼、阮仲一,請他們設法營救。經(jīng)各方串聯(lián)呼吁,加之警察廳“證據(jù)不足”,該廳廳長只好順水推舟,于8月12日放出了這四人,并批準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重新開業(yè)。
這件事發(fā)生后,潘漢年與中國濟難會的關系又深了一層。經(jīng)組織同意,潘漢年也加入了這一組織,并積極參與各項活動,成為該組織一名得力骨干。當時,中國濟難會里聚集著一批社會知名人士和中共早期領導人,他們中間有惲代英、張聞天、楊賢江、楊杏佛、沈澤民、郭沫若、沈雁冰等人,潘漢年受到了他們的影響,也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情。1926年11月23日,由該組織推薦,潘漢年代表中國濟難會上海分會,到武漢出席該組織的籌備會,商議有關全國代表大會的具體事宜。
潘漢年的此次武漢之行,收獲甚大。他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張國燾、向忠發(fā)、陳潭秋、李碩勛等當時中共一些最主要的領導人。會議期間,他認真地聽取了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的報告,李立三的工人運動報告,張國燾的國際國內問題報告以及李碩勛的學生運動報告,大大開闊了視野。
當時,武漢三鎮(zhèn)剛被北伐大軍收復,充滿了熱烈的革命氣氛,潘漢年多次參加了武漢的群眾集會,并同與會代表一起赴湘參加長沙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他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薰陶,在政治上似乎成熟了許多。這些變化,不久后即在他的實際工作中,在他的筆下,都有比較明顯的反映。會議結束后,潘漢年于1926年12月下旬返回上海。
主編《革命軍日報》
就在潘漢年往返滬漢之際,北伐大軍正以摧枯拉朽之勢,進擊東南各省,向長江中下游推進。國民革命繼續(xù)呈蓬勃發(fā)展的趨勢。當時,執(zhí)掌北伐帥印的蔣介石正盤算著發(fā)動反共陰謀,但在表面上,依然標榜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贊成國共合作。尤其是北伐戰(zhàn)爭正在進行之中,他還需要蘇聯(lián)軍事顧問,特別是需要共產(chǎn)黨人的幫助。于是,中共的知心朋友,大名鼎鼎、聞名大江南北的創(chuàng)造社盟主郭沫若,被請到了南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司令部,輔佐國民黨左派領袖鄧演達,出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郭沫若走馬上任后,迫切感到需要加強軍隊的政治宣傳工作,他與總政治部副秘書長李一氓協(xié)商后,決定以總政治部的名義,創(chuàng)辦一份小報,定名為《革命軍日報》。
《革命軍日報》是一張八開的宣傳性的軍中小報,其內容要求不僅政治性強,而且文字活潑,融理論性、可讀性于一爐。郭沫若與李一氓在南昌和武漢兩地居然未能物色到合適的編輯人選,便把主意打在了潘漢年身上。
郭沫若和李一氓雖已投筆從戎,但他們在戎馬倥傯之中仍然關注著上海文壇,很欣賞潘漢年主編的《十字街頭》,對這些“如同李逵的板斧,排頭一路砍去”的雜文、小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xiàn)在急需合適的編輯人才,潘漢年是最合適不過的了。于是,郭沫若親自出馬,向上海的潘漢年發(fā)去邀請,并在南昌恭候他的到來。
潘漢年返滬后,繼續(xù)主編《十字街頭》。當他接至郭沫若的邀請信后,立即向所在地下黨支部書記丁曉元作了匯報,黨組織經(jīng)過討論,很快答復潘漢年:同意他去南昌工作,并為他開具了組織介紹信。
1927年2月上旬,把一切工作交待完畢,潘漢年自虬江碼頭登船,溯江西行,經(jīng)九江,于是月中旬抵達南昌,拜見了郭沫若、李一氓之后,便脫去西裝,換上了一套國民革命軍軍服,正兒八經(jīng)地當起了“丘八”。此刻,他感到別有一番風味,用他的話說,叫作“置身營幕、軍書旁午”。
潘漢年到任后,總政治部任命他為《革命軍日報》總編輯。作為一個主筆,他以忘我的革命熱情,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全身心地投入了編輯部的工作。在他的辛勤努力下,這份報紙越辦越有特色,很快成了國民軍將士愛不釋手的讀物了。
4月12日,一場腥風血雨席卷浦江兩岸,無數(shù)革命志士慘死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之下,這就是蔣介石一手制造的反革命“四·一二”大屠殺。
7月15日,汪精衛(wèi)在武漢實行“分共”,這位自詡為國民黨的“左派”領袖,高叫“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的偽君子,終于撕下了他的假面具,與蔣介石歧路同歸了。
上海的“清黨”與武漢的“分共”,就這樣把共產(chǎn)黨人和廣大革命志士推向了血海之中。
7月下旬,潘漢年隨郭沫若等總政治部機關一行人,從武漢抵達九江。原來他們打算共赴南昌參加起義,不料受張發(fā)奎
阻止,未能去成。這樣在政治部工作的共產(chǎn)黨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黨中央報到。
潘漢年也無法去南昌了。由于他在這段時間所表現(xiàn)出來的工作能力,特別是政治活動的特殊才干,以及對黨的堅定信念和對政治局勢敏銳的洞察力,黨組織對他的信任和重視是必然的。在當時這種復雜而動蕩的形勢之下,中共總政治部黨組織決定由潘漢年擔任返回上海同志的領隊。他沒有辜負組織上的信任,一路將同志們安全帶到了目的地。
再回上海變“小開”
此時的上海,依然為嚴重的白色恐怖所籠罩。“四·一二”大屠殺使寶山路三德里已經(jīng)面目全非了。
很快,潘漢年找到了葉靈鳳他們,大家異常高興,并決定繼續(xù)過去的宗旨,再唱《幻洲》,仍由葉主編上半部《象牙之塔》,由潘主編下半部《十字街頭》。
大革命的勝利和失敗,嚴酷的戰(zhàn)斗洗禮,在潘漢年的心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也留下了沉痛的傷痕。他的思想認識水平有了一個飛躍,他不僅從大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更從大革命的失敗中醒悟到更多更深層次的道理。革命是一條艱巨彎曲之路,革命的勝利絕不可能一蹴而就;革命要成功就必須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要以流血犧牲作抵押。正因為如此,在革命處于低潮的動蕩年代里,才會有嚴重的分化,既有不屈的斗士,也有落伍的懦夫、叛黨的鷹犬,還有許多人徘徊于十字街頭,他們更需要激勵和幫助。為此,潘漢年經(jīng)過許多個不眠之夜的深思熟慮,在《幻洲》第2卷第1期上,發(fā)表了一篇閃光的杰作《我再回上海》。文中寫道:
“悠悠的歲月,在咱們昏昏不甚清楚自己生活似的中間,又飛過去八個足月。在1927年的今年我個人的生活史上平添這八個月的灰色、刺激、苦厄、病痛和流浪逃避的生活,頗足我將來余暇的細細回憶未亡的中國。在這八個月中,也開拓了一頁復雜、劇變與黑暗中的殘酷的歷史。八個月以前,在黑暗中企求光明,在苦厄中希望樂趣,在壓迫中要求解放,到現(xiàn)在——八個月以后,所有的希望,都成了夢影,依然在黑暗、苦厄、壓迫的道路上掙扎!這個,不是環(huán)境的錯誤,我以為是咱們自己認錯了‘時代。”
從這段文字中,不難發(fā)現(xiàn)這時的潘漢年,不僅對政治形勢有著較深邃的洞察力,并一改昔日那種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新流氓主義”文風,潘漢年顯得老練了。更可貴的是,他還從失敗的教訓中,去尋找自己的缺點和錯誤,這是一個革命者對人、對事,對自己乃至對革命事業(yè)負責的崇高思想境界。正因為有了這種思想境界,他才敢于檢查自己過去的“錯誤”,向自己的“錯誤”開刀,這也就為他此后不久更好地促進左翼文化界大團結,奠定了思想基礎。《我再回上海》一文的發(fā)表,可以說是潘漢年步入文壇后從政治思想到文學藝術發(fā)生轉軌性變化的一個標志。
潘漢年回上海后,寶山路三德里這地方不能再呆下去了。
1927年9月間,也是潘漢年和葉靈鳳合編《幻洲》快一年的時候,他們搬到了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一間臨街的“亭子間”。
潘漢年自宜興到上海后,慢慢養(yǎng)成了一種穿西裝的習慣,他壓根兒不喜歡穿長衫馬褂,也不愿穿上被人指責為“赤化”的中山裝。西裝革履,是他衣著上的一個特點,也為他日后對敵斗爭帶來了方便。由此緣故,不相識的人還以為潘漢年是資本家的兒子,熟識的朋友,則戲稱他為“小開”。“小開”在上海話里,即為資本家的兒子。于是,“小開”之名,就在這“亭子間”,在這頗為寒酸的日子里,被叫出了名。對此,潘漢年并不介意,他默認了,并且堂而皇之地以“小開”、“小K”等代號發(fā)表文章,甚至發(fā)展到后來在向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共產(chǎn)國際、中共中央?yún)R報的文書上,也署上“小K”這個代號。
一個顯著的變化是,潘漢年改變了以“罵”作為主要的斗爭手段和四面出擊的斗爭方式。其矛頭所向,主要針對國民黨新軍閥及其幫兇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揭露他們絞殺革命的種種倒行逆施。潘漢年開始從一般就事論事的方式,轉向從政治思想上加以剖析,給人以多角度、深層次的啟迪。
潘漢年的結論是:“只有發(fā)動文化運動,展開文化革命,才能釀成一個有希望的政治革命。”他大聲疾呼,“大家預備著二次革命”。他的這些文字,論述未必精當,分析未必深刻,但通篇所反映的“赤化”思想,不能不引起國民黨新軍閥的仇恨。1928年春,正是南京國民政府開張之初,也是蔣介石黃袍加身之際,這種大逆不道之言,能允許它繼續(xù)泛濫嗎?1928年1月,《幻洲》出版第2卷第8期后不久,果然被國民黨上海警方以“宣傳反動”的罪名查禁。
《幻洲》被查封之后,很快又于4月1日推出了《戰(zhàn)線》周刊。潘漢年經(jīng)過了大革命風暴的洗禮,經(jīng)過了實際斗爭的鍛煉,經(jīng)歷了生與死的考驗,他終于革心洗面,原有的小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態(tài)度,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激進性、盲目性,受到了沖擊,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一個跳躍式的轉變。當然,潘漢年還得繼續(xù)經(jīng)受實踐斗爭的磨礪。不過這段時間的長足進步,為他在不久后走上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崗位,奠定了基礎。
首任中央文委書記
二十年代,潘漢年以出眾的才華在上海文壇脫穎而出,為越來越多的人所佩服。他辦事機敏、干練,特別是廣泛的社會活動能力,逐漸為更多的同志所了解、贊賞,并引起了中共黨組織和有關領導人的重視。
第一個重用潘漢年,并將重擔交給他的是李富春。潘漢年返回上海后不久,李富春也奉命到滬,在江蘇省委工作,任省委宣傳部長。1928年5月,李接替項英任省委書記,由于當時上海隸屬江蘇省委,李富春又成了潘漢年在黨內的頂頭上司。為了加強文化界黨組織的統(tǒng)一領導,開辟黨的文化工作新局面,1928年夏,江蘇省委決定將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三個黨小組合編為一個支部,即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于是,就由李富春出面,找潘漢年談話,布置了任務,委托他擔任書記。從此,潘漢年在李富春的直接領導之下,負責溝通同文化界各級組織及成員之間的聯(lián)系,以貫徹黨的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
1928年冬,文化工作者支部劃歸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仍由潘漢年任書記。翌年6、7月間,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在上海召開。這次會議通過了《宣傳工作決議案》,強調黨的宣傳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宣傳教育是實現(xiàn)黨的任務的經(jīng)常的基本的工作”,并提出了加強宣傳工作的組織措施,要求“中央宣傳部本身必需有健全的組織,應當建立各科各委的工作”。據(jù)此,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負責“指導全國高級的社會科學的團體,雜志,及編輯公開發(fā)行的各種刊物和書籍”。潘漢年被任命為第一任文委書記。這一年,他才23歲。
潘漢年走馬上任。迅速解決了上海文壇持續(xù)了一年有余的一場大論爭。這就是有名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關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
論爭的雙方,一方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
的進步的文化團體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另一方則是被毛澤東稱之為中國無產(chǎn)階級文化運動旗手的魯迅及其追隨者。潘漢年對緩和這場論爭并得以逐步平息起了決定性作用。這位小開書記的話,對論爭一方的文化界人士尤其是黨員來說,是有說服力的,并有政治思想的指導性和組織紀律的約束力;但對論爭的另一方魯迅等來說,這位共產(chǎn)黨的年輕書記的文章,入情入理,而且態(tài)度誠懇,姿態(tài)又高,不能不由衷佩服。論爭雙方開始坐到了一起,心平氣和地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于是“爭論和糾葛轉變到原則和理論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藝學說的介紹,那正是革命普羅文學的新的生命的產(chǎn)生”。一場論爭頓時煙消云散,迎來了中國革命文學隊伍第一次大團結的艷陽天!
創(chuàng)建“左聯(lián)”
隨著文學革命論爭的平息,建立一個革命的文化團體的任務,自然而然地提到了“文委”的議事日程上,擺到了潘漢年這位年輕的“文委”書記面前。
這個革命的文化團體就是后來蜚聲文壇的“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不過,“左聯(lián)”的成立,不是在這場論爭平息之后才開始醞釀和籌備的,而是經(jīng)過了一段較長的時間,“中國著作家協(xié)會”可以說就是“左聯(lián)”的前身,并為“左聯(lián)”的成立提供了經(jīng)驗。
從“作協(xié)”到“左聯(lián)”,潘漢年殫精竭力地使出渾身解數(shù),自始至終充當主角。
“作協(xié)”成立于1928年冬。10月間,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所屬的文化工作者支部書記的潘漢年,根據(jù)中央指示,找錢杏村和馮乃超商量,發(fā)起組織文化界的左翼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經(jīng)他們多方聯(lián)絡,在夏衍、朱鏡我、周谷城、許德衍等文藝界著名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是年12月30日,“中國著作家協(xié)會”在上海四川路廣肇公學召開成立大會,出席大會的共有90多人,大會選舉了鄭伯奇、沈端先、李初梨等9人為執(zhí)行委員,潘漢年為監(jiān)察委員。大會還通過了宣言,聲明成立“中國著作者協(xié)會”的目的在于“維護自己的生存”,“改善經(jīng)濟條件與法律地位”,并致力對“中國文化”的發(fā)揚與建設。
由于成立這樣的文化團體,對中國共產(chǎn)黨而言實屬初次嘗試,也由于潘漢年等人缺乏組織工作的經(jīng)驗,“作協(xié)”成立以后,沒有開展什么活動,形同虛設,不久便無疾而終。越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六屆二中全會。會議在提出停止“革命文學論爭”的同時,再一次提出建立文化界統(tǒng)一的革命團體的指示。大會之后,潘漢年立即著手籌建新的統(tǒng)一的文化革命團體。據(jù)阿英回憶,時間是在是年5、6月間,正是六屆二中全會召開前后,“潘漢年同志就同我談過中央打算成立一個組織,聯(lián)合左翼文藝界。潘強調要吸取中國著作家協(xié)會告吹的教訓,這次準備工作做得充分一些。”
潘漢年清楚地看到,要建立這么一個團體,關鍵在于要有一個主帥,而這個主帥又非魯迅莫屬,但魯迅與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的革命文學倡導者們又有門戶之見,因此,做好魯迅的工作,取得魯迅的諒解和支持,是潘漢年工作的重點。
此后,潘漢年代表黨組織,不僅自己登門求教,還多次派人與魯迅聯(lián)系,征求魯迅的意見。據(jù)馮雪峰回憶:“1929年10月、11月間,潘漢年找到我,要我去同魯迅商談成立‘左聯(lián)的問題。他同我談的話,有兩點我是記得很清楚的:一、他說,黨中央希望‘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和魯迅及在魯迅影響下的人們聯(lián)合起來,以這三方面的人為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二,團體名稱擬定為‘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看魯迅有什么意見,‘左翼兩個字用不用,也取決于魯迅,魯迅如不同意用這兩個字,那就不用。”
馮雪峰按潘漢年的吩咐,去同魯迅商談,魯迅對成立這樣一個革命的文化團體表示完全同意,同時他也認為用“左翼”兩字還是好的,這樣旗幟可以鮮明一點。
當時,魯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的一個弄堂里,常到北四川路一家日本人開的內山書店看書和約人談話。一次,潘漢年與吳黎平約定一起到那里去見魯迅,并取得了魯迅的同意。“不久,我們按約定的時間來到內山書店,見到了魯迅先生。在一間僻靜的房里,我們和魯迅先生談起了對于文學界現(xiàn)狀的估計和黨對左翼文化運動的意見,希望文化界同志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請魯迅先生在組織進步文化界同志的工作中多出力多指導。魯迅先生完全贊成我們的意見,對攻擊過他的同志表示諒解,認為他們心是好的,只是態(tài)度不對,并同意用‘左翼作家聯(lián)盟作為組織名稱。我們提議開一個會,專門把成立‘左聯(lián)的事情講一講,邀請魯迅先生出席講話,他十分高興地接受了邀請。”
魯迅的鮮明立場和積極態(tài)度,加速了“左聯(lián)”的問世。也正是由于工作上的聯(lián)系,魯迅與潘漢年之間終于建立了珍貴的友情。
在取得魯迅先生同意和支持的同時,潘漢年以極大的精力,親自過問“左朕”籌備小組的建立。他廣泛征求黨內外作家的意見,做好認真細致的思想發(fā)動工作,夏衍、阿英、吳黎平、馮雪峰、馮乃超、朱鏡我、洪靈菲…一文化界黨內作家、黨外進步作家,潘漢年一個個找到他們,傳達黨中央的指示,請他們出馬組建“左聯(lián)”。
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館樓上,由潘漢年主持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議推選了包括魯迅、鄭伯奇在內的12人,作為“左聯(lián)”的籌備工作小組。根據(jù)中央的指示,這一小組的主要任務是擬出“左聯(lián)”發(fā)起人的名單及起草“左聯(lián)”綱領。會議決定這兩個文件一經(jīng)擬出初稿,就先送魯迅審閱,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漢年送中央審查。
這次會議之后,“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遂進入了實質性的籌備成立階段。潘漢年因有其他的黨務工作,同時還要聯(lián)系成立其他革命社團組織,因此沒有參加“左聯(lián)”籌備小組的具體工作,但據(jù)夏衍回憶,這個12人的籌備會,每周召開的一次會議,卻是潘漢年主持的;在有關“左聯(lián)”綱領、發(fā)起人的名單、組織關系草案擬出之后,潘漢年不僅親自審閱、修改,而且還派專人報請魯迅先生審定。由此可知,籌備小組的工作實際上都是在潘漢年的指導下進行的。潘漢年為“左聯(lián)”的成立費盡了心血。
1930年2月26日,潘漢年以“文委”的名義,主持召開了籌建“左聯(lián)”的預備會議。地點是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靠近外灘路口的一座紅房子二樓。會議以茶話會的形式進行。參加會議的大約二三十人,魯迅到會并講了話。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清算過去”和“確定目前文學運動的任務”。據(jù)此,會議首先對過去文學運動中所存在的“小集團主義乃至個人主義;批判不正確,即未能應用科學的文藝批評的方法及態(tài)度;過去不注意真正的敵人,即反動的思想集團以及普遍全國的遺老遺少;獨將文學提高而忘卻文學的助進政治運動的任務,成為為文學而文學的運動”等嚴重問題,表示譴責。其次提出了目前文學運動的任務,認為最重要的有三點:一是“舊社會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現(xiàn)的嚴厲破壞”;二是“新社會的理想的宣傳及
促進新社會的產(chǎn)生”;三是“新文藝理論的建立”。會議一致認為有“將國內左翼作家團結起來,共同行動的必要”,并鄭重宣布:“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不久即將成立。
這次會議后,潘漢年即與籌備小組具體討論了成立大會的時間、地點,以及開會的程序、主席團的成員及分工,并由潘漢年匯報中央批準。
根據(jù)潘漢年的精心安排,成立大會的會場選在北四川路與竇樂安路(現(xiàn)多倫路)交界的中華藝術大學。“左聯(lián)”成立大會前一天,3月1日下午,潘漢年與夏衍等人一起到會場進行最后一次考察,布置安全保衛(wèi)工作。他們不僅對校內各個房間,而且對會場內外的每一個死角,都作了仔細的檢查。特別對魯迅的安全保衛(wèi)工作,潘漢年作了專門布置。潘告知夏衍,他在會場內外已經(jīng)安排了大約20個工人糾察人員,其中4個身強力壯的專門負責魯迅的安全。他說:“只要我們警惕可疑人物,會場的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證的。”潘漢年還關照夏衍,讓他告訴馮雪峰和柔石,“萬一緊急情況發(fā)生,讓他們兩個人陪著魯迅先生先從后門撤退”。從這里可以看出潘漢年對魯迅的愛戴!為了保障魯迅的安全,他的工作是多么的細致,其措施又是何等的具體、周密,體現(xiàn)了他在白色恐怖中足智多謀的戰(zhàn)斗風格。
“左聯(lián)”成立大會如期召開。馮乃超報告了大會籌備經(jīng)過;鄭伯奇對“左聯(lián)”綱領作了簡要說明;魯迅發(fā)表了《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的著名演講;潘漢年則代表黨中央出席會議并作了重要講話。這就是刊登于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上的《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義及其任務》一文。這篇“講話”是黨指導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文獻,對三十年代“左聯(lián)”的發(fā)展壯大具有深遠的意義,也是研究潘漢年文藝思想的重要材料。
“講話”首先剖析了“左聯(lián)”成立的時代背景。潘漢年認為,我們現(xiàn)正處在“一個舊有的經(jīng)濟基礎到了不可避免的動搖崩潰,而形成急劇的變革時期”,“城市的民族工業(yè)非但沒有發(fā)展的可能,且日見衰落倒閉”,“工人所遭受資本的進攻,愈見殘酷,隨之發(fā)生目前繼續(xù)不斷的罷工斗爭”;“農村經(jīng)濟的破壞,更為顯著,一般農民的貧窮化,失掉土地的貧農日漸增多,因此貧農與地主的斗爭更為深入,農民武裝的游擊戰(zhàn)爭,彌滿了全國。”“左聯(lián)”正是在這種“中國革命復興的浪潮,正在高漲發(fā)展”的歷史背景下成立的。
基于上述判斷,潘漢年進而說明“左聯(lián)”成立的意義:“這聯(lián)盟的結合,顯示它將(有)目的(有)意識的有計劃去領導發(fā)展中國的無產(chǎn)階級文學運動”;“加緊思想的斗爭,透過文學藝術,實行宣傳與鼓動而爭取廣大的群眾走向無產(chǎn)階級斗爭的營壘。”
接著,潘漢年又指出了“左聯(lián)”應有的任務:“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宣傳與斗爭”;“確立中國無產(chǎn)階級文學運動理論的指導”;“發(fā)展大眾化的理論與實際”;“自己陣營內工作的檢討與批判,將加強我們運動的成果”。最后,潘漢年強調說,上述所列舉的四點,“不過根據(jù)目前革命的階段,擇其要者而言。”
由于這篇講話是根據(jù)黨中央的指示精神發(fā)表的,因此,對當時文藝戰(zhàn)線,特別是對“左聯(lián)”的行動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左聯(lián)”的誕生,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史上樹起了一塊豐碑;潘漢年為此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也已留存青史。
“大同盟”與“總同盟”
潘漢年在調解革命文學論爭、籌建“左聯(lián)”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極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和超乎常人的組織能力,不僅博得了文化界同仁的稱譽和敬佩,也為黨組織所進一步了解,因此,黨中央對他加倍信任和重用。
就在“左聯(lián)”成立前夕,黨組織又把另一項重要的任務交給了潘漢年。
這件事情,與上海當時的整個形勢密切相關。大革命失敗后,一方面由于許多進步的文化戰(zhàn)士返回上海,上海成了繼“五四”運動之后新的文化運動的中心,加之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同時又有租界作掩護,這就為革命的文化運動提供了比較有利的客觀條件;但另一方面,上海又是國民黨反動勢力十分強大,控制十分嚴密,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地方。有鑒于此,黨中央準備以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為主體,聯(lián)合其他進步力量,以爭取自由為號召,成立一個革命團體: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央委派潘漢年、馮雪峰參與領導“大同盟”的組織籌備工作。
根據(jù)中央的意圖,潘漢年他們先去征求魯迅的意見,雖然魯迅不太同意這種做法,但還是表示愿意作為同盟的發(fā)起人。接著,潘漢年又派人找到鄭伯奇、田漢等人,也取得了他們的同意和支持。
1930年2月13日,在“左聯(lián)”成立的前18天,“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借公共租界的漢口路圣公會教堂召開成立大會。魯迅、潘漢年、馮雪峰、鄭伯奇、田漢等50人出席,魯迅和潘漢年作即席發(fā)言。會議通過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宣言》。《宣言》對國民黨專制統(tǒng)治和黑暗政治作了深刻而尖銳的揭露。
為了爭取自由,《宣言》號召所有感受不到自由而極為痛苦的人們團結起來,“團結到自由運動大同盟旗幟之下來共同奮斗”。
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由同盟執(zhí)行委員會作為領導機構,魯迅、潘漢年等21人為執(zhí)行委員。潘漢年還擔任了執(zhí)委會常委,同時又以文委書記的身份,兼任大同盟的黨組書記。“大同盟”成立伊始,即與“左聯(lián)”等文化戰(zhàn)線革命團體互相配合,積極參加和領導了當時的政治斗爭。在斗爭的實踐中,“大同盟”不僅進一步擴大和加強了自身的組織,并且擴大了影響,僅幾個月時間,在上海及南京、漢口、天津、北京、哈爾濱、廈門、香港、廣東等地,紛紛建立分會,最多時達50余個。
毫無夸張地說,三十年代革命文化領域的條條戰(zhàn)線上,都印著潘漢年的足跡,留著潘漢年的心血和汗水。
“中國左翼戲劇家聯(lián)盟”是在潘漢年的幫助指導下誕生的又一個革命文化團體。
1928年春,當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倡導者們,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中高舉革命旗幟時,話劇界也開始了對無產(chǎn)階級戲劇運動的提倡。翌年秋,鄭伯奇、陶晶蓀、馮乃超、沈學誠等人開始籌建上海藝術劇社,剛剛出任“文委”書記的潘漢年了解了這一情況后,立即委派夏衍去過問,并參加了“藝術劇社”的籌備工作。
是年10月下旬,“藝術劇社”在北四川路永安里“文獻書店”正式成立。潘漢年出席了成立大會。“藝術劇社”以鄭伯奇為社長,沈全苓為總導演,許幸之負責美工,夏衍和馮乃超負責宣傳。參加者還有錢杏村、孟超、朱光、石凌鶴、陳波兒、司徒慧敏等人。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第一個左翼戲劇團體。潘漢年對此十分重視并寄于厚望。他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予以指導,還從多方面對這個組織進行關心幫助。為了解決演出的經(jīng)費問題,潘漢年曾親自捐獻了二三十元大洋。“藝術劇社”成立后不久,即與摩登劇社(由原南國社的左明、陳白塵等組成)聯(lián)合發(fā)起,聯(lián)合南國、辛酉、
戲劇協(xié)社等戲劇團體,成立了上海劇團聯(lián)合會。1930年8月,經(jīng)潘漢年與夏衍、馮雪峰、鄭伯奇、田漢等人商量,在上述團體的基礎上,成立了“上海左翼劇團聯(lián)盟”,該組織不久又改名為“中國左翼戲劇家聯(lián)盟”。
“劇聯(lián)”問世后,在介紹進步的戲劇理論,開展左翼戲劇的創(chuàng)作、演出活動,成立工人藍衫劇團,組織為工人、學生、農民演出的移動劇團,推動進步電影事業(yè)的發(fā)展等諸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劇聯(lián)”成了在三十年代有重大影響、分盟遍布各城市的左翼文藝團體。
“中國社會科學家聯(lián)盟”的籌建工作,也是在潘漢年的關心指導下進行的。據(jù)馮乃超回憶,1930年3、4月間,潘漢年出席了“社聯(lián)”的第一次籌備會。這次會議是在鄧初民家里召開的。除鄧初民本人之外,與會者還有吳黎平、朱鏡我、錢鐵如、寧敦伍、王學文和馮乃超等10余人。會議主要討論了成立“社聯(lián)”的具體事項。
5月20日,潘漢年參加了“社聯(lián)”的成立大會,并代表籌備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潘在報告中要求“社聯(lián)”通過出版刊物、書籍,組織研討會等形式,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國內外政治經(jīng)濟形勢,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駁斥非馬克思主義思潮,有系統(tǒng)地領導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興社會科學運動的擴大、深入與發(fā)展。根據(jù)潘漢年的講話精神,大會討論并通過了“社聯(lián)”綱領。綱領指出,“社聯(lián)”的宗旨是“團結光大和發(fā)揚革命的理論,以應用于實際”。提出了“社聯(lián)”的主要任務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中國及國際政治經(jīng)濟,促進中國革命”;“研究并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統(tǒng)地領導中國的新興社會科學運動的發(fā)展,擴大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
此后,潘漢年又對“社會科學研究會”、“中國左翼美術家聯(lián)盟”、“書業(yè)職工會”等左翼文化團體,進行具體的幫助指導。潘漢年與文化界各個系統(tǒng)的左翼團體,結下了不解之緣。
為了進一步統(tǒng)一和加強對革命文化的領導,以適應新的形勢發(fā)展的需要,1930年8月26日,由“左聯(lián)”發(fā)起,召開了包括各個系統(tǒng)的左翼文化團體參加的代表大會,莊嚴宣告“中國無產(chǎn)階級文化總同盟”的成立。會議推舉“左聯(lián)”、“社聯(lián)”、“左美”、“左劇”、“書職”等團體組成執(zhí)行委員會。潘漢年順理成章地被任命為“文總”的第一任黨團書記。“文總”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chǎn)黨在文化戰(zhàn)線上已經(jīng)建立起了一個從中央文委到“文總”再到各個系統(tǒng)左翼文化團體的垂直的組織系統(tǒng)。1929至1930年之間,潘漢年成了這個系統(tǒng)中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導者、革命斗爭的組織者,是這個系統(tǒng)各級組織的核心領導。
從1928年至1930年,是潘漢年投筆從政,由文化人向職業(yè)革命家轉變的三年;也是他政治上逐步成熟并取得顯著成績的三年;又是他從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世界觀轉向無產(chǎn)階級世界觀的三年。
潘漢年曾經(jīng)說過這樣一句話:“我雖愛好文學,但沒有功夫研究文學;我喜歡寫作,但我不想成為什么家。”當他從政之后,他發(fā)現(xiàn)自己找到了比文壇更好的用武之地。盡管許多人贊賞他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是個文思敏捷的多產(chǎn)作家,并為他過早地離開文壇而感到惋惜,但在他未來20多年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可以得到驗汪,他的選擇是正確的。當然,作為共產(chǎn)黨人,他還得服從組織上的安排,聽從黨的指揮。黨分配給他的戰(zhàn)斗崗位,就是他更好地施展自己才能的廣闊天地
1931年初,潘漢年奉調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不到兩個月,組織上決定調他到中央特科工作。時代和機遇,從此把他推到了黨的隱蔽戰(zhàn)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