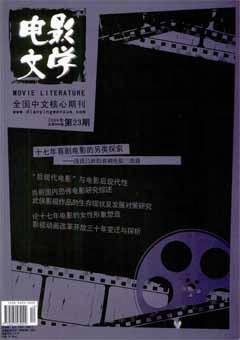近十年來電影《羅生門》研究述評
張奚瑜
[摘要]多年來,人們為傳統的一元化本質觀的思維方式所蒙蔽,總是以世俗的眼光去探討《羅生門》中所謂的“事實的真相”,總是認為這個故事中“事實的真相”只有一個,并想通過“事實真相”竭力去給故事或人物加載某些道德上的評價。近lO年來,電影《羅生門》在中國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研究者圍繞影片的主題思想、藝術特色等展開了詳盡的分析,為我們進一步深入理解《羅生門》提供了多維視角。
[關鍵詞]《羅生門》;黑澤明;主題;藝術特色;研究述評
黑澤明重新創作、導演的《羅生門》是一部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作品。繼榮獲1951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大獎后,第二年《羅生門》又榮獲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為日本電影登上世界影壇起了開路先鋒的作用。也因為《羅生門》的巨大成功,黑澤明一舉成名,從此奠定了他在日本電影史乃至世界電影史上的重要地位。日本電影理論家巖崎旋在他的專著《日本電影史》中說,“這部日本戰后電影的杰作,使日本電影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近幾十年來,尤其是近10年,中國的研究界圍繞作品的思想主題、藝術特色等展開了形式多樣的深入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本文試做簡單的歸納。
一、《羅生門》的思想主題
《羅生門》于1950年完成。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的神話崩潰。舊有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以至到達崩潰的邊緣,懷疑主義、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盛行,因此,它的問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日本的社會現實。吳海清從英雄的道德化、歷史的象征化、敘事的儀式化和生存處境的荒涼化等角度指出,以《羅生門》為代表的黑澤明電影,其實是在書寫日本民族的現代寓言。黑澤明創作的英雄史,事實上是從救世到失敗的英雄史,是從自信到懷疑的心靈史,是個人主義與否定意識不斷加強的精神史,是英雄越來越與世俗和時代分離的孤獨的生存史,也是重塑民族精神譜系的寓言敘事越來越被現代性話語不斷拆解和質疑的歷史。這一精神歷程與日本文明的現代化進程是相伴相隨的:黑澤明的英雄失敗史正是日本物質與技術文明不斷膨脹而精神不斷失去根基的歷史;黑澤明從自信走向懷疑的時候正是日本試圖脫離亞洲文明并入歐洲文明、重新書寫甚至抽空日本歷史的時候;而黑澤明絕望的、抗爭的個人主義與否定意識發展的歷史正是日本虛偽的、庸俗的、實用的個人主義盛行的歷史。…吳海清進一步指出,這種民族寓言與現實語境的分離給黑澤明影片造成了許多裂縫:英雄理想與世俗話語、個體追求與體制整合、人文關懷與技術理性、語言表達與生存真實、普遍理念與民族文化,等等。…從歷史角度解釋《羅生門》的價值意義的觀點,無疑是富有見地的。
不過《羅生門》之所以獲得世界影響,不僅僅在于它反映了日本的現實,更在于它揭示了人類的普遍困境。與從民族寓言的宏大敘事的角度提煉《羅生門》的主題不同,魏莉莉則從歷史與現實的關系角度入手認為,電影文本不僅僅被動地“反映”這一歷史,它也參與到歷史之中,“介入”和“生產”歷史。它“生產”出整個人類歷史,這個影片從更深層次上反映了人類身上的一些卑劣的本性,如自私、虛榮、欺騙、狠毒、貪婪、怯懦等形形色色的本性;它不僅僅是當時社會背景的反映,更是整個人類生活狀況的一個突出的縮影!周興杰也認為,黑澤明用電影語言消解了歷史話語的霸權地位。影片《羅生門》中的爭訟表明:揭示歷史的真相只是大眾的癡心妄想。影片中敘述者們提供的就是四個充滿歧義、相互矛盾的個人歷史文本,對歷史真相的言說反而表明,對歷史真實性的關切最終只是一場空。邱紫華認為,《羅生門》的價值在于它表現了作品中的人物,“在個體意識的驅動下,面對自己的生命的苦難和毀滅,面對自己‘意識和欲望超出自己能力的絕境,以及在動機與結果悖反的反因果境遇時的人生態度,揭示“個體與社會、環境、自然之間的對立與沖突,展現出受自己意志、欲望所驅使的行為過程以及這種行為受到阻礙的毀滅結果”。
從哲學高度探析《羅生門》的意義,是近年來研究的一個新的動向。多年來,人們為傳統的一元化本質觀的思維方式所蒙蔽,總是以世俗的眼光去探討《羅生門》中所謂的“事實的真相”,總是認為這個故事中“事實的真相”只有一個,并想通過“事實真相”竭力去給故事或人物加載某些道德上的評價,想在人物中區分出誰善誰惡、誰對誰錯、誰高貴誰卑賤等等。邱紫華認為這種做法不妥,他從哲學的角度概括了黑澤明所要表達的哲學理念一真理都是相對的,任何真理只是有限范圍內的真理;沒有絕對的、客觀的真理,因緣和合才是事情的本真。王文平從生命意識、超越動機、動機與效果悖反、兩難境地等幾方面闡述《羅生門》思想的悲劇性——人對自身命運的無法把握,人只能被動地卷入尖銳的矛盾沖突,陷入苦難的境地,顯示出兩難處境的特征。杜剛認為,《羅生門》蘊藏著對人性、對客觀真理的不信任、疑惑甚至絕望。”
馮志宏認為,《羅生門》向人們展示了生活的多種可能性!真正把握住了電影一如人生的幻象本質,把所有的故事做到最假、最虛妄,最后你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一切就是真相。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四個故事里找到自己生命的真相。與大多數研究者從正面肯定《羅生門》的意義不同,傅紫瓊則指出,《羅生門》中因強烈的道德批判色彩而可能帶來表達的武斷褊狹的缺點。她指出,《羅生門》過于強烈地透露出一種求解或作結的企圖,讓電影一面倒地服從此企圖,其原本多層次的結構,就會坍塌成一個“單音獨鳴的觀點”。電影流于武斷褊狹,于是在觀眾的納悶與隱隱不安中,結束電影。這不得不說是電影中的一個失敗點。
二、《羅生門》的藝術技巧
《羅生門》之所以能贏得世界聲譽,與其開創的獨特的藝術技巧不無關系。關于《羅生門》的結構,李寒陽認為,《羅生門》的敘事可以分為兩個層次:在羅生門下避雨的賣柴人、行腳僧和打雜的講述、議論構成超敘述層次,在他們的轉述中出現的強盜、女子和鬼魂(由巫婆代表的武士)的敘述構成主敘述層次。而賀忠則認為,敘述者本身也是不可靠的。在電影中,我們看到了人性虛偽的種種表現,羅生門下的兩位敘述者行腳僧、樵夫的敘述是第一層次,包括行腳僧及樵夫的7個人的行為是第二層次。問題是,不僅第二敘述層次中武士鬼魂的獨白不可靠,就連第一層次的敘述者本身也未必清白。因此,整個敘述可稱是幻像之幻像。更形象一點說,更像是在看經過兩面鏡子折射后的影像。在黑澤明這部作品之前的電影,主角與配角界限分明,但在《羅生門》中,情況變了,每一個敘述者都是主角,沒有輕重之分,導演站在超然的立場,把每一位敘述者都看成事件的主角,平等地分配鏡頭,讓每一個角色有均等的機會來說服觀眾,觀眾由此產生各種永遠不會有結果的猜想。杜剛認為,故事的“多重聲”敘述造成對事件本來面目的多種解釋,使觀眾始終不能斷定究竟誰講述的是事實真相,使故事的含義始終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狀態
中,突出了故事的多義性。
凌振元認為,運用多視角創作方法建構一個故事;巧妙運用快速跟拍、靜態特寫鏡頭;成功運用了表情的近拍特定鏡頭;豐富的影像含義。這些是《羅生門》在技巧上獲得成功的四大特色。
在藝術風格上。賀忠認為,《羅生門》建構了一種死亡美學。黑澤明在電影中表現的死亡是對生命的思考,是借助死亡表現人的本性。《羅生門》所揭示的死亡美學,把死亡看成是惟一的美,惟一屬于自己的美。死并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生命中美的新發現,死就像無瑕的雪、平靜的湖、靜謐的森林、純潔的櫻花、黑夜的火花……是大自然的一種美的形式,是需要心靈去尋找的永生。用死來證明這種追求的眾多日本作家,使得這種死亡美更具震撼力。《羅生門》在細節的處理上也非常獨到,比如背景音樂的運用就非常巧妙。凌振元認為。在影片四個人的敘述中,強盜、武士、妻子三個人的敘述是在一定的音樂背景下進行的,是配著音樂敘述謀殺案的,它們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這是主觀視點的敘述,是不真實的、不可信的;而賣柴人的敘述沒有背景音樂,不帶有主觀情緒色彩,說明他的敘述是客觀的、是真實可信的。
正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的哈姆雷特。黑澤明在影片結尾的處理,歷來爭議很大,學界有不同的闡釋。對于《羅生門》影片結尾,黑澤明安排了賣柴人收養棄嬰的細節,魏莉莉認為,嬰兒的偶然出現并不是毫無意義的,不僅如此,他也是整個陰沉昏暗的影片惟一的一抹亮色。他的出現,喚醒了人類最本真的本性,人并不是如整個兇殺案反映的那樣自私,互相欺騙,無法拯救。雖然這個偶然事件的出現在整個影片中所占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似乎如前所說顯得蒼白無力、單薄,而且似乎有些說教的感覺。但是這正是黑澤明一貫的人文主義理念的流露。凌振元也指出,這個細節宣揚了人道主義永存的觀念,說明黑澤明在影片最后是進一步強化了人是可以相信的觀點。楊春認為,黑澤明將拯救的希望賦予在民間歷經痛苦掙扎的樵夫,而非悲憫的僧人,這是民間力量的一次自我拯救。影片結尾處在一個羅生門的全景鏡頭之后畫面定格為殘缺一角的特寫鏡頭,無不傳達著這樣的信息:拯救始于殘缺處。何莉瓊認為,影片的結尾,通過樵夫懺悔并收養棄嬰,揭開了人性光亮的面紗,將言辭的立場從欲望轉移到善,即社會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