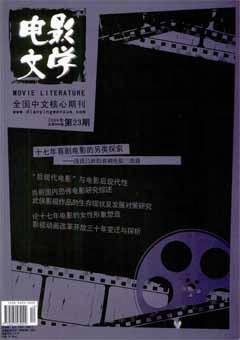論張愛玲小說的電影改編
儲 瑤
[摘要]張愛玲的文字小說讓世人著迷,人們甘之如飴地在她的字里行間找尋著謎一樣的世情和糾結著的玩味人生。而電影畫面技巧、蒙太奇的利用、鏡頭的多樣切換、音樂的合成、色彩的運用、演員的深度再創作都拓展了張愛玲小說敘事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審美新趣。
[關鍵詞]張愛玲;電影改編;再現
一、張愛玲小說的改編概述
張愛玲一生著有18篇短篇小說、10篇中篇小說、4部長篇小說,散文、小品文近百篇,張愛玲的文字小說讓世人著迷,人們甘之如飴地在她的字里行間找尋著謎一樣的世情和糾結著的玩味人生。
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內地及港臺地區的影視導演們和劇作者們便將目光集中在了這位奇女子身上,張愛玲作品經久不衰地在各色各樣的舞臺上刮起一股改編的熱力旋風,影視界因其風生水起:中篇小說《怨女》《紅玫瑰和白玫瑰》、短篇小說《色·戒》先后被改編為電影;中篇小說《金鎖記》分別被改編成電視劇和話劇;中篇小說《傾城之戀》分別被改編為電影、話劇、歌舞劇、廣播劇;長篇小說《十八春》改編成名為《半生緣》的電視劇、電影、歌劇、音樂話劇。
二、電影緣何鐘情于張愛玲
從形形色色的藝術改編來看,其中最值得研究的便是電影對于張愛玲小說的改編和演繹。為何這些改編者都如此青睞張愛玲作品,歸結幾點原因:
(一)小說的電影化
張愛玲天生與電影有著一種解不開的淵源,張愛玲對于電影的熱愛也潛移默化地融入到了她的小說創作中去,使其小說不知不覺中具有了電影藝術的某些特征。
張愛玲也是一個無師自通的“導演”“攝影師”和“服裝造型師”,在她的小說里,我們可以發現很多天然的電影元素和影視技法,仿佛她的小說就是為電影演繹而生成的,她將小說和電影這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渾然天成地融為了一體,兩者通過張愛玲的天才手筆達成了一種審美的聯結,體現了一種極力與電影藝術溝通的文學精神。我想稱其小說為“紙上電影”。
1蒙太奇的創作手法
電影美學家貝拉·巴拉茲說過:“蒙太奇是電影藝術家按事先構想的一定順序,把許多鏡頭連接起來,結果就使這些畫格通過順序本身而產生某種預期的效果。”蒙太奇作為電影藝術基本的表現技巧的結構手段,被稱為電影靈魂。而張愛玲的小說中隨處可見各式各樣的蒙太奇技巧,《金鎖記》里有一段經典的“蒙太奇剪輯”
風從窗子里進來,對面掛著的回文雕漆長鏡被吹得搖搖晃晃,磕托磕托敲著墻。七巧雙手按住了鏡子。鏡子里反映著翠竹簾子和一副金綠山水屏條依舊在風中來回蕩漾著,望久了,便有一種暈船的感覺。再定睛看時,翠竹簾子已經褪了色,在金綠山水換了一張他丈夫的遺像,鏡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這段描寫直接就給改編者提供了現成的鏡頭組成的場面單元,十年的時間,在張愛玲的筆下用一種近似蒙太奇剪輯的影視手法給予了巧妙過渡,類似鏡頭跳躍式的切換直接就完成了時空的轉換,堪比“好萊塢的流暢剪接”,張氏獨有的生花妙筆,怎能不讓現代電影趨之若鶩!
2色彩的充分運用
現代電影對色彩是非常重視的,電影人將色彩作為影視藝術中的視覺語言元素進行深入挖掘。色彩的變化和運用不僅形成影片的整體基調及調節整體氛圍,還可以表現人物的情感和心理,并且還體現時空轉換,具有隱喻、象征的敘事功能。而在電影還是舶來品的年代,張愛玲儼然是一位資深畫家和攝影家,在小說中把色彩的運用推向了極致,無論是自然景色、房屋建筑還是屋內陳設、服飾裝束都被她加之重墨濃彩,學者吳福輝在文章《新市民:傳奇:海派小說文體與大眾文化姿態》中曾對張氏小說中的色彩做過不完全統計,16段描寫景物或女人的文字中有9l處用了帶色調的詞匯,其中紅色23處,白色14處,黃色14處,綠色12處,金色8處,藍色7處,紫色4處,黑色4處,米色2處,銀色1處,栗色1處。
(二)小說改編有戲、有賣點
張愛玲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她的小說大都比較傳奇,描寫的大多是上海沒落淑女的傳奇故事,且具有通俗化、女性化、商業化的特點,其骨子里透露出來的小資情調也迎合大眾的通俗口味,而且注重心理探究,很“有戲”,非常適合改編成電影。另外,她的小說中那種唯美、傲然喧囂、臨花照水的女性形象、對人生滄桑的寫照和濃郁風味的“雙城”都市風情(上海和香港),都非常具有“賣點”,是不可能被電影人所忽視和冷落的。學者溫儒敏認為:張愛玲熱從上個世紀持續到今天,而且現在電影編導還是那么熱衷于張愛玲,主要還是因為有票房需求。正是由于張愛玲文字的這種獨特魅力,使得全球最頂尖的導演都為之魂牽夢繞,改編了一次又一次,這些改編者都有揮之不去的張愛玲情結。
三、張愛玲小說改編電影的分析
1984年香港女導演許鞍華首次將張愛玲中篇小說《傾城之戀》搬上了電影銀幕;1988年香港導演但漢章改編電影《怨女》;1994年香港導演關錦鵬執導的電影《紅玫瑰和白玫瑰》,改編自張愛玲同名小說;1997年導演許鞍華拍攝電影《半生緣》改編自張愛玲的長篇小說《十八春》;2007年導演李安執導的電影《色·戒》改編自張愛玲的短篇小說《色·戒》。從這二十余載電影改編路程來看,每一個改編者都在經受著巨大的考驗,也許每個改編過的電影人都會對張愛玲發出這樣的感慨:走近你就走近了痛苦,離開你就遠離了幸福。
以《傾城之戀》《半生緣》《色·戒》三部電影為例來分析張愛玲小說的電影改編,從“十年一改”中我們來窺其一斑。
(一)電影改編的得與失
1忠實原著的追隨,如履薄冰的謹慎
這三部影片無一例外地追求對原著高度的忠實,特別是在主線故事情節和人物主次上不隨意地更改和增刪。更準確地表達,應該說他們都不是考慮如何改編而是如何再現張愛玲作品的內在,但這恰恰是改編中的最難點,因為閱讀小說文本形成的審美高峰體驗先入為主,因為張愛玲小說主要擅長于人物心理的描寫、心緒的意會而非曲折動人的故事情節設計。
三部影片雖然是十年一改編,改編者也是慎之又慎,但一上映,都逃脫不了毀譽參半的命運,在影視批評尚不成熟的年代能給予電影人客觀評價和寬容少之又少。
2視覺藝術的新感觀,電影改編的多亮點
從電影改編后的硒面技巧、蒙太奇的利用、鏡頭的多樣切換、音樂的合成、色彩的運用、演員的深度再創作來看都打破了小說的敘事局限,帶來前所未有的審美新趣,這兩種不同文學樣式。
《傾城之戀》小說中張愛玲用了這么一段話來開頭:“上海為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個小時,然而白公館里說:‘我們用的是老鐘。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胡琴咿咿呀呀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胡琴上的故事應當由光艷的伶人來扮演的,長長的兩片紅胭脂夾住瓊瑤鼻,唱
了,笑了,袖子擋住了嘴……”,電影中許鞍華用了一段只有音樂沒有唱詞的昆曲作為影片的開頭。戲臺上男伶與女伶相遇、糾纏。這段表演隱喻(電影的一種表現手法)著電影所要展現的是一段男女愛情故事,戲臺上兩個“光艷的伶人”(一男一女)兩分十五秒的無聲表演奠定了整個電影的基調。印證了劇中白流蘇與范柳原的愛情周旋,不是情竇初開的熱烈相戀,像戲臺上伶人所表演的一般他們之間仿佛是一場較量,互揣心思,舉步思量,欲拒還迎。接著是一組蒙太奇鏡頭:戲臺下一個小女孩(從后面白流蘇回憶的一場戲可知小女孩正是白流蘇)的臉部特寫,特別是那雙看戲專注的眼睛,轉而隱去承接出女主人公(成年后白流蘇)低著頭坐在古色古香的椅子上,旁邊是一盞紅燈罩的煤油燈,鏡頭慢慢拉開,呈現白公館的生活場景……
電影開頭敏感地抓住了可以搬上銀幕的“光艷的伶人”的意象,避開了張愛玲式的細膩、復雜的對“蒼涼”世事的心緒。張愛玲式的敘述從影片一開始就退去,影片選擇一段隱喻式的昆曲表演直奔點明故事主題。同時也增加了兒時的流蘇看戲這么一個鏡頭,為流蘇后來的命運埋下了伏筆,也強化了流蘇心理、性格的刻畫,這在小說中是沒有的。兒時看戲純真、憧憬的眼神的流蘇與成年后第一次感情婚姻失敗的流蘇形成鮮明的對比,孩童時的流蘇看戲的眼神很專注,仰著頭。給影片觀眾的信息是她也許在憧憬、在想象美好的男女之情,在旁觀別人的命運。成年后的流蘇卻要歷經了一次失敗的婚姻,在當時世風封建的時代,她勇敢地選擇了離婚。影片開頭便刻畫了一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執著的白流蘇。
影片超越于小說的一處成功發揮,便是色彩的大膽運用。顧曼楨的那雙紅色絨線手套。在小說里,只是說三人郊游歸來,顧曼楨念念不忘丟了一雙手套,沈世鈞回去找也沒找到。到了電影里,沈世鈞先是傍晚獨自打著手電筒找到了其中一只。最精彩的是到了影片結尾,十八年過去,二人重逢之后只剩下無奈。沈世鈞再一次獨自打著手電筒回到郊游的故地,在角落里發現了另一只手套。全片的最后一個鏡頭就是那只手套的特寫,在從頭到尾的清冷色彩中突顯這一塊鮮紅,令人觸目驚心,這一只遺落了十八年,即使重新找到,也湊不到一對的紅色手套,再一次強烈地激起了觀眾心理對那句“世鈞,我們回不去了!”無奈和傷感的共鳴。
而《色·戒》的亮點在于以往改編張愛玲小說那種全盤照搬的超越,李安拍《色·戒》的方式,與此前所有導演都不一樣。他只拿了張愛玲的框架。雖然他用的是張的臺詞、情景。但是李安用來講自己想講的事情。
(二)二十年改編之路的逐漸成熟
從這三部電影改編可以看到,同一個改編者對張愛玲作品的把握更加準確,再現更加靈活。
橫向比較上,電影《傾城之戀》《半生緣》都是由香港女導演許鞍華執導,十年前后,由最初的完全照搬原著,大量使用字幕和旁白到跳出拘泥原著的突破改變,在從文字到影像的轉換過程中,能夠看到許鞍華的苦苦心思和孜孜不倦。
許導的后來一部張愛玲小說《半生緣》的改編在選取演員、再現原著、電影技巧上都有了一個很大的提高和突破,張愛玲那冷漠的筆觸在電影《半生緣》中被許鞍華轉換成一種冷漠的影調。上海自來就給人風情別樣的繁華印象,但是許導卻特意選擇在上海的冬天拍攝。全片從頭到尾淡化了季節的轉換,男人們永遠裹在厚厚的風衣里。成為舊上海標志的旗袍,也一次都沒有穿在劇中女人們的身上。
改編的成熟還可見于《半生緣》的選角上。《傾城之戀》中,周潤發演范柳原,而上海人、港姐出身的繆騫人演白流蘇。繆騫人的長相偏于硬朗,并不符合白流蘇“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的形象。影評人陳耀成評價周潤發演的范柳原是“還可以”,而繆騫人演的白流蘇則是“慘不忍睹”,認為她的表情一直“介于惶恐與空白之間”,與許鞍華“一起崩潰”了。《半生緣》中,飾演沈世鈞的是黎明,飾演顧曼楨的是吳倩蓮,而顧曼璐則是梅艷芳,幾個主角的演員都非常符合原著人物形象和氣質。
縱向比較上,又一十年后的《色·戒》不僅超越了張愛玲原著文本,李安還超越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