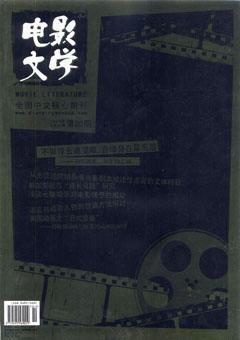出走與回歸
符亦文
[摘要]《佛洛斯河磨坊》是英國作家喬治·愛略特最具自傳性質的小說,它自問世以來便廣受贊譽。但是,評論家們對其中瑪姬和表妹露茜的未婚夫斯蒂芬出走這章卻一直眾說紛紜,質疑的焦點主要集中予以下三點:瑪姬為什么會出走?瑪姬為什么同斯蒂芬出走?瑪姬出走后為什么又閃電返回?本文試圖通過對瑪姬個性和艾略特創作手法的分析以及作者本人和瑪姬的比較,對以上三個問題做出回答。
[關鍵詞]喬治·艾略特;瑪姬;沖突;心理;倫理
《佛洛斯河磨坊》(以下簡稱為《佛》)是英國作家喬治·艾略特最具自傳性質的小說,它以其細膩、婉約的描寫和幽默、機智的語言對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進行了生動的描寫。小說自問世以來便頗受贊譽,但小說中女主人公瑪姬和表妹露茜的未婚夫斯蒂芬出走這章卻一直遭到評論家們的質疑,圍繞于此的評論也從來沒有中斷過。例如,在評論家萊斯莉·斯蒂芬看來,瑪姬和斯蒂芬的感情糾葛,特別是他們的出走是一種“不相干又不相稱的墮落”。一向對艾略特推崇至深的文學泰斗利維斯也不無遺憾地表示認同。瑪姬為什么會出走?為什么會和斯蒂芬出走?而出走后又為什么閃電返回?本文試圖通過對瑪姬個性和艾略特創作方法的分析及作者本人與瑪姬的比較對以上三個問題做出回答。
一、瑪姬為什么會出走
瑪姬的出走可從其叛逆的個性以及個人追求與傳統習俗的矛盾兩方面加以闡釋。
瑪姬的叛逆在小說一開始就已有所展露。這一點可在媽媽塔利維夫人對女兒的描述中得到佐證,在她看來女兒性格倔強得和一頭“野物”沒什么分別:“……她天生是個直頭發黑眼睛的姑娘……那頭發從紙卷里出來不到一小時就直了,她就只好不斷地晃動腦袋,不讓那濃密的黑發遮住她那雙閃亮的黑眼睛——整個動作使她非常像匹射特蘭小馬。”這傳遞給我們許多信息:首先,瑪姬的一頭黑發使她明顯不同于家族中的其他成員;再有,她的頭發還生就一種寧折不彎的性質。對頭發如此濃墨重彩的鋪墊只為順理成章地得出“她非常像匹射特蘭小馬”的結論,亦即瑪姬非但不是一個乖巧的小女孩,而且她的言行舉止還活脫脫沾上了些許“獸性”。
天性叛逆,易失去理智的瑪姬盡管長大后出落得亭亭玉立,言談舉止也頗具淑女風范,可那被壓抑的怨恨總會“像火山熔巖一樣淹沒了她的柔情和良心。”嚴格的宗教道德標準無法壓制她過人的精力和才智,更無法撫平她內心的情感和矛盾,這股暗流一直在待機而動,直至斯蒂芬的出現直接導致了瑪姬叛逆天性的復蘇。
可促成瑪姬出走的另一原因卻是她無法緩和或消解自身同所處環境的矛盾。“格格不入”貫穿著她成長經歷的始終,也成了她生活中揮之不去的陰霾。幼年時,她怪異的外貌和乖張的性格一直得不到媽媽和姨媽們的認可;旺盛的求知欲以及同她年齡不相稱的“博學”也使她不能見容于所處的環境。父親塔利佛的一番高論頗值得我們深思:“……聰明的女人就像長尾巴的羊,尾巴再長也不能多賣錢。”把女兒視為掌上明珠的父親在欣喜之余不免有些許遺憾,因為在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聰明才智無用武之地,她們的職責是做好“家庭中的天使”;再者,工業生產的狂飆突進使婚姻更像是一場交易,而女性則淪為婚姻市場中待價而沽的商品,聰明非但不會提升她們的價位,反而會成為阻礙她們獲取幸福的絆腳石。成年后的瑪姬根本無法融入閉塞的圣奧格鎮——在那里宗法習俗統治著人們的言行,教堂布道和生活的歷練就是他們教育的全部;文娛活動貧乏,鄰里間的飛短流長點綴著波瀾不驚的生活。“你要是在這樣的人群中是無法生活的;你會因為無法跟某些美好、偉大、高尚的事物相通而感到窒息。”痛苦的瑪姬游走在現實與幻想之間,忙著在現實之外構建屬于自己的“小天地”和“避難所”;于是瑪姬“在不太寒冷的雨天最喜歡往閣樓里躲”,因為在那兒她可以“……大喊大叫,發泄一肚子的不高興……”她還喜歡去磨坊找仆人路加聊天,因為“磨坊是她日常生活外部的小世界。”在哥哥冷落她后,她竟一時興起,逃往吉普賽人營地,因為她天真地認為那里才是屬于自己的王國,原先受到的冷遇也都會在那里得到補償;家道中落后,苦悶無依的瑪姬又開始在湯瑪士·阿·肯丕斯的理論中尋找精神寄托,徜徉在自己構筑的世界里。還是母親塔利維太太一語道破了天機:“我肯定那孩子在有些問題上是個半白癡,如果我打發她到樓上去拿東西,她總會忘記是去干什么的,說不定就會坐在太陽光里的地板上。梳起小辮來,只顧自己唱著歌,像瘋子一樣,讓我在樓下好等。”這番話更讓我們見識了一個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不能自拔,很享受“精神出走”的瑪姬,而正是這種“精神”上的頻頻出走為之后她在現實中的真正出走預設了最有力的前奏。
二、瑪姬為什么同斯蒂芬出走
斯蒂芬這一人物的刻畫一直為許多評論家所詬病。L·R·利維斯曾指出:“……斯蒂芬·蓋斯特是喬治·艾略特筆下一個可悲的疏忽。”他還被評論家們冠以“花花公子”之名,因為他們認為秀外慧中的瑪姬對這樣的“土鱉紈绔”一傾芳心簡直是不可思議。萊斯莉·斯蒂芬覺得這是“喬治·艾略特不會描寫男性的又一力證……”:而弗吉尼亞·沃爾夫則把它歸咎于“艾略特從不知道怎樣為她的女主人公找一個合適的伙伴”。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可我們恰恰忘了喬治·艾略特有別于同時代其他作家的除了博學,還有她在創作中對人物心理描寫的率先嘗試。以此為觀照就不難發現上述觀點不免有失公允,因為安排瑪姬同斯蒂芬出走符合她一路走來的心理成長軌跡。
小時候的瑪姬盡管是父親的掌上明珠,可母親的不了解和姨媽們的不欣賞使她的整個孩提時代都在“拒絕”中度過,這使她內心總是升騰著被人憐愛和崇拜的渴望。為了得到所需的愛,她會表現得過分謙卑和過度“慷慨大方,自我犧牲”,希望借此尋求與人為善,表現愛心,最終得到他人的愛。為了鞏固所需的愛,在欣賞她的人面前,瑪姬總是“很少堅持自己的權利,也很少有自我保護的舉動……”對于欣賞她的腓力浦是如此,對于愛著她而自己又同樣愛著的斯蒂芬更是如此。就這樣,不懂拒絕的瑪姬輕易就接受了腓力浦的愛情,盡管她深知“腓力浦打動她的更多是憐憫之情和女性的奉獻精神”,只是她實在太需要延續或擁有被人接納和疼愛的感覺;就這樣,不懂拒絕的瑪姬輕易陷入了斯蒂芬的情網,為了鞏固所需的愛,她拖著自己的腿,頂著已被感情沖昏的腦袋踏上了斯蒂芬的船。
但是她希望被愛的防御機制總是受到表妹露茜的威脅。露茜漂亮、整潔,招人喜歡,這同瑪姬胎巧相反。露茜一出現,便可以把本來停留在瑪姬身上少得可憐的注意力全部轉移掉,因此,露茜一直以來都是她嫉恨的對象,小時候把她推到爛泥里只是一曲前奏。長大后的瑪姬和露茜相處得還算融洽,那是因為她身上“各種攻擊性傾向都受到強烈壓抑”,那份妒忌被很深地掩蓋起來,但它還是不自覺地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當腓力浦看到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瑪姬時,開玩笑地、兌瑪姬能夠把露茜的崇拜者全部吸引走時,她頓時感到一種震顫的喜悅;出走前的
心理描寫讓我們瞥見了瑪姬的內心,被斯蒂芬的愛情俘虜后,她曾被一種自認為很無情的自私所控制:“為什么就不可以讓露茜痛苦一下……”盡管做出這樣的抉擇讓她備受煎熬,可這的確是她的心聲。所以當斯蒂芬邀她去劃船時,她便被驅使去“屈服于那強大的魅力”。正如派里斯所說,“她對斯蒂芬的征服滿足了瑪姬內心深處被壓抑的報復心理,反映出她想超過露茜的一種對勝利的欲望,因為她經常在露西的陰影里活著”。
當然,讓瑪姬冒著身敗名裂、眾叛親離的危險同斯蒂芬出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她喜歡斯蒂芬。她承認這同她與腓力浦之間的關系不同,和斯蒂芬交往是出于“虛榮或天性里其他的個人激動”。瑪姬同斯蒂芬的愛情是典型的一見鐘情,雖發生于偶然,卻十分動人心魄。初見斯蒂芬她便覺得“這新的體驗很美妙——美妙到幾乎抹去了她以前對腓力浦的情愫”。利維斯對瑪姬和斯蒂芬的出走沒有感到絲毫的突然,他覺得“瑪姬不敵斯蒂芬的誘惑,根本就不那么令人吃驚;之所以這樣說,原因即在瑪姬那熱情奔放的一面,在她對于理想情感升華的渴望上……”對這話的理解可以分為兩層:第一,利維斯所強調的“熱情奔放”同我們之前談論過的瑪姬叛逆的性格十分合拍:第二,瑪姬“對于理想感情升華的渴望”,在利維斯看來是與她和斯蒂芬的愛情磁場所發出的強烈吸引聯系在一起的,意即瑪姬選擇同斯蒂芬出走是順從了自己的個人情感。
所以,選擇和斯蒂芬出走既符合瑪姬的心理發展軌跡,也呼應了她內心的情感吁求。
三、瑪姬為何閃電返回
如果說瑪姬和斯蒂芬的出走尚可解釋,那么她最后的返回卻令評論家們百思不得其解。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他們把瑪姬和愛略特等同為一人,利維斯對此更是篤信不疑:“瑪姬·塔利弗和年輕的瑪麗·安·伊文斯(喬治·艾略特的原名)根本就是一個人”,可循著瑪姬的成長軌跡,他們卻沒能如愿地在小說結尾處看到如艾略特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那驚世駭俗的感情“創舉”。原因何在?
《佛》是一部自傳體小說,瑪姬的成長經歷猶如作者早年生活的拷貝,可自傳體畢竟只是一種創作風格,把自傳性的素材加以典型化處理的過程是相當主觀的,因此,作者筆端展現的故事情節不能和她現實的生活相提并論,更不能將瑪姬和艾略特完全等同。尤其在感情一事上,瑪姬和艾略特雖同為“第三者”,卻有著本質上的差別:劉易斯與前妻的感情早在艾略特出現之前就已產生隔閡,艾略特并非造成他們感情破裂的“第三者”,只是他們公開同居這一行為有悖于維多利亞社會的傳統,所以才會受到當時社會輿論的譴責。瑪姬則不同,如果她在和斯蒂芬出走后繼續選擇將錯就錯的話,就會牽連到許多無辜者:她的橫刀奪愛會辜負天真的露茜對她的信任,從而喪失純真的姐妹之情;她不計后果的沖動之舉還會傷害對自己無比崇拜并寄予厚望的腓力浦。由此可見,戲里的瑪姬根本就不是戲外的艾略特,那作者賦予瑪姬這樣一個結局的真正原因何在?
“綜觀19世紀中葉英國有關小說的評論或爭論,幾乎每一種觀點都在強調小說的某種實用功能……討論得最多的是小說的道德教誨功能。”把這話用來描述艾略特的小說可謂再恰當不過了,因為倫理性是艾略特小說的又一鮮明特點,與她筆下其他的主人公一樣,艾略特在此借助瑪姬出走并回歸一事來理性地探索一個人的行為選擇跟命運的關系,探索人們面臨選擇時的道德躊躇。因為“小說是最高級的道德教誨工具,卡萊爾就曾經強調偉大的小說家必須同時是預言家,他們應該洞悉社會、針砭時弊,同時為當時的倫理搖旗吶喊”。
19世紀的維多利亞時代是英國人引以為豪的“黃金時代”之一,經濟日漸繁榮,版圖不斷擴張,可欣欣向榮的表面下卻暗流涌動,特別是功利主義盛行在極大地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急功近利和自私自利的心態在社會上的泛濫,不僅在追逐財富上如此,在追求個人感情上亦是如此。當同時代的許多作家在“大聲疾呼人的權利、贊頌個人奮斗時,艾略特卻在引人思考入的義務,謳歌富于責任感的人物”。小說中的教區牧師肯恩博士悲哀地察覺到“教區的人和人之間……伙伴之情和彼此負責精神的缺少……人人都只想為所欲為,不愿堅持義務。”這在小說瑪姬和斯蒂芬出走一事上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們初次相見便墜入愛河,可惜兩情相悅的愛情卻為社會倫理所不容。斯蒂芬忘了自己已是露茜的未婚夫這一事實,更忘記了由此應當承擔的責任,策劃并安排了這次私奔;而瑪姬也忘記了自己對腓力浦的承諾,在懵懂中共謀了此次私奔。這是一場以自我為中心的感情“出軌”:斯蒂芬試圖這樣說服瑪姬:“沒有愛情的忠誠是空洞的,他們會因為我們這樣做而感謝我們嗎?”可見他的愛情觀以是否“有用”的功利主義原則為指導。而且,他所謂的“忠誠”只是忠誠于自己的感情,而絲毫不顧及他人的感受。瑪姬最初也為情所困,選擇了盼望已久的愛情,可是在痛苦的思索后還是決定放棄,因為“忠誠與堅貞意味著別的東西,而不光是做自己覺得最輕松最快活的事。它們意味著放棄一切跟別人對我們的信任相抵觸的東西,放棄一切能使在生活里依賴我們的人痛苦的東西……”。因為這份感情不但會傷及無辜的表妹,更會在出走后平添上鬼鬼祟祟的成分。任何崇高的愛情都會因為獲取方式的不崇高而黯然失色。而正是來自內心強烈的倫理沖突,令瑪姬“無法覺得神圣起來”,也才讓她在最后果決地拋棄了這段損人亦不利己的感情。
喬治·艾略特一直因為個人生活的“不檢點”而頗受諸多指責,更有人含沙射影地指出,像這樣一位“劣跡斑斑”的人,根本無任何資格談論道德和責任,可她卻通過瑪姬出走并回歸一事向我們彰顯了道德的真正含義,告知我們既無法拋卻歷史建構的責任,也不能漠視對他人的責任,更不該為了一己私利做出傷害他人之舉。基于此,瑪姬才選擇在最后走上了高尚但自毀的回歸旅程;基于此,現實生活中的艾略特才在劉易斯結束與前妻名存實亡的婚姻后,負責地履行了為人妻、為人繼母所應負的全部責任。
撥開歷史籠罩在她身上的疑云,我們看見了一個背負責任在人間行走的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第三者”——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和她在小說中創造的人物告知走近她的讀者“上帝令人無法想象,靈魂不朽令人難以置信,而責任才是絕對的,不可違抗的”。而這也正是她費盡心思安排瑪姬出走后又閃電折回的真正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