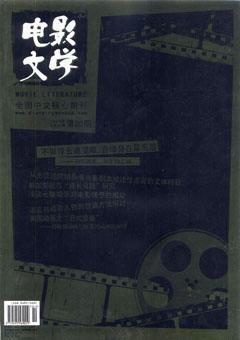沈從文《邊城》小說的隱喻性結(jié)構(gòu)
李谫博
[摘要]沈從文《邊城》小說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來的一個突出特色,即“隱喻性的結(jié)構(gòu)”,它主要體現(xiàn)在四類象征本體的塑造中:田園牧歌式的詩意世界;理想化的健全人性;表層的愛情悲劇;心中的意象“白塔”。
[關(guān)鍵詞]《邊城》;隱喻性;詩畫;意象
小說《邊城》給沈從文帶來了“震動中外文壇”的盛譽(yù),自問世以來,備受世人關(guān)注,其評論一直不斷,尤其是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國內(nèi)外的評論文章不勝枚舉。沈從文《邊城》小說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來的一個突出特色,即“隱喻性的結(jié)構(gòu)”,它主要體現(xiàn)在四類象征本體的塑造中:田園牧歌式的詩意世界;理想化的健全人性;表層的愛情悲劇;心中的意象“白塔”。
沈從文說:“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但同時也說不定,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至此,沈從文這部作品的隱喻主題幾乎被說得明明白白——作品獻(xiàn)給:“基于對中國現(xiàn)社會變動有所關(guān)心,認(rèn)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和在那里很寂寞的從事民族復(fù)興大業(yè)的人。”正是這個隱喻性主題決定了整部作品所具有的隱喻性結(jié)構(gòu)。
一、田園牧歌的詩意世界到文明狀態(tài)的湘西世界
《邊城》構(gòu)筑了一個田園牧歌式的詩意世界,酉水岸邊的吊腳樓,茶峒的碼頭,小溪流上的繩渡,翠綠的竹篁,清澈的溪水,幽碧的遠(yuǎn)山,清澈透明的碧溪咀,溪邊的白塔等等,為我們勾畫出一幅充滿詩意的湘西風(fēng)景圖。而端午節(jié)賽龍舟,捉鴨子比賽以及男女中秋月下的對歌,元宵的爆竹煙火,走車路或馬路的求婚方式,辦喪事的繞棺等,又構(gòu)成了湘西社會特有的民間風(fēng)俗。還有像擺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這些邊城生活中習(xí)以為常的平凡小事,在作品中都得到了理想化的描述。
文中有一處茶峒的人居環(huán)境做了這樣的描述: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時只需注意,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可沽酒。夏天則曬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褲,可以作為人家所在的旗幟。……自然的大膽處于精巧處,無一地?zé)o一時不使人神往傾心。
正如其題目“邊城”一樣,這里的人們是生活在一座與現(xiàn)實(shí)隔絕的桃園仙境中了。這樣美輪美奐的童話世界在30年代的湘西茶峒人的心目中,只能成為一種夢想。
沈從文勾畫了一座“空中田園”式的“邊城”,但并非那些納入“田園化”框架的作品。他的《邊城》完全擺脫了“田園化”的框架,它并不是無力改變現(xiàn)實(shí)而逃避現(xiàn)實(shí)產(chǎn)物,其作品旨在對現(xiàn)實(shí)重造。作者筆下的境界表現(xiàn)得越完美,隱喻在這種境界中的思想也便愈深刻。我們不能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找到“邊城”那樣完美的世界,但是我們可以從那人為的完美世界中,體味到更深一層的精神實(shí)質(zhì)。
二、從“理想化的健全人性”到20世紀(jì)30年代湘西人“唯利庸俗的人生觀”
20世紀(jì)30年代的湘西地區(qū)并非世外桃源。1934年沈從文曾從北平返回故鄉(xiāng)一趟,他對湘西的印象是“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最明顯的即農(nóng)村社會所保有的那點(diǎn)正直樸素的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20年來實(shí)際社會養(yǎng)成的一種唯實(shí)庸俗的人生觀。”在《習(xí)作選集代序》中沈從文明確地點(diǎn)明了他寫作《邊城》的動機(jī),他“要表現(xiàn)的本是一種‘人生形式,一種優(yōu)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因此,他把邊城寫得那么美好與純潔,不是逃避現(xiàn)實(shí),也不只是思古懷舊,而是痛感于當(dāng)前現(xiàn)實(shí)的黑暗,企圖將過去生活的美對照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丑,讓人們來鑒別真善美和假丑惡,從而啟發(fā)人們棄惡向善、舍丑求美。
翠翠是沈從文作品中虛構(gòu)的人物,在現(xiàn)實(shí)生活當(dāng)中是無法找到她的,翠翠是沈從文夢幻一樣的想象,是他追求的一種理想。
翠翠在沈從文的筆下是老船夫心目中的“一個太陽”,文章對這個老船夫?qū)懙溃?/p>
他從不思索自己職務(wù)對于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地很忠實(shí)地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頭起時,感到生活的力量,當(dāng)日頭落下時,又不至于思量與日頭同時死去的,是那個近在他身旁的女孩子。
那么對于一位老人有如此深重意義的翠翠是一個什么樣的女孩子呢?沈從文寫道:
翠翠在風(fēng)日里長養(yǎng)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yǎng)她且教育她,如山頭黃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fā)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見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jī)心后,就又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
由此可見,她是大自然孕育的一個“小獸物”,一頭黃麂。她的整個生命的長養(yǎng)不是靠我們今天家庭的母愛、父愛,而是風(fēng)日,是大自然。也就是說,她是沒有沾染人世間的一切功利是非思想,是不含渣滓,純凈透明的,已達(dá)到了與自然融為—體的境界。
翠翠的爺爺是國家雇傭的,是有工資的。撐船擺渡幾十年,風(fēng)雨無阻,他把這視為本分,分文不收。他那粗獷豪放、爽直豁達(dá)的性情,輕利重義的品德,寬厚正直、助人為樂的精神,集中體現(xiàn)了茶峒人的美德。當(dāng)?shù)氐拿耧L(fēng)民情非常淳樸、善良,人都好得不得了,可以看出作家在故意夸張。
妓女在《邊城》里也是很重感情的。她們雖然與商人在一起,心里卻想的是水手。這里涉及另外一種民間淳樸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一般情況下。民間是弱勢,它總是被強(qiáng)勢文化道德所覆蓋,所以封建的一套道德標(biāo)準(zhǔn)仍然會在民間起作用。但在真正的民間底層,人的生存是第一性的。所以沈從文在文中說:“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紳士還更加信任。”沈從文筆下的妓女,她們都是“重義輕利”“守信自約”,比“知羞恥的城市中紳士還更可信任”這是有所針對的。
船總順順是個大方灑脫的人,他喜歡交朋友,慷慨而又能濟(jì)人之急。他明白出門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他的兩個兒子,因在他的教養(yǎng)、磨煉下都結(jié)實(shí)如虎、不嬌惰、不浮華、不倚勢凌人。父子三人在茶峒邊境上都是有口皆碑的。沈從文對船總順順的描寫,不是以19世紀(jì)30年代流行的階級分析眼光來寫,沒有寫不同階層的對立,反而寫邊城人整體的融合,沒有那種等級的差別。沈從文正是從這種原始古樸的民風(fēng)里找到了他渴望的人情人性的美。
沈從文曾明確表示,他創(chuàng)作《邊城》是為了表現(xiàn)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意在反襯目前的墮落。在《邊城》題記上,曾提起一個問題,即擬將“過去”和“當(dāng)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么方面著手。《邊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熱情,雖然已成為過去了,應(yīng)當(dāng)還保留些本質(zhì)在年青人的血里、夢里,相宜環(huán)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輕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由此可見,沈從文小說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人性皆美善的理想性描述只是軀殼而已,其靈魂之所在正是重造現(xiàn)實(shí)和民族的,尤其是年輕人的品德。
三、表層的愛情悲劇構(gòu)筑的本體象征
從《邊城》所構(gòu)建的表層結(jié)構(gòu)看,這是一個愛情故事,一個愛情悲劇。這個愛情故事簡單,沒有其他言情小說那種大波大瀾的曲折情節(jié)。但這個本來并不復(fù)雜的,應(yīng)
順其自然發(fā)展而能成就的愛情過程中卻充滿了陰差陽錯的“誤會”,致使一段美好的愛情故事變得支離破碎,最終留下了令人憂傷的悲劇結(jié)果。
對于這出悲劇,沈從文有意回避或沖淡了人為的沖突。他在小說中設(shè)計(jì)許多誤會。翠翠的愛情悲劇,表面看來像是發(fā)生在無沖突的和平之日,除了“誤會”就是“不湊巧”,但細(xì)細(xì)品味,就可看出它原是深深地植根于現(xiàn)實(shí)的階級對立的土壤之中。船總和老船夫之間雖說一向和好友善,但是一個是社會上的頭面人物,一個是處于社會底層的百姓,因此在他們的意識深處仍然存在著地位高低不同的牢固觀念。正是這種觀念,使老船夫在船總面前總是言語紆曲、自卑不安,不能直言相告;而船總對待老船夫時,又總是漫不經(jīng)心,甚至以粗略的語氣中止談話。這便從側(cè)面表現(xiàn)出他們之間社會地位的懸殊以及由此造成的隔閡。船總順順對老船夫的樂善好施只不過是出于富人對窮人的一種憐憫、同情罷了。請吃幾回酒就能夠上是同一階層的人嗎?當(dāng)然不!當(dāng)真正談到關(guān)系富人家族利益的婚姻大事時,他們選擇的標(biāo)準(zhǔn)便是“門當(dāng)戶對”。
正因?yàn)樯驈奈膹目此破届o的社會環(huán)境中,看出了這種隱存著的階級對立現(xiàn)實(shí)。所以才在《邊城》題記中熱切地希望把它奉獻(xiàn)給那些“極關(guān)心整個民族在空間與時間下所有的好處與壞處”“很寂寞地從事民族復(fù)興大業(yè)”的人們,使他們“從作品接觸到另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發(fā),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這里包含著沈從文對現(xiàn)代文明玷污的不合理的人生制度的憂郁與不平。
四、中心意象“白塔”的設(shè)置
作品結(jié)尾,一夜暴雨過后,矗立在碧溪咀邊上的“白塔”倒塌了,這是與老船夫的死同時發(fā)生的。白塔不僅關(guān)系著小城的風(fēng)水,作為某種不可知的,難以動搖的命運(yùn)的象征,它寄寓了茶峒人的希望、祈禱和敬畏之情。它的消失將意味著一種恐怖的末日,每個茶峒人都將去守護(hù)這座心靈深處的“白塔”。于是故事的結(jié)尾出現(xiàn)了捐錢建塔運(yùn)動。這里的白塔已具備“圖騰”的威力,塔的坍塌與重建可能構(gòu)建了整個茶峒的歷史。沈從文在這里所運(yùn)用的象征和意象,已經(jīng)不僅僅是一種簡易的隱喻手法,而是包含艱苦的虛構(gòu)過程。“白塔”是與整個故事的虛構(gòu)密切結(jié)合在一起的,與中華民族的衰敗與復(fù)興這一隱喻主題的揭示,存在顯而易見的藝術(shù)預(yù)設(shè)關(guān)系。
“從主題和結(jié)構(gòu)來看,《邊城》故事的敘述是沈從文對民族命運(yùn)思考、觀察和體驗(yàn)的表現(xiàn)。因此作品采用了隱喻的敘述模式。對‘塔意象的描述是作家偏離人物而轉(zhuǎn)向時空背景,以完成主題意象和象征變異重復(fù)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這從根本上決定了《邊城》的隱喻性結(jié)構(gòu)。使得整個結(jié)尾像一個征兆,起到了文明死亡和毀滅的象征作用。可以說白塔是這部帶啟示錄性質(zhì)的小說中最具有恐怖象征意義的形象。”
總之,沈從文的《邊城》正如李健吾所評價的那樣:細(xì)致,然而絕不瑣碎;真實(shí),然而絕不教訓(xùn);風(fēng)韻,然而絕不弄姿;美麗,然而絕不做作。沈從文用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為支點(diǎn),撐起的卻是他整個的關(guān)于重造民族精神的宏愿。作者以他清新富于靈性的筆觸,獨(dú)特的審美情趣,如詩如歌的抒情語言,為這篇小說披上了優(yōu)美朦朧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