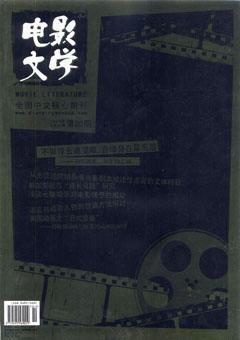后現代主義語境中的戰爭敘事
郭林紅
[摘要]新播劇《我的團長我的團》開創了一種新的戰爭敘事手法。以傳統英雄人物的非典型化、宏大敘事模式的摒棄、軍旅作品主題思想的顛覆,對戰爭題材典型化的消解,完成了對經典傳統革命英雄主義戰爭題材影視作品的徹底解構。該劇通過對戰爭與軍事活動中人、人的命運與處境等問題的思考,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從而使作品具有更深刻的哲理意蘊。
[關鍵詞]《我的團長我的團》;戰爭題材;英雄形象;宏大敘事;消解
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思潮正以其強大的沖擊力影響和踐行于文學、繪畫、建筑等各個領域。它所主張的放棄現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規范內容,提倡非理性主義,強調反思和批判,突出多元性思維和世界的多樣性。致力于解構一切傳統恒定意義等等,同樣吸引了大批電影工作者前赴后繼的探索和實踐。新播劇《我的團長我的團》(以下簡稱《我的團》),以傳統英雄人物的非典型化、宏大敘事模式的摒棄、軍旅作品主題思想的顛覆,對戰爭題材典型化的消解,完成了對經典傳統革命英雄主義戰爭題材影視作品的徹底解構。
一、對傳統英雄形象的解構
傳統革命英雄主義戰爭題材影視作品,通過政治理性的主導,建立了典型環境的描寫和典型化的人物塑造等影視規范,形成了革命英雄主義的崇高風格。傳統戰爭題材影片英雄形象:一是背負建立強大民族國家理想,勇于抵御外敵入侵,敢于英勇獻身,為國家、民族和崇高理想,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二是睿智善戰,熟諳戰爭規律法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能在困境、危局中挽狂瀾于即倒,敢于決策、勇于指揮,是戰爭進程及勝敗的決策者、指揮者;三是具有軍人典型的人格力量和審美價值,有堅忍的意志與不可戰勝的精神力量,即使面臨現代社會家庭、社會、生活、心理等多重壓力和金錢物質的極端利誘,仍然是忠誠、責任、奉獻、陽剛的化身。這些影視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不論是“高大全”式的人物,還是近年來在人物的選擇和性格塑造上有很大突破的李云龍(《亮劍》)、常發(《狼毒花》)等另類英雄或許三多(《士兵突擊》)等經軍營磨礪具有軍人性格與意志的普通士兵,審示他們的審美特征,依然是伴隨著激動人心、高昂雄壯、激昂慷慨、蒼涼悲壯的審美享受,仍屬于“英雄”的范疇(具有軍人品格的優秀人物)。
《我的團》是對上述英雄形象的徹底顛覆。它著力刻畫一群生活在最底層的潰兵,最低標準的生命延續是他們每天的目標,動物的本能是他們的生存方式。為了一餐豬肉燉粉條,極盡坑、蒙、偷、騙之能事,甚至連妓女的口中食都要欺騙。按照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的理論,這是一群還沒能解決溫飽基本生存需要的最底層群落。破舊的軍裝,無序的軍容,行動的散漫,自稱是人渣、炮灰,這種生命外在形式的卑微,來自于整個社會群體的公共評價,更來自他們的內心深處。就軍人而言,這是一群無崇高理想、無堅定信念的活著的軀體,沒有追求的勇氣,沒有生活的自信,當然也就缺少生命的雄健與熱情。生命形式的卑微伴隨著國家民族意識的淡漠,在直面國土淪喪、祖國被蹂躪、同胞被屠殺的境況下,給他們留下的是對死亡的極度恐懼和活著的無奈與冷漠。
《我的團》沒有傳統英雄的神圣光環,找不到“典型化”的英雄形象,虞嘯卿、“小書蟲”、龍文章等似乎具備某些“英雄形象”的外在氣質,但已非傳統精神楷模的“英雄”人物。虞嘯卿:具有軍人的外在氣質,果敢、有氣魄、有膽識,以“國家有難,豈能坐視之”為警句,為抗擊日軍不惜殺了擅自逃跑的胞弟,他在怒江邊建立了與日軍對峙的防線,但他在關鍵時刻放棄了對他委以生命信任的戰友(雖有不得已的情況),之前所有軍人的外在表象,頃刻轟然倒塌,在自己前程及虞氏家族的榮耀面前,他是軍人,卻更像政客,這是對軍人人格的徹底背叛,雖未投敵,心靈實已變節;“小書蟲子”,伴隨著“天之涯、地之角”的校園抒情歌曲走進我們的視野,吟唱著“我們要在黑夜里樹立火炬”,為了理想和信念,激情似火;為了國家民族敢于奉獻,勇于犧牲自己的生命,但面對生命絞肉機的戰爭,他們生命的消亡,猶如絢麗的彩虹那樣短暫,那樣易于毀滅,雖美麗,但對于長期處于災難中的國家民族,似乎只能是一個美好的記憶;龍文章(又稱死啦死啦),于潰敗中收編了近一團散兵,自封團長,組織了慘烈的南天門阻擊戰和最后的攻堅戰,表現了獨到的軍事素質,但他在上司虞嘯卿面前怯懦卑微,在南天門上為一個基數的炮火支持,長跪作揖,雖打退日軍18次沖鋒,卻在最后率眾逃跑,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在軍事上的種種表現或是為了自己34歲當上連長卻未實現的軍事夢想,從現實視角和語境出發,或可列為英雄,但已非傳統意義上的典型英雄。
《我的團》顛覆傳統英雄形象,轉而展現最底層小人物的生命形式和生存方式,深切關懷并同情小人物的命運,揭示人性的復雜,從而突破“典型化”以及塑造和謳歌的傳統英雄形象的創作模式。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不再把普通人當做英雄人物的配角,而是作為歷史的主體、影視作品關注的中心,還原小人物的本來面目,把他們作為創造歷史的“真正英雄”,是傳統英雄形象走下神壇向常規人性的價值回歸,小人物“英雄形象”的樹立完成了對傳統英雄形象的解構。
二、對宏大敘事模式的解構
傳統革命英雄主義戰爭題材影視作品,以宏大的敘事模式突出對戰爭進程和戰爭事件的展現,全境式展示決定戰爭勝負的敵對雙方指揮員心智、謀略、力量、武器裝備、人心向背等決定因素和各種偶然因素,戰爭場面激烈、氣勢恢宏,即使有普通人物生活細節、場景的勾勒,也是為整個戰爭事件而服務,單個生命個體只是戰爭中的一個微小構成單元,普通士兵乃至高級將領只能服從并服務于戰爭需要,宏大敘事時常伴隨英勇的故事、鮮明的旗幟、偉大明晰的經典化戰爭理論。宏大的敘事,與細節描寫相對,與個人敘事、私人敘事、日常生活敘事和“草根”敘事等等相對。《我的團》從敘事視角、敘事構成、敘事節奏等方面完成了對傳統革命英雄主義戰爭題材影視作品宏大敘事的解構。
在敘事視角上,《我的團》是一個戰爭中傷殘下級軍人孟煩了的個人敘事,他以第一人稱的視角作為敘述者,聚焦了他的所見、所為、所說及大量意識、潛意識心理活動,從他的視野中展現《我的團》。而孟煩了本人是一位心靈和身軀嚴重受到戰爭創傷,介于傳統與現代、理性與叛逆、麻木卻不失熱情、碌碌卻不乏思考、尖酸卻也高尚的小人物,在他雙重而矛盾的性格中,從他的視角敘述戰爭,感知身邊的人和事。在孟煩了的視野中,親歷戰爭被殺戮的噩夢永遠揮之不去,伴隨的是對國家、民族、抵御外敵入侵的麻木與冷漠,在戰爭中他時時切身感受到一個個鮮活生命的消失,以及這種消失給敘事者心靈帶來的震撼與傷痛;感受到面對死亡一個個普通生命的存在方式,并著力通過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行動,觸及他們的靈魂深處,展示戰爭中小人物、邊緣化人物的生命存在形式;感
受到普通民眾的生存態度,如小醉、迷龍媳婦、禪達民眾,他們為生存而苦苦掙扎,但美好的人性、善良的情懷、質樸的情感并未在他們身上消失。這種敘事視角帶有敘述者的主觀性,必然導致被講述的故事并非完全圍繞宏大的戰爭展開,也使戰爭中英雄的主題得以沖淡。
在敘事構成上,《我的團》以滇緬抗戰為背景,在這場慘烈的民族反侵略戰爭中,史料顯示,1942年第一次遠征軍入緬作戰,中國參戰部隊即達到10萬之眾,1944年開始的反攻作戰,又投入軍隊20多萬人,僅松山戰役(《我的團》中南天門戰役的原型),就歷時120天,中國軍隊先后投入兩個軍5個步兵師總計6萬多人,動員后勤民3210余萬人次,在最后攻克松山主峰的反復爭奪戰中,中國軍隊采取坑道作業,填埋數噸炸藥,徹底將山頭連同日軍暗堡一同毀滅,戰斗之慘烈已達極致,是役中國官兵陣8000余人,傷者逾萬,日本守軍1200余人除個別突圍外全部戰死,整個滇西抗戰,彪炳史冊的還有滇緬公路、駝峰航線、飛虎隊等等。就敘事構成而言,敘事內容資源豐富,但《我的團》放棄這一宏大主題選材,就偉大的滇西衛國戰爭而言,我們既沒有看到戰爭的全貌,也不能體味戰爭史詩般的進程,更未看到經典戰爭理論對戰爭勝負的決定作用。盡管該劇戰爭場面占到40%,運用了大量戰斗場面特技,但就全劇而言,我們看到大量瑣碎、紛雜的生活細節鋪陳,以及講述者心靈深處的個人感受,多個情節的反復重現。這種敘事內容選擇上的瑣碎,情節設置上的平淡,人物塑造上的平民化,關注戰爭中普通士兵的生命價值、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從而以更寬、更廣的視角審視了戰爭。
在敘事節奏上,傳統戰爭題材影視作品圍繞戰爭鋪陳,多層次、多角度展現敵對雙方為奪取戰爭勝利而作的系統籌謀,制造大戰一觸即發的態勢,矛盾沖突尖銳驚險,情節節奏緊張扣人,各方命運撲朔迷離。而《我的團》沒有圍繞戰爭勝負展開,而是以敘事者不緊不慢的生存感受展開了一條直線式“勻速”敘事,與戰爭無關的事件被有意在時序上拉長、變慢,甚至于精雕細刻,用較長的時間來敘述較短時間內發生的故事,把事件的過程細節放大。不惜用兩集的時間長度表現要麻、康火鐮等人的死,用冗長的影視文本講述迷龍如何騙床、如何占屋、如何安家,敘述川軍團在與日軍隔江對峙時的無聊、無奈、無序……即使直面戰爭,也不再刻意解釋、標榜,沒有戰爭的精心謀劃與準備,似乎在不經意間完成了戰斗過程的敘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南天門阻擊戰,也是在后有追兵,前有怒江天塹絕境中不得不做的惟一選擇;具有對反攻有重大意義的渡江偵察,初衷也是為了救出孟煩了的父母。作為戰爭題材影視作品,放棄最吸引人的戰爭敘事,使敘事節奏在有意無意偏離這一中心。《我的團》宏大敘事模式的摒棄,不刻意展示戰爭重大歷史題材,以普通人的視角,略顯冗長的生活瑣碎敘事,平面展示戰爭進程,展現戰爭中普通人的生活,不再把戰爭勝負成敗作為惟一的關注點,有意跳出戰爭,遠距離進行眺望與審視,還原戰爭的本真狀態,走出為戰爭而戰爭的認識誤區,從而為全面展現戰爭、認識戰爭、反思戰爭提供了更深、更廣的角度。
《我的團》開創了一種新的戰爭敘事空間,消隱傳統英雄主義戰爭題材的神圣光環,不再圍繞戰爭勝負展開敘事,不再塑造英雄典型,而是更多地關注戰爭中普通士兵、小人物的生命及生存狀態,通過描寫戰爭中普通人瑣碎、平庸的日常生活,還原歷史現實的原生態、取消英雄、解構崇高。該劇通過對戰爭與軍事活動中人、人的命運與處境等問題的思考,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從而使作品具有了更深刻的哲理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