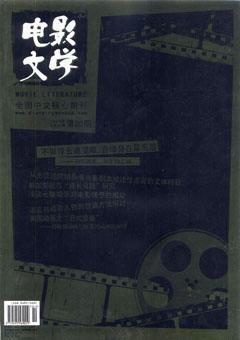和諧文化下的農民進城路
龔祝義
[摘要]《走西口》商業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抓住了當下的熱點話題——農民進城,并給予深刻的人文關懷,探討出了“仁義禮智信”是農民進城的“通行證”和構建農民與農民、農民與城市、國內和國外和諧關系的“中國式智慧”。同時,《走西口》也存在對人性表現不足的缺陷。
[關鍵詞]《走西口》;和諧文化;農民進城
2009年央視的開年大戲《走西口》平均收視率9.6%,創2002年以來新紀錄。《走西口》為觀眾青睞的原因似乎有很多:動人的故事情節、燦爛的山西文化、傳奇的晉商經歷。但之前的《喬家大院》和《闖關東》也具備這些因素,并且在表現上述因素時比《走西口》有過之而無不及,以“喜新厭舊”的文藝審美心理而言,《走西口》的收視率應該遜于《喬家大院》和《闖關東》,但它在收視率上不遜反強,說明上述因素只是它成功的表面原因。其實,通過對《走西口》的主題分析,我們會發現,《走西口》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抓住了當下的熱點話題——農民進城。
一、風風雨雨進城路
《走西口》的主題之一是農民進城的道路艱辛又坎坷。為了將這一點展示給觀眾,編劇對主人公活動地點的安排煞費苦心,四個地點連起來對應農民進城的路線:祁縣=農村,殺虎口=農村與城市交界點,包頭=城市,恰克圖=國際貿易中心。主人公田青依次循著上述地點進城并在城市立足,田青和他的同伴在這些地點發生的故事也告訴觀眾:進城途中是艱辛的,進城后的奮斗也充滿血和淚。于是,我們看到:田青在殺虎口遭逢劉一刀為首的黑社會;剛踏入包頭,就身陷囹圄;在包頭生意剛剛起步,又被污為“盜墓賊”;生意做到恰克圖,已經進行國際貿易了,又莫須有地被控為“勾結蘇聯”。
在表現進城農民悲慘遭遇的同時,《走西口》也展現了進城的歡欣,或親人相聚,或戀人會面,或惡人天譴。但這種歡欣往往是苦澀的歡欣或短暫的歡欣,如田青攜妻回歸故里,但其時正是丹丹斷腸時;田青會晤數年不見的翠翠,但隨即翠翠身陷死牢;田青因翠翠已嫁而向豆花求婚,但翠翠正是為他而所托非人;吳玉昆離開包頭,但又逢物價上漲;徐木匠答應與淑貞完婚,但完婚日等來的是徐木匠的骨灰。從故事編排而言,這些處理是為了使劇情波瀾起伏、跌宕生姿,使觀眾饒有興致地收看。但從農民進城的主題而言,卻是告訴觀眾:進城的艱辛多于休閑、痛苦多于歡欣。
對于農民進城的艱辛和痛苦,《走西口》并不是冷眼旁觀,而是給予深刻的同情。這一同情在劇中的表現之一是純化主人公的進城目的。田青進城的目的是解決生活的艱辛,還贖母的500銀元貸款,贖回被騙去的田家大院;王南瓜是為了尋回從未見面的父親,以慰母親在家苦等的寂寞的心;梁滿囤只想讓父親、母親和丹丹有飯吃。這些目的或為生存、或為人倫,無一不正當、樸素、純真。目的的純正與進城途中和進城后的非人遭遇形成強烈反差,《走西口》對農民進城的同情也就昭然紙上。之二是展現主人公和同伴進城的悲慘遭遇或結局。田青三次入獄;王南瓜尋見父親,父親卻出離紅塵;大個子像駱駝那樣憨厚、忠誠,卻命喪匪手;即使是喪了良心的梁滿囤,編劇也讓他最后良心發現,為救田青而殞身不恤。之三是講述主人公背后女人的悲慘故事,在劇中,這一點尤其表現在丹丹和翠翠的故事上。丹丹一手抱大梁滿囤,等呀盼呀,盼來的是進了包頭的梁滿囤的一紙休書,但丹丹依舊癡心不改,為薄情郎祝福,最終在土窯洞中寂寞地死去;翠翠在田青走后,先遭夏三陷害,后又嫁給比自己大30多歲、嫉妒心極強的鄒老板,最終為擋住射向田青的子彈,命喪父親劉一刀之手。
開年大戲播出時,外出務工人員回家,《走西口》講述的雖然是清末民初的故事,但看著這些故事,觀眾想起曾經聽過或親身經歷的車匪路霸和進城后的不公平對待,再加上《走西口》中百試不爽的情感戲,所以,雖隔百年,看著這些故事,觀眾怎能不灑下一掬同情的淚水?
二、仁、義、禮、智、信是進城的通行證
農民進城的“進”是容易的,但如何在城里生存或立足卻是難題。《走西口》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思考,并通過田青和同伴及父輩的故事得出自己的論點:只有“仁愛、忠義、禮和、睿智、誠信”五常兼備才可以在城里生存并揚名立萬。
為了論證這一論點,編劇特意在《走西口》中安排了兩類人物,第一類人物的作用是烘托主人公田青,包括王南瓜、龔文佩和大個子。王南瓜、龔文佩和大個子具備“仁愛、誠信”這些特征,但不夠睿智、勇敢,只有“修身齊家”之志,所以進包頭多年,王、龔經營的山西莜面館還是以前的規模,大個子還是長年拉駱駝。通過這三個人的故事,《走西口》告訴觀眾:只擁有“仁愛和誠信”可以在城里生存,但不能出人頭地。
第二類人物的作用是與田青形成對比,包括梁滿囤、田耀祖和裘老板。梁滿囤拋妻害師、坑友欺人,面對匪徒與權勢,膽小怯懦。雖說依憑上門女婿的捷徑在包頭立足,但由于五常俱缺,最終“裘記皮匠鋪”瀕臨破產。田青的父親田耀祖,輸光祖業,以妻抵債,在殺虎口與劉一刀狼狽為奸。最終機關算盡,反算了自己的性命。裘老板雖說已在包頭創下家業,但以私利為重,為了家業和女兒,不惜拆散梁滿囤和田丹丹,最終被梁滿囤氣得半身不遂,隨即含恨離世。通過這三個人的故事,《走西口》昭示:在城里打拼時,如果以損害他人的利益為前提來獲取一己私利,最終會自食惡果。
田青五常兼具:他大忠大愛。為了心愛的翠翠,違心地拒絕豆花的愛情;黑土崖的匪窩中,一心想的是怎樣將同伴、豆花、龔豐倉和裘老板都救出去;事業成功了,還不忘大個子和王南瓜。他大孝大勇。無論在祁縣還是包頭,都盡其所能地孝敬母親;面對匪徒,起身相斗,面對酷吏貪官,當場呵斥。他不只求一己、一家的幸福,還救助遭災鄉民,幫助諾顏王子救國敦民。他大恩大恕。對連累自己的瘦猴,不但不殺之而后快,反在其出獄后委以重任;對處處與他為難、拋棄他姐姐的梁滿囤盡心照顧。他做生意公平合理。不管是在包頭還是在恰克圖,都秉持公平合理原則做生意。正因為五常兼備,所以田青可以屢遭坎坷,屢次爬起;并在包頭置產購地,成為包頭商會會長。通過田青的故事,《走西口》不但告訴觀眾進城的通行證是“仁義禮智信”,而且還向觀眾解釋了“仁義禮智信”的內涵,即“大忠大愛為仁,大孝大勇為義,修齊治平為禮,大恩大恕為智,公平合理為信”,這也正是田家的祖訓。
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對強勢的西方和周邊崛起的日本和韓國,中國民眾都亟求商業經營管理中的“中國式智慧”。《走西口》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掘出“中國式智慧”,對于希望民族強大、國家發展的中國民眾而言,無疑是一荊強心劑。在這一點上,《走西口》并不是先例,之前的《大宅門》和《喬家大院》的成功也是基于這一點。但由于這一因素確實具有現實適用性,并且為主流意識形態、城里人和農民一致認可,所以它在電視劇中可以屢試不爽。
三、和諧主題中的不和諧
《走西口》在為農民進城灑一掬同情淚和探尋何為農民進城的通行證時,也存在對主人公表現不充分和拔高主人公的毛病,以致于讓觀眾覺得主題做作、空洞。
表現不充分的毛病體現在對諾顏王子和徐木匠的處理上。為了多層次地詮釋“仁義禮智信”,編劇在《走西口》中安排了明暗兩條線索,明線是田青走西口的故事,暗線是諾顏王子救國的故事。明線表現的“仁義禮智信”的內涵是田家祖訓,暗線昭示諾顏王子和徐木匠的世界觀是“天下一統為仁,民族興亡為義,自強不息為禮,福虧自盈為智,以義取利為信”。但在全劇中,諾顏王子和徐木匠只做了對故事發展方向起決定作用的四件事:第一件事是徐木匠解救田青的母親,第二、三、四件事是諾顏王子和徐木匠將田青從死亡邊緣救回,劇中的時局和其余百姓的命運并沒有因為他們的努力而有一絲的改觀。也就是說,就劇中故事而言,諾顏王子和徐木匠只表現出是田青的救世主和保護神。這一處理既讓觀眾覺得他們的行為不能很好地詮釋他們的世界觀,又讓人誤解成結識一個重要人物比擁有“仁義札智信”更重要。
拔高主人公的毛病的表現之一是拔高了田青。在劇尾,《走西口》明暗線索交匯,共同升華出“世界大同為仁,祖國山河為義,家國天下為禮,剛柔相濟為智,一諾千金為信”。從而使“仁義禮智信”的內涵有了逐層遞進的三個層次。編劇在電視劇的前半部就讓田青放下田家的祖訓,強行讓他恪守暗線詮釋的“仁義禮智信”,但就田青在劇中的待人、接物、經商而言,他踐行的一直是田家的祖訓,只是到了全劇終,才勉強可以說進步到恪守第二層次的信條,《走西口》人為地將田青拔高到以“世界大同”為己任,實在是牽強。
之二是拔高了田青的母親淑貞。淑貞一直待在祁縣。她的人生信條就是相信兒子,根據她的性格和故事發展邏輯,最終她也會同意賣田家大院,但她同意是因為她相信兒子,相信兒子做的是正事、大事、好事,至于這正事、大事、好事為什么“正、大、好”,她不知道。所以,《走西口》最后一集讓她講出一番“為國為民做大事”的至理是人為地將她拔高。
通過對《走西口》的文化主題分析,我們發現,《走西口》的商業成功在于三點:一是大氣的歷史劇外衣下百試不爽的情感戲;二是抓住了當下的熱點問題——農民進城,并給予深刻的同情;三是告訴觀眾:“仁義禮智信”不但是農民進城的通行證,而且是構建農民與農民、農民與城市、國內與國外和諧關系的“中國式智慧”。同時,《走西口》也存在對主人公表現不充分與拔高主人公的毛病。如果能進一步按照人物性格和故事發展邏輯來表現和諧文化的主題,則《走西口》將不僅僅是即時消費的文化快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