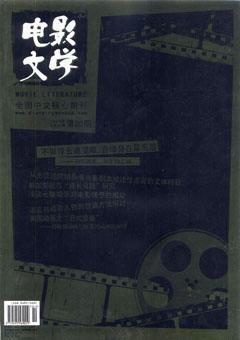電影音樂:獨特而美麗的述說
曹 暉
[摘要]電影音樂,作為一種獨特而美麗的語言,成為電影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王家衛無疑是20世紀最后20年華語電影圈最值得關注的電影作者之一,他以極端風格化的視覺影像、富有后現代意味的表述方式和對都市人群精神氣質的敏銳把握成功地建構了一種獨特的“王家衛式”的電影美學。基于此,本文以王家衛電影為例,分析電影作品中音樂的運用。
[關鍵詞]電影;音樂運用;王家衛
在人類還沒有產生語言時,就已經知道利用聲音的高低、強弱等來表達自己的意思和感情。《詩經·關雎》同樣有言“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可見音樂的巨大魅力。當音樂走進電影,跟電影結合在一起時,就成了電影這門綜合引述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稱之為電影音樂。它的演奏通過錄音技術與對白、音響效果合成一條聲帶,隨電影放映而被觀眾所感知,并伴隨電影畫面、劇情進展而產生了純音樂之外的審美特性和審美功能。可以說是“銀幕形象的一種詩意延伸”。正因為音樂和電影結合后碰撞出絢爛的藝術之花,電影音樂才備受青睞。
那么在電影中,影像與音樂是如何結合的?電影導演如何決定和使用音樂?在華語電影圈眾多出色的導演中,王家衛無疑是其中最值得關注的電影作者之一。他迄今為止的作品已經憑借著其極端風格化的視覺影像、富有后現代意味的表述方式和對都市人群精神氣質的敏銳把握成功地建構了一種獨特的“王家衛式”的電影美學。
基于此,本文擬以王家衛的電影為例,試圖闡釋電影音樂對電影的意義。
一、激發聯想,渲染氛圍
音樂在電影中有一種延伸敘事或“補充敘事”的功能,激發看電影的人在音樂聲中感受畫面,想象畫面之外的聲音。如果音樂和電影的畫面達到和諧保持音畫統一的關系,視覺和聽覺就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體,畫面和聲音共同營造氛圍。觀眾就沉浸在氛圍之中,全身心地感受劇中人物的悲歡離合及導演的用心,思維不會游離在畫面之外去聽音樂,也不會在音樂之外去看劇情。如同王家衛所言“音樂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于是音樂,成為一種提示,提示你身處于什么樣的環境、什么樣的年代。在我自己的電影里,我會先了解這環境是怎樣,包括地理環境以及這地方會有什么樣的聲音?所以往往音樂成為環境的一部分。也有的時候,我心里會先開始有一個音樂,完全不能解釋。就是直覺悟認為這戲應該是這個氣氛、這個年代”。王家衛的話充分說明了在他的電影王國中他需要畫面和音樂的和諧。
2000年出品的《花樣年華》故事很簡單,沒有太多華麗的成分,是常見的婚外戀故事。但整部電影的視聽元素幾乎都是呈現出風格化意識和唯美主義的色彩。片中選取周璇演唱的《花樣年華》這首歌,就激發了觀眾的很多想象,渲染了那個年代的氣氛。《花樣年華》這首歌是周璇1946年在自己主演的電影《長相思》中所演唱的插曲。影片講述的是在顛沛流離的抗戰年代,妻子因與丈夫失去聯系,失去生活來源,而不得不淪為舞廳歌女的故事。歌中所唱的“分離兩地的痛苦、愁苦的心情”正與影片《花樣年華》中男女主人公的心情不謀而合。盡管電影中兩個人的言語不多,更多的是眼神上的交流,但配合著音樂旋律的深沉、悠長,觀眾在日常的生活之外看出了更多的東西,能夠體會到兩人內心世界的憂愁和淡淡的無奈。同時張曼玉的旗袍、發式以及片場的設置都彌漫著那個年代的浮糜氣息,這種氣息在緩慢、沉重的音樂聲中同樣得到了很好的闡釋。
從始至終,音樂不斷地引發觀眾對那個已經逝去但仍像幽魂般繞在很多人包括王家衛腦中的花樣年代的各種遐想。可以說《花樣年華》是王家衛的留聲機,這部留聲機不斷地播放著五六十年代的老唱片,不斷播放著老歌《花樣年華》,不斷播放著很奇妙的爵士樂,這些都讓觀眾不斷地想起二三十年代的舊上海。王家衛電影中的留聲機真的具有勾起人回憶、讓人懷舊的功能。
用音樂去闡釋畫面,同時也用畫面注釋音樂,這使二者都擁有了單獨使用時都不曾擁有的“指示能力”,而這種合成的“指示能力”恰恰符合觀眾的審美情趣,使觀眾很容易感受到王家衛影片所渲染的環境氛圍,同樣也讓觀眾通過聯想,與王家衛的影片達到了一種情感上的溝通。
二、傳遞人物的精神狀態
音樂就其本質來說,并不擅長表現視覺上可以把握的現實世界中有形的客體,而是善于高度概括地表現人類最內在的心理體驗,抓住人類微妙豐富的感情狀態。用音樂抒發人物的內心情感,更是電影借助音樂的主要目的。音樂以音調起伏和旋律的流轉創造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情感的形象”,是描畫、傳遞人物內心世界的行之有效的手段,直接打動人心,喚起欣賞者思想和心理情緒上的共鳴。
如果說留聲機具有記錄時代并讓人勾起那個時代的遐想的功能,那么王家衛電影還賦予留聲機另一個功能:記錄情感。“王家衛的作品都圍繞著百無聊賴的孤獨的角色,而伴隨他(她)們的往往是哀怨纏綿的角色。”王家衛電影中的人物,舉手投足之間都透露著寂寞。寂寞,實際上就是不懂得愛,不會溝通,寂寞的人就是不懂得說也不會說。人物就像《花樣年華》的女主角張曼玉空靈般的行走一樣,盡管所屬的世界繁華、熱鬧、喧囂,但人物始終有一種無所歸依的生存體驗,空寂、冷漠。與之相匹配的是,悠長、低緩的主題音樂(指的是日本作曲家梅林茂作曲的“Yumejis Theme”)不斷地回響在影片的各部分。
在《花樣年華》中,剛開始時三步舞曲緩慢、沉穩的節奏,之后是中提琴悠長、輕柔的旋律,在這樣舒緩的聲態中出場的主人公傳遞出來的信息是:不是大富大貴,但也不愁吃穿,精神狀態并不昂揚。接著在吵鬧的麻將聲中,夾雜著悠揚的小提琴和聲,女主角百無聊賴地打著麻將,透露出無奈和悠長的思緒。中間男女主人公相遇在狹長的樓道上,沒有臺詞,小提琴的聲音出現了,恰如其分地代替了主人公的語言,彌補了單調的視覺形象。傳遞出主人公壓抑、憂郁的情緒及彼此的相互探視和渴望。不久,相遇的畫面和小提琴的聲音再次重復展現,不斷地強化著人物的情緒。
故事結局的音樂依然是主題音樂的三步舞曲,大提琴的憂傷占了主導地位,主角在憂傷中結束了一段情感。此外,影片中還有三首由黑人爵士樂歌手NatKing Cole創作的拉丁情歌,有點沙啞和磁性的男聲的音色、爵士風格典型的節奏型(變化不多)、弦樂、小號、鋼琴的伴奏、帶點慵懶味的旋律,另外還有著拉丁音樂中的熱情、愉悅和趣味。這三首用葡萄牙語演唱的歌曲被王家衛挪用過來在片中來預示男女主人公的愛情,那種既渴望又無奈的心情被歌曲渲染得淋漓盡致。
男女主人公之間那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糾葛和精神狀態,單純從視覺符號并不足以描繪。而音樂可以有一個很強的、用來形容精神狀態的指示功能。有些不能用言語表達的奇妙感情,王家衛用鏡頭和留聲機配合表達。產生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效果。
三、加強影片的連貫感
當電影中的音樂不斷地渲染氛圍、傳遞人物的情結時,也就在間接地引導著故事情節的進展,讓后面故事的
進展順理成章。音樂的旋律也不斷地調動觀眾的感官去感受、猜想情節的進展。特別是在蒙太奇鏡頭多的電影中,音樂對鏡頭結構的連貫作用更是突出,它能使一些分散的鏡頭在觀眾的思維中組成一定的結構,自如地把不同時間、空間的畫面連成一氣,而不是雜亂無章地堆砌。在電影中,一段完整的歌曲(音樂)往往能完成鏡頭轉換和場景銜接,這對于王家衛相對破碎的畫面效果尤其重要。
《阿飛正傳》就像片中那句經典的臺詞:“世界上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它只能夠一直地飛呀飛,飛得累了就睡在風里,這種鳥一輩子才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死亡的時候。”一樣,影片中只有人物,并無完整故事,導演通過鏡頭不停地為觀眾展現香港青年人的生存狀態,故事若有若無,人物展現完了即結尾的時候。而能夠連貫成片除了人物彼此的關系外,很重要之處就在于片中的音樂。幾乎在每一個敘事小段落的結尾處,都會出現一段音樂。電影中選的音樂分別來自巴西的Los Indios Tabaiaras和古巴的Xavier Cugat音樂,共同特點是浪漫、熱情、不羈、乖張。王家衛在電影中一連用了Xavier Cugat的六首作品:MyShawl,Perfidia,Siboney,Maria Elena,El Cumbanchero,Jungle Drums。比如在影片的35分鐘處,蘇麗珍離去后,此時響起了優雅、舒緩而略帶感傷的My Shawl,在這個段落的結尾,警察借錢給蘇麗珍后離開,那首傷感的My Shawl再次出現,將類似風格的音樂在片中不同人物身上反復出現,就讓人強烈地感覺到,雖然人物彼此間的關系是偶然形成的,但他們都是同代的人,有著同代人的煩惱和體驗。影片盡管鏡頭變幻莫測,但依舊是同一個故事。
《阿飛正傳》中,類似這樣的處理手法被反復多次地使用,無疑導演是有意地運用這種藝術手法,其深層意義在于:填補情節嚴重省略后帶來的感受上的空白,省卻了所有不必要的交代性的鏡頭和對話,在對故事的理解上,我們很多時候是通過調動格式塔心理來完成情節內容的大量省略,在形式感受上容易產生支離破碎感,而音樂的多次出現,無疑有助于減弱這種形式感受上的支離破碎感。
四、促進影片跨文化傳播
作為一名華語電影導演,要使影片跨國化,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理解,必須首先打破不同地域之間(臺灣、香港、內地以及海外的華人)的文化邊界,其次還必須處理好各地域間與世界其他國家越來越深入的相互滲透,即“世界性”和“全球性”的社群。但是另外一方面,不同地區由于歷史背景、文化風氣等都有一定的差異,也就是所謂的“文化鴻溝”。因此當一個文本到另外一個族群的文化語境中不可避免會有一些難以理解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音樂就是一種完美的媒介。音樂的語言是共通的,都是使用五線譜,因此音樂是一種跨文化的語言。
從音樂的運用來看,王家衛很能自在地游走于跨文化之間。2008年10月10日英國《每日電訊報》在百大電影中選出“最佳原聲大碟”,《花樣年華》榜上有名,該片被贊執導手法及音樂富有懷舊味道,其華爾茲配樂令悲傷鏡頭更完美地襯托出片中情侶的無奈。《每日電訊報》的解讀可以說很好地傳遞出電影的意味。
著名導演希區柯克曾說:“有聲電影的到來開啟了一個大好的時機,伴隨音樂最終完全由電影制作人控制。”可以說音樂為電影藝術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和可能性,聽覺形象的無限性擴大了視覺形象的無限性,止電影人也讓觀眾有了更豐富的符號選擇。王家衛的電影完美地達到了音樂和電影的有機結合,我們有理由期待電影人在聲畫結合上有更好地運用與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