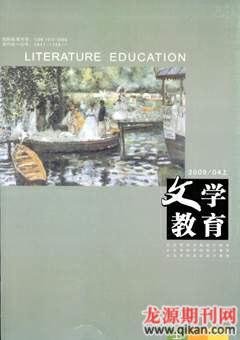李白詩散論
王 碩
一、關于李白詩歌的體裁
有唐一代是詩體的大發展和完備時期。胡應麟在《詩藪》中有這樣的感嘆:“甚矣,詩大盛于唐,其體則三、四五言,六、七雜言,樂府、歌行,近體絕句,靡弗備矣。”詩歌體裁發展到唐代,可謂是一次集大成。而且唐人還開創出了自己的獨特詩體——近體詩。近體詩自“沈宋”二人的倡導和實踐,至初唐后期定型,成為唐代占有統治性地位的詩體。不僅廣大詩人普遍樂于創作,而且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
通觀李白現存的近千首詩作,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問題:作為有唐一代負有“詩仙”盛譽的大詩人李白是以樂府、歌行類古體詩著稱,并以《行路難》三首、《天姥吟》、《蜀道難》、《古風五十九首》等代表作品馳名詩壇。近體詩只占很小比率。據筆者初步統計,李白全集中,現存五、七言近體絕句約九十首(不包括《靜夜思》等古體絕句),五律約八十首,七律近十首,(據1996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鮑方點校《李白全集》統計)僅占到全詩總數的約五分之一。不僅在絕對數量上只能望杜甫項背,而且在相對數量上(占全詩的比率)也不及王維、孟浩然。盡管李白近體詩中不乏佳作,如絕句《峨眉山月歌》、《獨坐敬亭山》、《忘廬山瀑布》、《早發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廣陵》等均為后人傳頌。但不可否認,其律詩寫得確實一般,不僅數量有限,且藝術成就不高。僅有《渡荊門送別》、《送友人》、《登金陵鳳凰臺》等幾首得到后人稱許。不得不讓人感嘆:在唐代,李白似乎是被“排斥”在主流詩壇之外的詩人。這種情況絕非偶然。
有人說,近體(尤其律詩)成熟于杜甫晚年漂泊西南之時,李白還不諳近體之道。這種說法看似有理,但卻不能解釋早于李白的“王、孟”二人的近體詩創作,尤其是王維的五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筆者以為還是應該從李白的個人氣質和性格方面找原因。
我們知道近體詩(尤其律詩)要求甚嚴,不僅要求音律上的平仄粘對,句式上的對仗,而且各聯之間還要遵循固定的格式即所謂的:起、承、轉、合。嚴重限制了詩人的個性發揮。李白天生放蕩不羈,無拘無束,當然不習慣這眾多的束縛。我們可以看到:李白的近體絕句,大多是山水游記和送別之作。這些詩大多是詩人抓住眼前實情實景,一揮而就寫成的佳作,正符合了詩人飄靈灑脫的個性。至于律詩確不為其所擅長,偶有為之,也多為唱和之作。如回贈給杜甫的那兩首五律《沙丘城下寄杜甫》和《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不僅格律不嚴,而且藝術成就亦不能與杜甫相比。又如《等金陵鳳凰臺》,據說是詩人因游覽黃鶴樓時為崔顥的詩才所折服,欲題詩而不得。但狂放的李白是定然不“服輸”的,于是在游金陵鳳凰臺時,和崔詩的原韻寫了此詩,以挽回顏面,實有勉力為之之嫌。此詩后世學者評論不一,但總體意見仍是認為此詩不如崔詩。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李白不多為近體(尤其律詩),是揚長避短之舉,亦是性格使然。
二、李白詩歌的藝術特色
若論藝術特色的鮮明,中國詩歌史上恐怕再也沒有哪位詩人能與李白相比,李白的特色是獨一無二的。筆者在此想談三點:
其一,鮮明的形象塑造。李白詩歌善于塑造鮮明的藝術形象,尤其是自我形象。如《月下獨酌》,詩的開頭兩句“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簡單的兩句卻是全詩的總背景,給人留下月光皎潔的夜晚,詩人獨自一人在花叢中飲酒無伴的整體形象。接下來兩句“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詩人沒有知己,便想象以明月作伴,這種神來之筆將詩人那充滿幻想和童真的形象表現的活靈活現。“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似乎讓人聯想出詩人對月狂歡仍不盡興,而借助酒興在月光中狂歌亂舞之像。“我歌月徘徊,我舞月零亂”,詩人似乎與月亮融為一體了。全詩把詩人狂放不羈的性格和形象描繪得淋漓盡致。
此外,李白詩歌還描繪了各個階層正反兩面人物形象。對正面人物,詩人總是帶憎恨的感情,用銳利的筆法勾勒其丑惡嘴臉和污濁靈魂;而對下層勞動人民,詩人則以飽含同情的筆調,描繪他們美麗的外表和高尚的道德以及內心的痛苦和歡樂。《古風五十九首》之二十四和《丁都護歌》即分別是這類詩歌的代表。
其二,奇特的想象與大膽的夸張。藝術是生活的反映,但詩人在反映現實時,往往借用超現實的藝術手法。詩人具有豐富的想象力,當他痛恨現實社會的黑暗、熱烈追求理想境界時,往往虛構出仙境與幻境;當現實生活本身不足以表達他的滿腔豪情與憤懣時,詩人又常常借助于想象與夸張。
如《蜀道難》通過對蜀道山川的夸張描寫,極言其險,不可攀越,隱喻自己仕途的坎坷和對黑暗現實的激憤。又如《秋浦歌》之十五,詩人描寫愁緒時,運用夸張手法,把描寫對象(無形的愁)與具體事物(有形的發)聯系起來,以“白發三千丈”喻言愁緒之深,使得無形的“愁”通過有形而夸張的“發”,表現得形象鮮明,給人以具體生動之感。想象和夸張手法的運用,使李白的詩歌具有夢幻般奇特的意境,激昂豪邁的情感,奔放飄逸的風格。讀后給人一種豁然開朗、激情澎湃、樂觀向上之感。
其三,明白曉暢、樸實自然的語言。李白是以超凡的才氣寫詩。他善于抓住生活中情與境相會的時機和情感波動的瞬間,淋漓盡致的表露興致與真情。往往靈感產生,興致所達,則揮毫立就。所謂“李白斗酒詩百篇”(杜甫《飲中八仙歌》)即言詩人作詩的超凡靈感。所以李白的詩不需要長期醞釀,亦不必在遣詞造句上過分錘煉與推敲。與杜甫“為人性僻為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江上植水如海勢聊短述》)不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李白《經亂離后天疏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衣宰》),道出了詩人在詩歌語言藝術上的追求。因而,李白的詩沒有苦吟的味道,沒有錘煉的痕跡,韻味天然,語言明快。如《贈汪倫》,前兩句“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以簡明的筆調,清晰描繪出離別前情景,但卻不含悲傷之意,而表現出一種豁達和灑脫;后兩句以桃花潭水之深就近取喻,巧奪天工,感情真摯。又如《望天門山》:“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本詩中,詩人用白描化的語言,勾勒出一幅幅鮮明而生動的畫面,語言清麗明快而又韻味深長。
千百年來,李白詩歌廣為流傳,上至才子佳人,下至勞苦大眾,對其詩大多能隨口道來。一些作品如《靜夜思》、《早發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廣陵》等還被當作兒童的啟蒙詩歌讀物。這與其詩明白曉暢、樸素自然的語言風格不無關系。
三、李白詩歌與“盛唐氣象”
公元八世紀前半葉即唐代玄宗(李隆基)統治時期,由于經過初唐百余年的發展和積累,出現了一個社會高度繁榮的局面,史稱“開元盛世”。天才詩人李白即生活于這樣安定富庶的時代。“國力的強盛,經濟的繁榮,思想上的兼容并包,文化上的中外融合,創造了對文化發展極為有利的環境;盛世造就了士人的進取精神,開闊胸懷和恢宏氣度,極大地豐富了文學的創造力。”(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卷)盛唐詩人將那種博大寬廣的胸襟,豪邁雄壯的氣魄,昂揚向上的精神,融入到詩歌的創作中,使得盛唐詩歌呈現出一種與其他歷史時期不同的獨特風貌,即被后世稱道的“盛唐氣象”。“盛唐氣象”是唐代社會政治安定、國家統一、經濟繁榮和思想解放的產物。作為一種文學術語,其具體內涵是:健康向上的風采,恢宏豪邁的氣質,雄渾寬廣的境界(趙克堯《盛唐氣象論》)。
在盛唐詩歌中,我們幾乎找不到消極頹廢的意志、悲苦凄涼的情境。即便是描寫邊疆戰事也是體現出“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王翰《涼州詞》)的曠達豪邁之胸襟。即便是描寫秋湖景色也蘊藏著“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孟浩然《臨洞庭湖上張丞相》)的雄渾寬遠之意境。
在整個盛唐詩壇,“李白的詩歌是‘盛唐氣象的最典型代表。”(林庚《盛唐氣象》)的確,李白詩歌諸如那“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將進酒》)的非凡自信;那“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渡荊門送別》)的闊大意境;那“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瀉入胸懷間”(《贈裴十四》)的恢宏氣象,加之整體上呈現的清雄奔放、飄逸豪邁的風格,使其詩無處不煥發出“盛唐氣象”之氣息。
可以說:“盛唐氣象”造就了天才詩人李白,盛唐詩壇因有了李白而更加絢麗多彩,中國文學史因有了李白而更加輝煌燦爛。只可惜唐代自“安史之亂”后即由盛而衰,中國封建史上再也沒能出現“盛唐氣象”那樣的文學空氣,亦再也不能造就出第二個李白了,李白成了中國詩歌史不可逾越的藝術高峰,這不能不說是“詩國”的悲哀。
王碩,湖北師范學院文學院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