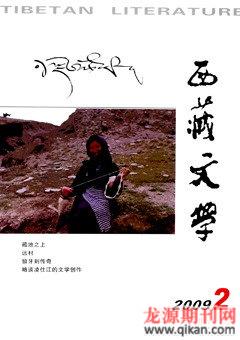降臨
凌仕江
寫一組文章的創作談。好比寫一本書的后記,這樣的時刻是許多正在夜色里獨行的作家十分期許的。我想這里面大概有一種叫著“快感”的東西存在,一方面既有渴望停下來去別處玩玩的想法。另一方面又有期盼下一次重新出發的激情和準備。
但這樣的結局會出現在什么時候?真正的寫作者是全然不知的。特別是那些從事長篇小說創作的人,盡管迫不及待地想早一天收工,甚至恨不能早一點進入“后記”的寫作,可這樣的事情是萬萬不能操之過急的,你一定要有耐心和毅力,這樣才能遇見降臨的時刻。我把克珠群佩先生在一條短信中囑我為即將發表的《藏地之上》這組散文寫一篇創作談的事兒,看得十分神圣,好比“降臨”這個詞匯。
其實,這本身就是一個降臨的時刻,我身邊的人們都提前回遠方的故鄉過年去了,有的或許正在乘船,有的或許正在轉機的路上,只有高原不明不暗的星光陪同我的文字,在靜靜的夜色里慢慢抵達。四周靜靜的,好像這樣的時光就是讓我一個人用來回憶的,奇妙的是,此刻我回憶的盡是四川盆地的一些人和事。還有我所走過的一些山南水北的影子,那么瑣碎。那么模糊,那么多猶如乞丐趕也趕不走的回憶,這不成樣子的回憶自然關系到我與西藏的關系和我的創作。盆地與西藏是奔走者的二度空間,它們構成了我精神的故鄉,也就是說。我在四川或在盆地之外的許多地方,也會像此刻自然地回憶或想念在西藏的各種場景和片斷,相反,那時的西藏在腦海里的印象,比之此時的盆地要清新得多。對于記憶,如果盆地只是一種重現,那么西藏則是一種降臨,這地脈相接的回憶難道不可以叫神圣的“降臨”嗎?我平靜地等待降臨,這不是我生活的有意為之,有時感覺來了甩也甩不掉。當然,在西藏回憶盆地,很多時候我面臨的是無法重建的影像困難,尤其是想起早些年,一次次從成都返回我生命的根據地自貢榮縣。我曾寫下一個標題《一路盛開的憂傷》,可那樣的內容沒有能夠一直延續下去,原本那是一部厚重的長篇散文,因為西藏的原因,我只寫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章節,而每次在盆地憶起西藏,回憶卻一次次成全了我對西藏靈魂的重建和想象,仿佛我立即騎上了夢中的白馬,在藏地之上穿行,不用揮鞭,一眨眼,或一轉身,已走過草原,走過寺院。走過雪線,走過陽光,走過傳說,走過風。走過血。走過人,走過靈魂,走過鮮花與果實裝點的節日,走過泥濘凍結的戰爭,來不及拐角,所有的蹄印,都生長出風景,它們如花朵般綻放,到處都是文章。
有人說,熟悉的地方沒有風景,我想遠離熟悉的地方,自然會想起風景,這是超隱喻的自然法則,也是我面對西藏不寫西藏的原因。毫不夸張地說,很多時候,我是在不斷遠離西藏的時光中揀到這些文章的,在一個越來越熟悉的環境里坐下來想遠方的西藏,西藏在我筆下一步步延伸至陌生狀態,我想這首先恰到好處地滿足了我生理的需求。好比我一針見血地止住了自己身體某個“痛”的部位。當然,這其中也包括許多來信來電的讀者,他們對西藏的關愛遠遠超越了我寫西藏的意義。當一個人常常游離在生活之外的長街短道,心堵得慌的是西藏,暢懷心襟的也是西藏,可無法意料的是,最終它們成了生命中這些看不見痛感的文字,所有的痛感已潛伏在被風吹過的傷口之下。那么,西藏到底意味著什么?或西藏究竟是什么?這一問題,也許他們尚未想過,對此,我已經在前不久創作的一部《0米喜馬拉雅》的新作中進行了闡釋或回答——不求天和堂,恩愛西與藏。有一直生活在西藏的人看了我筆下的西藏,說我說出了他們想說但一直沒說出來的話。在他們眼里,也許石頭永遠只是石頭,波浪白晝也只是波浪,只是他們沒有遇見降臨,我遇見西藏。或西藏遇見我,這都是緣分中降臨的時刻。
既然注定,就要珍惜。
最后,我還要替讀者感謝用心編輯《藏地之上》的編者,我們不只是說好一起去西藏。我們一同接受神圣的降臨。
責任編輯:克珠群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