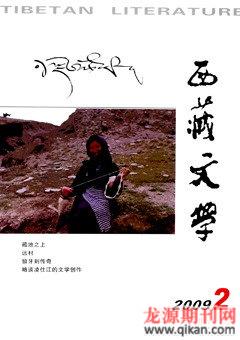就像格桑花在陽光下盛開
王雪瑛
冬日的夜晚,暖色的燈光抵抗著窗外彌漫的黑暗和寒冷,我的視線沿著《天邊的納木措》的字里行間,漸行漸遠,忘記了一個職業編輯的日常冷靜,心仿佛飛躍了萬水千山。來到了天邊的納木措,那片遠離塵囂的無垠之藍。看著初雪般晶瑩清澈的湖水,看著陽光在湖面上安靜地打盹。聽見自己孤寂的心在水邊有力地跳動。
我想起了勒·克萊齊奧的長篇小說《長途旅行》里的第一句話:“阿烏爾布先生,您何時啟程?跟隨著阿烏爾布先生,那雙想象的眼睛,那另一個人就要開啟一個全新的世界了。”而我也跟著凌仕江先生的文字,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一個格桑花開,風過無痕的西藏;一個陽光如瀑天天天藍的西藏;一個雪山綿延,超凡人圣的西藏……
如果你在都市渾濁的空氣或洶涌的人流中感到壓抑,如果你在現代傳媒無窮無盡的信息包圍中感到麻木,你會渴望進入這樣一個喚醒了想象力和被想象力呈現的世界;你會流連在這樣一個遠離你的日常經驗之外的世界;你會被西藏這個自然之子的神奇容顏所吸引。而凌仕江的寫作就是對西藏容顏一次次地凝望,與西藏內涵的一次次地對話。因為他就生活在西藏,十多年來他的生活就在高原和平原之間度過。十多年來他的青春也在西藏的雪山和峻嶺之間奔流,西藏的神奇和純凈,西藏的壯麗和雄渾成為他人生的風景,也成了他青春日記里永不失落的主題。
在《天邊的納木措》里,我聽見了他和牧人的對話。一個蒼老的牧人對他說:“你來納木措看水,水在看你的心。”而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我到納木措,不是為看水,只為看一眼時間停在天邊的皺紋。”在《梅里雪山的雪》那純美的冰雪世界中,他又想象著自己在城市中的未來生活。他擔憂物質對心靈的異化,他審視自己的選擇,他對自己的判定是:“我做到的只是沒有遠離詩意。”
《內心的河流》中他不但寫出了拉薩河的四季,也寫出了拉薩河在他內心的流淌,“夕陽西下,濃墨重彩的必燒云潑在河水緩緩流過的河床上。暮色四合,搖著經筒的老阿媽斑白的發絲在風里飄蕩。一汪在陽光下藍花花的水。不緊不忙地滋潤著我的靈感和身體,使我教年如一日地寫下一個地域的文字。”讓我看到了拉薩河與拉薩這座城市的交融。也看到了拉薩河與他心靈的交流。而《苦讀珠峰》的文本中流露出的是他對珠峰的解讀,深入到了歷史、文化的高度,他提醒自己,也提醒眾人:“越來越多的人挺進珠峰,越來越多的人向珠峰發起挑戰。但越來越多的遺憾是,越來越多的人讀不懂珠峰。”我想這是他的提醒,也是他對自己內心困惑的敏感和揭示。
在西藏的生活當然不會是一部風光片,西藏的山水風物,西藏的天地靈氣塑造出的是人。《西藏男人》、《闖進西藏的女人》都是他對西藏人的關注與描摹。從標題就可以看出,他是從本地與外來,地域的本色和融入的異彩兩個不同的層面去描繪他眼中的西藏男人和女人。我很欣賞他寫西藏男人時,切入的多種角度。角度一,“如果說西藏女人是打酥油的好手。那么西藏男人則是喝茶的高手。他們可以無憂無慮從早上九點喝到晚上深夜,甚至可以從茶中喝出自己的愛情。”角度二,“西藏男人的歌聲像山谷的風一樣。無論如何地抒情,也掩不去那刻骨的蒼涼。這樣的真情足以征服每一座雪山上有著真情的靈魂!”角度三,“翻開西藏厚重的歷史。發現藏族發展的歷史并不是對這些山的征服、掠奪、廝殺的斗爭史,而是與山為伴,與山相愛。與山廝守的歷史,可以說西藏的男人都是山做的。”角度四,他把自己也歸入了西藏的男人。他筆下的西藏男人是生動可感的,也是需要你以自己的想象力去塑造的。
如果說西藏的山水和人文是他真實的生活環境,是他青春的成長空間,也是他重要的寫作主題,那么他又是以一種怎樣的方式來展示自然與心靈的交流呢?在他散文的敘事中有什么特點呢?
西藏蘊含著無數的神奇,而凌仕江以年輕而善感的心發現和體驗著西藏自然中的神奇。在這樣一個被科學和理想所闡釋的現代社會里,他給我們帶來一種寫實與神話自然轉換的敘述空間。當然他的神話不是宏大敘事意義上的,而是細膩的,由意象和細節呈現出的神性。
在《另一座高原的細節》中,我看到了他的敘述中現實與神話不露痕跡地自然過渡:“幾天之后,我住進了卡普的家里。后半夜常常被風喊醒——那時的夜空無比空靈,熠熠青光從天宇傾瀉而下,有淡淡的魚紋在天幕里游游蕩蕩,大地如同爺爺的爺爺舒展著筋骨的筋骨,透窗而入的遠山圣潔脫塵,屋外叮咚低吟的小河遍體流銀。仿佛可以讓我一個人在遠離和寂寥中揭開一個靈異纏繞的世界。”
西藏是山的博物館,西藏是陽光的家園。走進西藏的畫卷,雪山和陽光是不可或缺的兩大意象。也是凌仕江散文中的重要意象,雪山和陽光以自然的力量和神性的光芒喚醒著我們內心的詩意和激情,也在他的筆下閃爍出神奇的斑斕。《握一把蒼涼的陽光》中處處可見陽光灑落他的心田,而他的文字中又透出陽光的氣息。“西藏的陽光是燃燒的錫,閉上眼睛也能讓人感受到耀眼的明亮。在云里,在納木措碧藍的水草上,在漫山遍野的雪蓮之間,在吹滿長風的山谷里。陽光就像拉薩通往林周那一路上的胡楊葉子。簌簌地從天頂上落下。把許多神秘和蒼涼的美感一直落進我的心里。”
“老牧人吹著口哨走了,他獨自沿著白云的影子一路向西。”雖然文句中并不出現“陽光”,但陽光在他的心里,因為沒有陽光就沒有白云的影子,這真是寫陽光的傳神妙筆。
“陽光邁向成熟的田坎,青稞揚花了。長長的穗從細小的夾縫里奔竄出來,在雪野里寫著我無法描摹的藏文書法。”“邁向”兩字讓陽光從天上走向了人間。只有一顆在陽光下融入自然的心,才能寫出這樣唯美而又自然的句子。只有真正融入自然的心,才能和自然對話,無論是清新的晨曦還是絢爛的晚霞,無論是雄奇的雪山峽谷,還是激越的河流湖泊,無論是冷峻的荒漠戈壁,還是安寧的山寨人家,都是西藏原始而新鮮的語言與符號,他們的豐沛與流動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心靈資源,也讓我們有了反思城市生活的能力,讓我們嘗試以寧靜躲避喧囂,以質樸洗去浮華,以悠然抵御焦灼。
幾天來東海之濱的天空總是被寒冷的云層包圍著,在溫暖的燈光下我讀完了那些聽得見自然心跳的文字。窗外是一片黑暗,晶瑩的雨絲不知疲倦地在玻璃上寫下一行行詩句,靜默地等待著閱讀的眼睛。我的思緒穿越冬雨,飛得很遠,很高,西藏的夜空中滿天的星光是不是等待著相通的心呢?我想起了美國哲學家愛默生說過的話。星星成了思想的閃光體,成了希望獨處的個體的象征。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速度時代。一個多媒體時代,網絡以神奇的傳播速度,不斷刷新著讀者的眼球,現代的通訊技術,讓地球變成了一個村落,現代生物科學似乎可以將以往的神話變成現實。克隆技術的進步、人類基因圖譜的破譯讓人類越來越敢于幻想,我們可以超越自然的法則嗎?我們的欲望可以被無條件的滿足嗎?以人類的智力和欲望建造起來的城市日益強大,我們常常忘記了曠野的存在,忘記了對自然的敬畏,日益嚴重的污染、災害性的天氣、有限的資源不斷地提醒我們:我們是自然中的一員,對自然的毀壞,就是對我們自己的傷害。
凌仕江的寫作中并沒有環保主義的說教,但這的確是他寫作的重要時代背景,我們的時代面臨的課題中不能忽略自然對我們的意義。愛默生讓我們在研讀自然的過程中了解自我,我想在與自然對話的過程中,我們才會感悟自然賜予了我們什么,在遠離自然的過程中我們丟失了什么?自然不僅是我們生存的環境,還是我們審美的天空,是我們審視城市生活的重要參照系。
2008年的九月,我從上海飛到了北京。在魯迅文學院的評論家研修班里,我和凌仕江成了同學。在北京的秋天里,太陽常常從湛藍的晴空中無聲地飛流而下,望著純凈的晴空,我會忍不住地問:“西藏的天空還要藍嗎?西藏的陽光還要亮嗎?”他總是拉長聲線肯定地向我宣布:“還要藍,還要亮——”從沒有到過西藏的我還是難以想象,只能回答他的名篇——《你知西藏的天有多藍》。
閱讀作品是熟悉一個作家的最好途徑。他對寫作是非常認真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在仔細地審看、修改后,才定稿的。但在談到自己的寫作時,他是很自信的,對自己有很高的期許。我想這是自然對他個性的一種塑造,嚴謹而敏銳,自信而坦然。青春的生命在西藏的自然中展開,是一種成長和磨礪,也是一種詩意的綻放,就像格桑花在陽光下盛開,青稞在陽光下抽穗,沒有什么可以影響格桑花在天空下的綻放,也沒有什么可以阻礙青稞在高原上的生長。那是生命和自然的交融,也是心靈和自然的對話。
只有一顆善感的心,才會有一雙敏感的眼睛,才能透過城市的塵埃看到自然深處的寧靜和神奇,才能用文字構筑一個詩意的世界。他的文字有著雪的純凈與輕盈,也有著鷹的矯健和力度,飄落在大山的皺褶中,飛翔在審美的天空里。
責任編輯:克珠群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