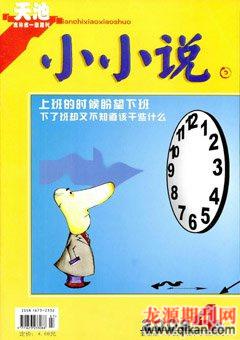釣魚
懷 銳
傍晚,細雨蒙蒙,我和老張提著漁具走下江堤。等我們裝好漁具,支好傘,天空又不下雨了。我笑著對老張說:“你說這天氣怪不怪,有傘不雨,無傘呢則雨。”
老張說:“誰猜得透老天呢。”
正說著,老張嘴巴一緊,漁竿一提,一條鯽魚便破水而出,直線般送到老張的手里。老張笑笑說:“看來,今天開頭不錯。”
我看看自己水里的浮子,還是一點動靜也沒有。天空又飄起了雨絲,打在水里咝咝作響。
“老陳,你看。”江堤上下來了一個人,看樣子,也像是個釣魚的。
老張笑著說:“想不到還有和我們一樣的人呀。”
“可能人家和我們一樣忙了一個星期,也想趁這個時候找個清靜的地方放松一下。”
那人沒向我們這邊走來,而是挑了一個離我們有一段距離的位置。他戴個帽子,帽檐壓得很低,看不清他的臉。
這時,我突然感到自己手里的漁竿被拽了一下,才發現已經有一條魚上鉤了。提上來,卻是一條小魚,接著就再也沒一條魚上鉤了。再看看老張,他已經釣了好幾條了。
我見老張的得意樣,就覺得無味。接著,便想起了剛才那個人,就站起來,朝他那邊走去。
“釣到了么?”我問。
“嗯。”他沒有回頭。
我蹲下來,翻看他的魚簍,還真不少。
我說:“你釣魚還挺內行的嘛。”
“馬馬虎虎。”他還是沒有抬頭。
回來時,老張聽我一說也想過去看看。我說這人有點古怪,最好別自討沒趣,老張也就作罷了。
接下來兩個星期,那人沒有來。我和老張沒事兒時,偶爾也會聊起他。
也不知道哪個星期,同樣是傍晚下著小雨,那人又出現在江邊,一樣的打扮,一樣的枯坐。我有時還是忍不住要跟他搭訕幾句,雖然他愛理不理,但我敢肯定他是個孤獨的人。
接下來,每逢雙休日傍晚下雨,他都會來這里。有一次,是個陰天,似乎有落雨的跡象,我以為他會來的,到最后下起雨來,他也沒來。第二天傍晚時,來了個年輕人,他一來就去解鎖在夾竹桃上的腳踏板。我走過去,覺得他有點面熟,一問,才知他以前來過我們單位。
老張見我跟那人聊,就跑上來問他:“那個經常來釣魚的人是你什么人呀?”
“哦,你說我們局長呀。”
我說:“他就是楊一舉?”
“嗯。”
老張說:“哪個,哪個局的?”
我說:“文化局的。”
我又回頭對那個年輕人說:“那他昨天怎么沒來釣魚?平常這個時候下雨他都會來的。”
“他最近身體不大好,住院了,昨天突然跟我說要我把這個腳踏板帶走,說長期被雨淋濕了容易生苔,以后坐上去會滑倒。”
我說:“哪個醫院呀,我們可以去看他么?”
“不必,不必,他最怕別人打擾他了。”
年輕人連連擺手,就提著腳踏板走上堤壩,只剩下我和老張呆呆地站在那里。
我們回到原位,我跟老張說應該去看看這個楊一舉,畢竟也算相識一場,老張沒多想就答應了。
我們找了幾家縣級醫院,終于在一個名氣不是很大的醫院里找到了他的名字。我們敲了門,開門的就是江堤上見過的那個年輕人。年輕人像是嚇了一跳,又囑咐我們不要待太久。我提著一袋水果進去,他在病床上轉過頭來,一副憔悴而又驚奇的樣子。
我說:“幾日不見,你就把我們忘了呀。”
他綻開笑容說:“沒想到你們會來。”
他又問我們怎么找到這兒來的。老張笑著走過去說:“楊局長,我們是……”
老張還沒說完,我見他的臉色馬上暗淡下來。
老張又說:“楊局長,我們那天知道你生病了,不知有多擔心呢。”
我向老張使了個眼色,示意他不要說了。
老張還想說點什么。這時,那個年輕人過來了。他說:“不好意思,我們局長有點累了,你們還是請回吧。”
年輕人把我們送到門口,我說:“你們領導得了什么病呀?”
“其實,我們局長一點事兒也沒有,只是最近應酬多了點,多喝了點酒。”
下樓的時候,老張還念念有詞,說他的一個親戚想開個什么店,文化局一直不批,本來想趁此機會跟他當面講講,誰想還沒開口就被人家請了出來。
第二天,老張打電話過來,問我還要不要去醫院,我委婉地推辭了。當然,每個雙休日我和老張還一起去江邊釣魚,但我總覺得身邊缺少點什么。當老張問我那人為什么就不再來時,我保持沉默。其實,我后來又碰到那個年輕人,他說他們局長現在還喜歡釣魚,只是常換位置,他想找一個清靜的地方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