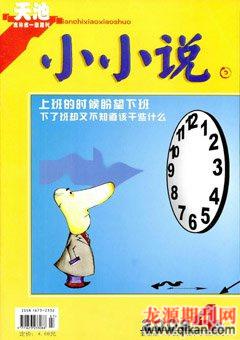阿旺嬸
遠(yuǎn) 山
村子里沒(méi)人知道阿旺嬸叫什么名兒,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是被五十歲的老光棍阿旺伯帶回村的,阿旺伯是個(gè)木匠,長(zhǎng)年挑著一副木匠工具走村串巷。
阿旺伯帶個(gè)女人回來(lái)引起了轟動(dòng)。
一頭長(zhǎng)發(fā)的阿旺嬸太漂亮了,那蓬松的頭發(fā)用一塊手帕在腦后隨意一扎,衣服雖然臟點(diǎn)還不合身,卻蓋不住她那豐滿婀娜的身姿。村里的女人不免又羨慕又嫉妒。我們一群小孩圍著她轉(zhuǎn),她始終微笑。
有時(shí)候,阿旺嬸聊著聊著會(huì)突然唱、跳起來(lái)。一首《蘇三》模仿得惟妙惟肖。
原來(lái)阿旺伯帶回的是個(gè)“白癡”。
可阿旺伯不管別人怎么指點(diǎn),仍把她當(dāng)寶貝一樣的疼。
阿旺嬸每天都傻傻地笑,從來(lái)不攻擊別人,尤其喜愛(ài)小動(dòng)物。
我對(duì)阿旺嬸的親熱,是源于幾次割豬草。
那時(shí)一放學(xué),我就背著大背籮去山上割豬草,跑東跑西到天黑總還裝不滿一籮筐,這樣回家是要被娘罵的。有一次,阿旺嬸笑嘻嘻提著一網(wǎng)袋豬草來(lái)到我面前嚷著“給你、給你。”
我不知道她為什么對(duì)我特別好,許是我看到幾個(gè)惡作劇的小孩兒向她扔石子時(shí)呵斥過(guò)小孩兒;或是那次她裸著身子在村子里邊走邊唱,我脫下自己的外衣替她遮過(guò)羞。總之,我去割豬草都能收到她的一大網(wǎng)袋早已為我割好的豬草,有時(shí)候還會(huì)偷偷地塞給我?guī)讉€(gè)熱膜膜。
那段日子,我有時(shí)候和阿旺嬸一起坐在石塊上玩撿石子,或者跳房子。偶爾她會(huì)拿來(lái)兩只裝面粉的袋子套在手臂上給我唱《蘇三》。
沒(méi)過(guò)多久,阿旺嬸懷孕了。阿旺伯五十歲得子該是件喜事,然而,村子里的老人們都說(shuō)阿旺伯是個(gè)“太監(jiān)”呵。
我不明白“太監(jiān)”是什么意思,去問(wèn)娘,被罵了一頓。
也就是從那時(shí)開(kāi)始,村子里很難見(jiàn)到阿旺嬸的身影了,聽(tīng)娘說(shuō),阿旺嬸被阿旺伯關(guān)到了一間小房子里不再讓她出來(lái),阿旺嬸不吵不鬧仍然笑嘻嘻的。
阿旺伯發(fā)現(xiàn)阿旺嬸懷孕后,每天出去找活了。每天一早,在關(guān)阿旺嬸的小房子里給她放上一桶井水和幾個(gè)膜膜。村子里的男人也不敢再打阿旺嬸的主意了,因?yàn)榘⑼弥琳ㄋ幵诖遄永锇l(fā)狠話:他要是知道誰(shuí)把他媳婦的肚子搞大的,就炸了他全家。
我讀書(shū)的小學(xué)建在村子的半山腰上,距阿旺伯的兩間土房不遠(yuǎn)。
好幾次我偷偷去看她。躲在關(guān)阿旺嬸的房子角落盯著,看有沒(méi)有男人去看望阿旺嬸。這樣觀察了好多天,一個(gè)也沒(méi)見(jiàn)到。
阿旺嬸在那樣的環(huán)境里,在沒(méi)有任何營(yíng)養(yǎng)補(bǔ)充的條件下,居然度過(guò)懷孕期。這時(shí)候,阿旺伯也不再冷著臉了,有時(shí)還會(huì)帶著她在學(xué)校邊走動(dòng)一下。
阿旺嬸那雙茫然清澈的眼睛給了我很大的溫暖。我從沒(méi)把阿旺嬸看作是個(gè)傻子,有一次,我偎在她身邊,摸了她那高高隆起的肚子。我感覺(jué)到了生命的神奇,阿旺嬸仍然不知道自己是誰(shuí),但她知道自己要當(dāng)母親了,她總是用雙手撫著肚子,喃喃自語(yǔ),不清楚她說(shuō)什么。
村子里又一次因阿旺嬸熱鬧起來(lái)。淳樸的村民拿來(lái)了自家小孩穿剩下的衣服,阿旺嬸就傻傻地笑。
最后一次看見(jiàn)阿旺嬸是躺在村口的大操場(chǎng)上。村民叫來(lái)了懂醫(yī)的爺爺,爺爺看了看,搖搖頭走開(kāi)了。
阿旺嬸的肚子已經(jīng)癟了下去,旁邊用一條草席裹著一個(gè)小生命。
阿旺伯蹲在路邊哭得驚天動(dòng)地,村民跟著抹眼淚。聽(tīng)娘說(shuō),阿旺嬸是被村子邊上的一個(gè)什么單位的汽車給撞了。
本來(lái)被撞的不是她而是村里的一個(gè)小孩,娘說(shuō),阿旺伯哭得那么傷心是因?yàn)榘⑼鷭鹪陂]眼前對(duì)阿旺伯說(shuō),她叫素云,她記起了自己的名字和家,可沒(méi)說(shuō)完就死了。
村民們?cè)谏缴蠋桶⑼诹藘勺鶋災(zāi)梗淮笠恍 ?/p>
那天,我到阿旺嬸的墳地,插了一大把的杜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