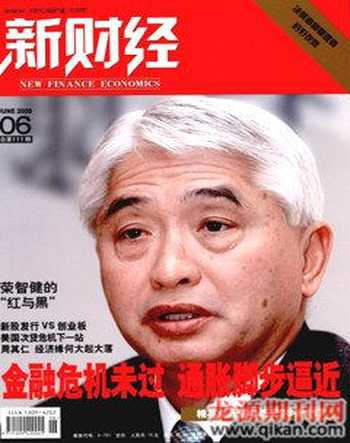從吳英案透視民間金融的尷尬境遇
崔曉紅

在一個小小的縣級市,吳英就可以非法吸納如此巨大數額的民間資金,說明大量的民間游資急需出口。國家應該予以重視,出臺更加明細的法規,一方面給民間游資以出口,另一方面,也部分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
2009年4月16日,吳英站到了法庭的被告席上。當日,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首次開庭審理吳英涉嫌集資詐騙一案。這也是她自2007年2月被批捕以來,首次在公開場合露面。
庭審現場,來了30多家媒體及近200名旁聽者,足見外界對這起案例的關注程度。盡管吳英的暴富神話已于兩年前終結,但只要案件一日不審理,法庭一日不宣判,公眾就會等著看。這就像一出話劇,雖然大幕已經落下,但只要主角不出來謝幕,就不能真正算完。
當天,吳英身穿白色長袖T恤衫,外套黃色馬甲,梳著馬尾辮。從她在庭上的表現看,她是做了充分準備的,她甚至當庭翻供,為自己作最后的努力。
庭審從早上9點30分一直持續到下午6點35分,雙方爭辯激烈。法庭沒有當庭宣判,表示擇日再審。
財富神話的緣起與破滅
吳英“出名”是在2006年,迅速而突然,猶如一出鬧劇,沒有鋪墊,沒有前奏,直接進入高潮。有關她的報道充斥報刊雜志以及網絡,諸如“東陽女演繹暴富神話”、“億萬財富是怎樣煉成的”等標題相當打眼。
一些媒體報道說,吳英的財富高達38億元。按這個數據,她可位列2006年胡潤百富榜的第68位,女富豪榜的第6位。這一年,吳英只有26歲。
在此之前,吳英還只是一個開美容院的小老板。她的背景也不復雜:東陽市歌山鎮塘下村人,曾在東陽技校就讀一年半后輟學經商,父親曾是一包工頭,母親務農。
幾乎毫無征兆,美容院的小老板突然發跡。2006年10月,吳英一擲千金買下了東陽縣城漢寧街的700多間商鋪,隨后一口氣注冊了十多家公司,并成立了本色集團,自任董事長。在東陽的黃金街道,吳英名下的產業隨處可見,本色商貿城、本色正道汽車服務、本色網吧、本色建材城、本色概念酒店、本色咖啡館……
人們對此類充滿傳奇神秘色彩的暴富故事總是充滿了興趣,更何況主角又是一個只有26歲的年輕女子。
對于吳英巨額財富的來源,民間猜測五花八門:有的說她是炒期貨賺的,有的說是她向義烏、溫州、東陽一些老板融資而來,還有的說是走私、販毒、賣軍火、幫人洗錢賺的,甚至還有人說是繼承了東南亞某國軍閥的遺產。
吳英自己的解釋是,賣“羊胎素”賺到了第一桶金,隨后得到一位高人指點,炒期貨獲利不少。另外,還有部分資金來自家族成員的支持。
一時間眾說紛紜,人們進行著各種猜測、遐想和演繹。但很快,東陽市公安機關介入,推翻了上述的所有說法和猜測。
2007年2月7日,吳英在首都機場被警方抓獲;2007年3月16日,吳英被東陽市檢察院批捕;警方以吳英涉嫌合同詐騙及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立案。
一度被爆炒的財富神話,就此終結。
吳英案VS孫大午案
2008年10月27日,金華市檢察院向金華市中級法院提起公訴。事實上,吳英被捕后,案件經過兩次補充偵查,才最終被提起公訴。公訴機關也從開始的東陽市檢察院改為金華市檢察院。起訴罪名從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合同詐騙,最后確定為集資詐騙。
檢察機關的起訴書中寫道,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吳英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個人或企業名義,采用高額利息為誘餌,以注冊公司、投資、借款、資金周轉等名義非法集資,所得款項用于償還本金、支付高息、購買房產、汽車及個人揮霍等,集資詐騙人民幣達38985.5萬元。集資詐騙數額巨大并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應當以集資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
在法律上,對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將如何認定?《新財經》記者采訪了法學博士許志永。他說:“按照我國現行刑法相關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指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規,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行為。集資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行為。兩者最主要差別,就是動機不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可能是企業以經營為目的,資金周轉不開,約定還本付息,主觀動機是為了經營。而集資詐騙,核心在詐騙。主觀上不是有信心或者是有希望能還,客觀上也不具備還款能力,只是通過某種方式不停地卷錢。”
吳英案很容易讓人想到2003年曾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另一案件,孫大午案(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大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一案)。
許志永就是當時孫大午的代理人。孫大午當時是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起訴。對比這兩起案件,許志永說:“吳英案和孫大午案存在相似的地方,都是借錢,約定還本付息,區別在于募集資金的范圍和數量。孫大武案的集資對象大部分集中在熟人社區,募集資金量也要小一些,最后法院認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只有1300多萬元。”
2003年10月30日,河北省徐水縣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孫大午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10萬元。對于這一判決,公眾普遍認為法院量刑偏輕。許志永分析“偏輕”的原因在于:孫大午在當地百姓中的口碑較好,當地百姓認可這種方式。而且,孫大午完全有能力償還,公司的負債率不高,只有40%。許志永還告訴記者,孫大午“非法集資”的款項早已經還上,“案發一兩年后就都還上了。”
就目前來看,吳英面臨的形勢要嚴峻得多。吳英的代理律師楊照東也坦言,上述兩個變化對吳英來說是非常不利的信號,“其一,一審從基層法院改為中級法院,區別是基層法院審理的案件最高只能判十五年,中級法院可以判到無期徒刑以上;其二,罪名從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改為集資詐騙罪,前者最高刑罰是十年有期徒刑,而后者如果是自然人犯罪,則最高可以是死刑。”
吳英翻供與律師的無罪辯護
面對公訴人的指控,代理律師楊照東為吳英作了無罪辯護。雙方就罪與非罪進行了激烈辯論。爭議的焦點是,吳英借來的巨款是否存在主觀故意詐騙,這將決定吳英最終面臨怎樣的刑罰。
檢察機關認為,吳英明知本色集團的經營狀況不可能負擔如此高額利息,仍向債權人大量借貸用于償還利息,明顯屬于詐騙。本色集團旗下產業不過是吳英非法集資的工具。
楊照東則認為:吳英借來的錢只是朋友間的民間借貸行為,并沒有使用欺詐手段,也沒有要非法占有的想法,借款用于本色集團的經營活動,并承諾歸還。吳英的行為不構成集資詐騙罪,只能算民事糾紛。
庭審現場,吳英本人也為自己作無罪辯護。她說自己沒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也沒有個人揮霍。她甚至當庭翻供,表示之前在公安機關所作供述,是受人誘導,“有人跟我說,這樣說才能早日取保候審。”吳英反復說,她借款是以經營本色集團為目的,“想做到上市,如果不是被抓,錢也許是有機會還上的。”
對于吳英的翻供,許志永認為也在情理之中:“數額那么大,很可能是會判死刑的。她聰明一點的話,當然應該說有信心或者是有能力還上,這是生與死的區別。從法律角度看,不認罪、翻供,犯罪情節可能會加重。但是,對她本人而言,可以說是最后一搏。”
雙方爭議的另一個核心是:是不是“非法集資”。最高院的司法解釋認為,所謂非法集資,是未經批準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的行為。那么,吳英的集資對象是否屬于“社會公眾”的范疇?檢察機關認為,吳英與大部分集資對象之前并不認識,應該歸入“社會公眾”的范疇。而楊照東則認為:目前起訴書認定的吳英的集資對象只有林衛平等11人,這些人有些是吳英的親朋好友,有些后來成為了本色的高管,屬于特定人員,并不屬于“社會公眾”。
據許志永回憶,如何認定不特定人群也是當年孫大午案的爭議焦點。“當時,對方認定都是不特定民眾。他們有一個邏輯,就是只要有一個‘不特定就都是‘不特定,這個邏輯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也存在說不通的地方,照此邏輯,屬于特定的也都變成不特定了。比如,孫大午的父親將4000元錢存在兒子處,就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了?哪些屬‘不特定范疇?家人、親戚、朋友、員工,是‘特定還是‘不特定?對于這一點,法律規定并不明確。因此,從辯護角度看,也就存在較大的辯論空間。”
從孫大午案到吳英案,
金融體制沒有明顯進步
吳英案庭審現場,坐在旁聽席上的,有相當一部分是吳英的“債主”。原本希望有高額回報,沒承想,“借出”的錢有去無回,損失慘重。
有人認為,吳英案再一次拷問了中國的商業監管機制。本色集團在成立之初就疑點重重,監管部門沒有及時介入,任憑吳英把騙局搞大。據悉,在本色被查封后,外地大筆資金還在涌入其賬戶。這一方面說明公權力的行政不作為,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當地政府信息公開化與透明化的欠缺。
對此,許志永表示,“監管部門當然負有行政責任。”但他并不主張實施特別嚴格的監管,“因為有很多小企業初期發展需要靠這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地方經濟發展。這種民間借貸在江浙地區比較普遍,其實是一種半公開狀態。一邊缺錢要貸,一邊有錢要放,有需求就有市場。政府真的想取締,也不容易,最好的辦法就是陽光化。”
許志永認為,中國金融體制目前存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監管層次不夠科學,不能滿足社會需求。“金融體系應該分更多的級別,你什么樣的信譽等級,可以做什么樣的事,可以進入多少資金。信用等級低,資金規模就小,比如幾十萬元或者更少,放貸范圍也有限。信譽等級提高了,你可以做更大的事。這是一個金融體系監管的細化問題。我們現在是粗放型管理,對監管部門而言,容易管理,但忽略了社會的需求,真正現代科學的管理應該是多層次的。”
許志永說,當初代理孫大午案,一是因為對孫大午這個人比較認可,“案發之前,我和他見過一面,感覺他是一個比較有思想的人”;此外,他還寄予了一些個人理想,“這個案子涉及金融體制改革以及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環境等問題,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案子對這些方面有所推動。”
當記者問及他對結果是否滿意時,許志永沉默了片刻,說:“孫大午案子結束后,河北省專門出臺了一個不追究企業家原罪的文件。因此,初衷還是實現了一部分。但金融體制改革,沒有明顯的進步。”
記者觀察
民企非法集資案緣何屢禁不止
近年來,民營企業涉嫌非法集資案屢禁不止。這其中當然不乏惡意欺詐之徒,但確實有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是迫于無奈,為了企業發展鋌而走險,通過向社會融資的方式來解決資金難題,不惜觸犯刑律。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不能簡單地從人性、道德層面去分析評判這類事件。而是更應該從制度層面找到問題的癥結和解決之道。
無論是孫大午,還是吳英,以及其他類似案件,盡管在情節上有輕重之別,但它們揭示了一個共同問題:民間金融的尷尬及其合法性問題。
從吳英所在的浙東地區來看,地下金融十分發達,從溫州炒房團到炒煤團,從搞實業到義烏的商鋪經營,背后都有民間借貸的影子在顯現。民間拆借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民營經濟的融資難問題。當然,在高額回報的背后,民間借貸也潛伏著巨大風險。
民營企業融資難早已不是一個新話題,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了。但問題一日不解決,就得一直談下去。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民營企業融資環境得不到明顯改善,此類案件將難以杜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