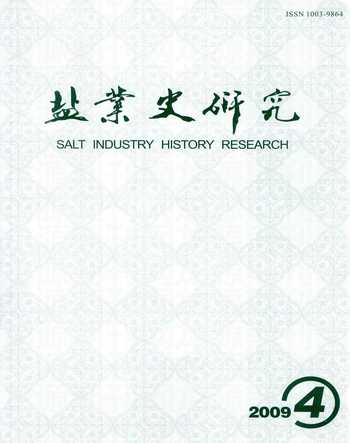朝向鹽文化的精神尋根
站在浩瀚的中華文化面前,對鹽文化進行研究時,張銀河先生具有一種獨到的洞見能力和精審的概括能力,他洞見到了中國文化中較為完整的“鹽文化史體系”,概括了這個體系可能包含和彰顯的諸多人類文化現象。不僅如此,還由于是站在對眾多資料了然于心和對有關鹽文化現象深思熟慮的平臺上,因此在對中國鹽文化史進行觀察研究的時候,他在不少地方穿透了以前一些研究盲點,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在現象與本質之間,發現了更廣闊的視野和更悠遠的風光,并給予正確客觀評價。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目光,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燦爛文化中洞見了鹽業文化的繁復奇異,并由此較為精確地勾勒出了中國鹽文化史的基本體系,這就形成了50萬字的新著《中國鹽文化史》,完成了在宏觀視域里,朝向鹽文化進行精神尋根的思想歷程,實現了他多年的研究夙愿。概括來說,這部著作有如下幾方面的特點:
一、史料性:文化厚重感與歷史縱深度的交融
無論從世界還是中國看,在人類文明的演進中,食鹽有著特殊的功績。總體上說,我國有關鹽的文字記載浩如瀚海,但大致而言,呈現兩極狀況,明朝以前的相對稀少短缺,明清以后較為繁多,僅就清鹽檔案來說,在國家的館閣中所藏的鹽務檔案可謂汗牛充棟,要想在有限的時間內把它們查閱一遍對一個人來說幾乎是不能做到的。這就給寫史者帶來了很大困難:前者要在遼遠悠長的歷史文化長河中尋蹤覓跡,擷取有關鹽的文字記載,后者則需要在浩如煙海的歷史記錄中翻檢爬梳,選擇有代表性的典型進行整理編串。這是一個既枯燥繁瑣又艱苦卓絕的巨大工程。不僅如此,對一些重要的問題的考察,僅憑文字記錄是遠遠不夠的,這是由所研究的對象的性質決定的。一般而論,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同時又是一種歷史現象;確切地說,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等。對如此蕪雜龐多的涵蓋,僅憑有限的文字記載是不能說明和證實的,特別是古代鹽文化在物態文化、制度文化和行為文化等方面的表現,至少就要用考古人類學的方法,用田野作業的手段來獲取和證明,這就是說,不僅要讀千卷書,還要行萬里路。我們沒有見到作者日復一日的風塵奔波和筆耕艱辛,但我們在書中卻看到了作者舉重若輕的體系建構和相得益彰的考據史料整合。這種史的縱深度與厚重感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對鹽文化源起性問題的研究上。在《中國鹽文化史》中,我們看到作者的精心考證。在宏觀方面,作者沿著人類發展的歷史順序找尋,從漁獵時期,到牧畜時期再到農耕時期,運用已有的考古成果,如羅振玉的《殷墟書契考釋》和黃河、長江流域在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以及這一時期的有關神話傳說等,對鹽的起源進行分析考證。在對黃河流域的考古史資料引述中,就涉及了周口店人、藍田人、丁村人、河套人、山頂洞人、南召人以及許昌人等考古成果,而這些地方都是自然鹽的分散地。作者詳細記載了晉南地區和膠州半島等地發現的古代鹽倉遺址和人類早期曬鹽煮鹽的器皿。在對長江流域的考古記述中,作者也詳盡地引述了可資引征的考古發現與鹽文化的關系,如巫山人、長陽人、元謀人等,具體的地名、時間、發現古鹽井的數量都一一列舉(見第39頁);而使用神話、傳記、史志等文字資料來厘清和佐證鹽文化的源起,更是嚴謹不茍,從《列子》、《山海經》到《呂氏春秋》至今人的研究新成就,無不包攬無遺。對人類使用自然鹽的問題上,作者指出曹學儉《蜀中名勝記》、康熙時期《黑鹽井志》等著作上均有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白鹿飲泉”、“牛舐地出鹽”、“群猴舔地”、“羝羊舐土”的記載。依據柏楊《中國人史綱》等研究成果,指證紀元前二十七世紀時,黃河中游跟汾水下游一帶,三個最為強大部落,即神農(炎帝)部落、九黎(蚩尤)部落、熊(黃帝)部落,征引《史記》記載和張其昀《中華五千年史》,認為:黃帝曾戰炎帝于現河南扶溝,敗蚩尤于涿鹿(現山西運城)“炎、黃血戰,實為食鹽而起”。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將中華鹽文化史的開端論述得清晰明確。
其次,對不同歷史時期的鹽的管理制度,鹽政人物以及該時期食鹽貿易、食鹽風俗習慣等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的論述上。這一部分的資料最為龐大蕪雜,但作者以時間為經,有條不紊地串珠連線,一一道來。在鹽的管理上,從血腥爭奪到自由兌換再到《管子》記載的官營政策,從《鹽鐵論》到明朝鹽業禁垣的修建,再到清朝、民國時期的各種鹽業政策,可以說,每一朝代的鹽業管理都可以在書中找到它的來龍去脈,尋查到它的成敗得失,進而體會到鹽文化對于國家每個朝代的重大作用和對市井小民悲歡生活的日常滲透。對于鹽業政策的制訂和實施,作者在敘述鹽政的同時引出歷朝歷代著名的鹽業管理人物,對這些人物在史志中的記載和民間傳說中的種種表現予以記敘評論,讓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僵化的死去的歷史,而是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參與活動的動態的歷史。在本書中,涉及的主要人物有三皇五帝,有朝野重臣,有富商巨賈,也有民間名人,林林總總不下百人之多。在風俗習慣的敘寫中,作者點面結合,重點介紹了夏商周時期的食鹽祭神、作貢、交易等習俗;漢魏六朝的食鹽腌制、作醬習俗等;唐宋時期的食鹽飼養、藥用以及用鹽鈔貿易等民間習俗和交易習慣。甚至,作者把視野從漢民族擴展到少數民族,從鹽文化拓展到中國的茶文化、酒文化,在歷史縱向的坐標里作跨民族、跨文化的比較影響研究。
再次,對鹽業科技文化史攬括上。這些主要表現在對池鹽、井鹽、海鹽的開發利用上。對自然形成的鹽的利用,有意識對鹽進行加工這是人類文明的重大表現,是人類聰明智慧在鹽文化中的具體體現。書中對這一歷程分別從池鹽、井鹽、海鹽等幾個方面予以展示,歷史地再現了這一科學技術的發明使用和創新發展,作者從李冰開井鹽,到墾畦澆曬技術的出現以及生產流程的介紹,再到粲海井的開鑿及使用天車、筧管輸鹵等科技文化的奇跡,從志書、神話、傳說,《天工開物》、《夢溪筆談》等科技典籍,以及漢代畫像磚《煮鹽圖》和元代《熬波圖》等史料予以詳實的說明和論證。
又次,關于近代和現當代時期的鹽業文化的著述、期刊學會的歸納梳理。《中國鹽文化史》作為一種史的體裁讓閱讀者一覽某一時期的重要著述,而省去研究時在大量資料耗時費勁之苦,是它的一大作用。《中國鹽文化史》在這方面做得特別精細。打開書的第487—491頁,我們就可以輕易地得到20、21世紀出版的主要鹽業著述以及這些著述的內容簡介,還有這一時期所有的有關鹽文化的研究的期刊、學會,從國家級到省級再到地級,中國鹽文化期刊、學會盡在其中,得一本而知天下鹽業,在這里并不是溢美之辭,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擁有。鹽文化文本形態的改變,也是這個時期的重大文化事件,從文字文本到鏡像文本,從固態保存到動態展現,為鹽文化的傳播
與研究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本書給我們提供了鹽文化的紀錄片,鹽文化博物館的存現狀況,讓我們對鹽文化的史料性了解掌握建立在更全面具體的信息平臺上。
此外,對史志、游記、文學、繪畫、雕刻等方面反映的鹽文化進行的細致爬梳也是本書史料性的重要體現,限于篇幅,這里就不再詳述。粗略統計,全書征引使用各種文字資料不下500多種,歷史畫像、地圖330多幅,涉及從上古時期出土文獻文物到現當代最新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上下五千年,縱橫二萬里,無愧為鹽文化研究中的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史書。
二、學術性:彌綸百家而后獨出新見
史的寫作忌諱史料的羅列,或者理論先行,以理論剪裁史實。我們看到《中國鹽文化史》成功地避免了這一寫史過程中易犯的毛病。在書中,作者大量引征史料,但并沒有給人以雍腫龐雜之感,因為它不光是簡單的梳理整合,更是在此基礎上指認這一文化現象現在的意義和作用,對于學術界爭論的東西,作者則是一一列出有代表性的意見,然后在論析史料的前提下,彌綸百家、明確地提出自己的觀點,發一己之獨見,出一家之言論,從而以史帶論,以論來整合約束史料的選擇運用。而且,這種論述往往是基于史實的文化意義論析得出,它完全不同于以往一些論著中以存在主義,純粹社會政治學等理論先入為主的觀照批評,因而在史與論結合時更合理更科學,從而更具有學理性。它不僅把讀者帶進了豐富的資料場里,也帶進了一個具較強學科意識和學術意義的思想競技場中。這種學術性特點貫穿全書,幾乎在每個小章節都充分體現著,我們僅舉幾例來說明。
其一,用考古學和詞源學方法來考查“鹽”字的源出與鹽文化的關涉。明人邱仲深根據《禹貢》的有關記載,斷言“鹽”字起源于夏朝。即“考鹽名,始于禹”。禹為夏朝時的帝王,從目前考古來看,我國在夏朝時尚無文字。根據現有的考古發現,我國最早的文字是殷商時期的甲骨文、金文。由于最早的“自然天生的鹽”不叫“鹽”,而稱“鹵”,真正稱為“鹽”的是“煮海為鹽”后人工制取的鹽。漢朝許慎《說文解字》對“鹽”字的解釋是:“鹽,鹵也,天生(即自然生成)曰鹵,人生(即人工制取)日鹽”。目前甲骨文上尚無“鹵”或“鹽”字發現,但在金文上卻有“鹵”字。金文出現于周代,按夏、商、周三代從周上溯至夏,夏朝時出現“鹵”字當有可能。基于這種認識,在第一章第九節和第二章第二節里,作者對“鹽”字的出現與對甲骨文、金文的考查結合起來。倉頡造字,不唯民間傳說至今,在《荀子》、《平陽府志·帝王》等書中都有記載,作者在這里很謹慎地記述了關于倉頡造“鹽”字兩個版本的傳說,但這仍不是信史,作者進而從出土的甲骨文和金銘文中指認“鹽”字來源。從郭沫若主編的《甲骨文全集》和羅振玉、李學勤等古文字學家的思想啟發下,通過對“鹵”字的分析和左樹珍在《中國鹽政史》中的有關論述,作者有據有理地指出“甲骨文中沒有被學者考證出‘盥字、‘鹽字,并不意味著當時沒有反應鹽的文字。”并令人信服地列出三條原因來加以論述(見第59頁)。作者在這里運用考古學、詞源學的方法,綜采多家之言,小心論證,最后得出自己的結論,為“鹽”在詞源學的意義上為鹽找尋著最早的文化地位。
其二,關于“鹽宗”問題。從事不同鹽角色的人群各有其自己認同的祖宗,從事鹽生產的人認同自己的祖宗為“夙沙氏”。從事鹽經營的人認同自己的祖宗為“膠鬲”。據《孟子·告子篇》和朱熹注:膠鬲是殷商末年人,原為商紂王的大夫,遭商紂之亂,隱遁經商,販賣魚鹽。而從事鹽管理的鹽官尊春秋齊桓公時代的管仲為鹽專賣鼻祖。宋朝時,有人認定“夙沙氏”一人(或一部落)為“鹽宗”,并在河東解州修建了鹽宗廟。清同治年間,有人在江蘇泰州建廟,主位鹽宗為夙沙氏,并同時也把膠鬲和管仲的塑像立在旁邊。后世把管仲稱為鹽宗,作者對此表達了不同的學術觀點。通過對管仲其人和《管子》的解讀,《中國鹽文化史》從專營方面指出,在管仲之前“專山澤之利”的記載就已經出現,這種政策在舜執政其間,在周厲王時期都已開始實施,只是到了管仲才從理論上予以論述;從最早開發食鹽方面看,貢獻最大應當是齊國開國先祖呂望,因而尊管仲為鹽宗之說不能成立。這一提法在學術意義上是一個比較新穎的觀點,是一種學術創見。這種理論創見還表現在對《鹽鐵論》的解讀上。作者對桓寬本人、鹽鐵會議舉行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鹽鐵會議本身審慎分析論證后,指出了《鹽鐵論》社會作用思想價值和審美價值,認為它盛傳于世的原因有:“其一,它得益于漢昭帝劉徹時期鹽鐵會議的記錄;其二,它得益于漢代深厚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其三,它得益于桓寬個人深厚的文化素養。”(第153頁)這種結論的意義,已經超越出鹽文化領域,對從社會政治角度和文學藝術角度理解《鹽鐵論》都不失有啟發意義。
三、文學性:對中國文學史的另一種解讀
張銀河先生不僅是一位鹽業文化研究者,作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而且也是一位對文學情有獨鐘的作家,這使得他的這本著作處處充溢著文學性的光彩。閱讀《中國鹽文化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在閱讀中國文學史,或者說是從鹽文化視角對中國文學史的另一種解讀和闡明。
文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精神文化的重要表現形態它與政治意識、宗教信仰、哲學等共同組成了精神文化中的金字塔。從文學體裁來看,本書涉及到文學的各種體裁,從上古時期的神話、傳說、詩歌、戲曲、辭賦、小說,到現代的影視文學都有較為詳細的反映。而小說從《穆天子傳》到魏晉小說到現當代的長篇小說,詩歌從上古時期虞舜的《南風》、南北朝民歌到唐詩、宋詞再到現當代的自由詩,而戲曲從漢代角抵戲到元明清傳奇,散文則從《尚書》到歷代辭賦到明朝的小品文,再到現代如林語堂等人的隨筆等也有較為完整的呈現。遠古神話和近代的民間傳說也使得幾乎和鹽文化相關的內容都包羅其中,千匯萬狀,洋洋大觀。不僅如此,古代的很多史志如《史記》、《后漢書》等,科技書如《天工開物》、《夢溪筆談》等,醫學書如《黃帝內經》、《本草綱目》等,地理書如《水經注》、《徐霞客游記》等,它們既是學術文本,也是文學文本,這些典籍中只要有與鹽有關的記述,本書也都一一涉獵,并以文學性的語言加以敘述論說。
從文學人物來說,我們看到從虞舜的《南風》詩以下,各個朝代的著名的散文家、詩人、詞人、小說家、戲曲家等大都包羅其中。荀子、管子、列子、屈原、賈誼、左思,唐宋以下的如李白、杜甫、柳宗元、歐陽修、范成大、鄭板橋、汪中,現代如郭沫若、田漢等,小說家如唐傳奇的多個作者,明清的馮夢龍、凌蒙初、施耐庵及才子佳人小說作家多人,意大利的馬可·波羅也赫然在列。此外,我們還看到金庸的《天龍八步》描繪了云南鹽業重鎮黑井的產鹽歷史盛況,林語堂的長篇小說《紅牡丹》也多次描寫鹽商生活,而專門以鹽場生活描寫鹽人
悲喜人生的小說如王余杞的《自流井》、羅淑的《井工》等在鹽文學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此,我們不能不提及與文學藝術并肩比美的其它藝術形式在本書中的表現,那就是繪畫藝術與石刻藝術以及棧道、八陣圖、鹽橋、鹽屋等造型藝術。《煮鹽圖》與《熬波圖》是本書重點介紹的兩幅圖畫,作者在分析這兩幅圖時不僅指證了它們對鹽生活過程的史料作用,也分析了這些圖畫所蘊含的藝術因素和審美價值,附在圖旁的詩文也更提升了它的藝術性。《河東鹽池圖》、張士誠起義《石刻記功碑》是兩幅圖文并茂的石刻,形象生動逼真,雕刻精美,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總之,在閱讀《中國鹽文化史》的時候,就是散步在中國文學藝術的長廊里,我們不僅又一次感受中國古代歷朝詩人們嘆息民生的細膩情懷,感慨《格薩王傳·保衛鹽海》優美的語言和動人的情節,還一次次與我們在文學史中所熟知的人物形象相遇,進一步了解到過去為我們所忽略掉的與鹽文化有關的細節,比如我們由此知道了伯樂所見的那匹千里馬原來是在拉鹽車的路上,《三國演義》中關羽原來是在山西販鹽的小商人,《杜十娘》中杜十娘所邂逅的孫富卻正是鹽商子弟等等。
四、普適性:恰好的敘述策略與話語方式
《中國鹽文化史》并非是只寫給鹽業內部人士閱讀的專業書籍,它同樣可以為所有閱讀者接受,這源于其內容對于接受群體的普適性,而這種普適性主要得益于它的敘述策略和話語方式,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恰當的敘事時序和敘事空間架構起來一個完美的文本體系結構。研究敘事學的荷蘭學者米克·巴爾說過:“敘事是一種文化理解方式;到處都是敘事,并非一切‘是敘事,而是在實踐上,文化中的一切相對于它具有敘事的層面,或者至少可以作為敘事被感知與闡釋。除了文學中敘事種類的明顯優勢而外,我們隨便就可以想到敘事可能會‘出現的許多地方,它包括諸如訴訟、視覺形象、哲學探討、電視、辯論、教學、歷史寫作等。”作者依照一般史書寫作的方式,以時間為經線,自上而下,自古而今,這種敘事時序符合一般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接受能力,這是一部具有普泛性文化史書寫作的常規要求,作者在這一方面沒有標新立異,從傳說時代開始到當代為敘述終點,以朝代為界限,娓娓道來,為本書突破專業限閾,成為一本普泛型文化普及書爭取了更多的接受者,這也是作者研究鹽文化史的初衷:不僅要成為專業人士研究的學術性著作,更要成為一般百姓樂于閱讀的科普書。但這種平常的敘事時序并沒有導致書的架構的平庸,我們看到,敘事空間的巧妙運用使本書建構成為一個既內容豐富多彩又體系完整的文本。在每個時序的敘事中,作者把神話傳說、文學藝術、制度政策、人物傳記、史志典籍、科學技術、風俗民情等都包容進去,在每一個朝代的鹽文化敘事中,都讓人走進一個多姿多彩、豐贍繁富的鹽文化博物館,物、情、事、理、天、地、人、神,紛至而來,應接不暇,使人恍然行走在中國古文化的大花園中,有觀賞之歡愉,無行走之辛苦。
第二,概括性敘述與具體性分析結合。在悠長的敘事時序和繁多的敘事時空中,作者沒有有意拉長拉寬閱讀視域,而是點面結合,繁簡適度,把概括性敘述與具體展開巧妙地結合起來,該長則長,應短則短,而所有設置既是在史論展現和分析的就欠的范圍之內,又在接受閱讀的限域之間,使我們在翻閱本書的時候沒有負累的感覺,相信讀者在打開本書的時候是可以感覺得到的。
第三,以“文”入史和史論結合。這里所說的“文”有兩層意思,一是文學藝術,二是文采文筆。對于前者,我們已經在前邊論述過了,就是作者以藝術的手法進行史的敘述,有的章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以鹽文化的角度對中國文學藝術的詮釋,從而使鹽文化史充溢著詩性。一般而言,史的寫作態度應當是冷靜客觀的,是零度寫作的態度,但史的寫作也并不完全杜絕情感的介入。作者在論及中華燦爛的鹽文化時,仰慕自豪之情油然而生,這些突出地體現在他的富有情感意味的文筆之中,在盎然的詩情詩意的流轉中達到情感渲染的文化敘事目的。史論結合的敘述策略我們在前面也有所談及,這種方法手段的運用,使得史中有論,在史料中提煉觀點,以史料支撐理論,使史與論結合完美,相德益彰。
話語方式是敘述策略得以完全實現的語言手段。在本書中言說方式的主要特點是文學性、情感性、簡明通曉性以及圖畫符號參與言說等。而其中話語的通曉性是其最主要的言說方式,這使得本書避免了可能出現的詰屈拗口的閱讀障礙,從而實現了史書在閱讀接受過程中的普適性效果。由于本書征引了大量的古文史料,所以如何避免由語言帶來的接受障礙是對著述者書寫能力的考驗。我們看到,在書中無論引用哪些文言史料,作者都不厭其煩地用現代漢語予以解釋,這種解釋不是簡單地從古文翻譯,而是用作者自己的特有的話語方式通過自己的理解加以闡明,在這里,作者用自己平白質樸的言語方式,越過了古文帶來的眾多的語言礁石,也行之有效地繞過了過多地使用“學術黑話”可能帶來的理解困難,因而,我們在這部書中瀏覽時,沒有翻山越嶺的勞累,卻如乘小舟泛清流的輕松與愜意,這是我們大家都能夠輕易感受到的。同時,為了使交流溝通更具直觀性和平易感,作者精心選取了大量的圖畫(包括地圖)等參與鹽文化史的敘述,這種對話方式,使相對抽象的文字符號與直觀可感的圖畫符號相互補充,相互指認,加強了接受者的理解能力,加深了對鹽文化史的印象。這樣使得全書在整體感覺上質樸通俗,平易近人,趣味盎然。
但這并不是說這本書是白璧無瑕的完美之制了,相反,書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是明顯的。由于著者追求史的完備性,因而有些重要的反映鹽文化的著述沒有能夠充分展開,如對《齊民要術》的論述即是這樣;可能由于資料的限制,或作者取舍的原因,一些文學中所表現的鹽文化情節如《南北史演義》(第十一回)中關于鹽池記載,孔尚任的詩歌《自鹽城》以及趙樹理小說《靈泉洞》等沒有能進入作者視野;在延安時期,共產黨人利用食鹽貿易渡過經濟封鎖的艱難階段,這也許算是鹽文化中的“紅色文化”部分,但卻沒有被論及。再者,為了追求普適性和趣味性的接受效果,部分章節的學術性做出了一些必要和不必要的妥協,從而使理論深度有所弱化,為著同樣的目的,極少數的插圖并沒有與該章節所論述的問題有直接的關聯性,也是一種細節上的遺憾。
當然,這種要求對本書來說也許過于苛刻了,因為,以一己之力在二三年業余時間里撰寫這樣一部鴻篇巨制,無論從哪個方面講都如二月河先生在序中所言“實屬不易”。它填補中國鹽文化史研究空白的學術意義是非常顯在的,以這樣的文本形式和言說方式來有效地傳播古老的鹽文化的社會價值也是相當重大的,我們期待著再版時會更加完美。
作者簡介:石長平(1968-),男,文學博士,許昌學院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文化和文學理論研究。
(責任編校周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