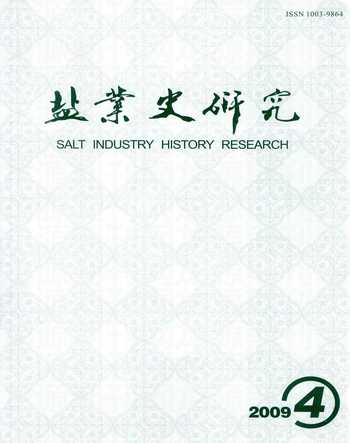對明代戰爭引起淮鹽困守支問題的初探
【摘要】:明朝開中鹽法的實施,是因軍隊對糧食的需求而引起。無休止的戰爭,導致無節制的開中,從而使淮鹽的開中數量遠超過其生產能力和社會消化能力,嚴重的“困守支”問題由此而產生。該問題的產生與演變,又從另一個側面推動明朝兩淮鹽政變革朝更深的層次發展,最終使朝廷由經營者演變為管理者。本文只是對戰爭引起“困守支”問題做一個初步的探討,并希望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關鍵詞】:明朝;戰爭;淮鹽經營;困守支;鹽政變革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864(2009)04-0034-10
明代的鹽政變革有兩大特點。一方面,它是將鹽的國家專賣制,逐步演變為國家壟斷下的商人經營,從而使朝廷由經營者轉變為管理者,并通過這種管理獲取專制性稅收;另一方面,則是將鹽貨作為與商人交換糧食的商品,以滿足軍隊對糧食的需求,從而有開中鹽法的實施。據史料記載,當商人按照規定,將糧食送到指定的官倉以后,他們并不能即刻得到鹽貨,而是要在鹽產地作無休止的等候,史料便將這種情況稱之為“困守支”。其中,因淮鹽既是全國第一大鹽種,又是商人最愿意經營的鹽種,因此有明一代,屬淮鹽的“困守支”最為嚴重。筆者曾經設想,既然開中鹽法的實施是為了滿足軍隊對糧食的需求,那么“困守支”是否就是因為戰爭而引起?最近,筆者就此問題做了一個初步的探討,現將有關心得表述如下,以供學界批評及參考。
一、明前葉的情況
有人批評朱元璋“重農抑商”。但朱元璋在鹽業經營問題上,從未主張過國家專賣制。這是因為,國家專賣制雖在獲利問題上能讓國家獨享其利,但大鍋飯的弊病又使國家“得利微而為害博”,只有實行私人經營,才有可能在相同的鹽價(即百姓所承受的壓力)條件下,使國家獲得更多的利益。因此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前,便在他所控制的區域內,鼓勵商人經營鹽貨,以便從中獲取稅收,“以資軍餉”。
明朝的建立,并不意味著戰爭的結束。當朱元璋于洪武元年登基的時候,他的軍隊只控制了長江中下游乃至東南一帶的地區,北伐軍也只打到山東境內。此后,他指揮軍隊繼續打河南。攻大都,并在這年的八月攻下大都,改大都為北平(即今北京),以應天為南京(即今南京)。并在洪武四年打下四川,十四年進入云南,二十年攻取遼東。到這時,朱元璋才基本完成統一國家的大業。
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當洪武三年六月,山西行省提出以淮鹽與商人交換糧食時,以“高筑墻,廣積糧”為基本國策的朱元璋便自然同意。這條重要史料的原文是: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若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俱準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從之。
同樣是在洪武三年六月,明朝軍隊打到應昌(在今內蒙古達里淖爾以南),迫使元朝殘余勢力退縮到大漠以北。并且,這時元至正皇帝已經去世。于是,朱元璋便開始實行緩和的政策。尤其可貴的是,他不否定前朝統治的合法性,不侮辱前朝統治者的人格,不過分吹噓自己的勝利,不虐待被俘前朝統治者的親屬及后代,這些都是我們在重溫這段歷史時,應當從中吸取教益的。例如,當時需要發布一道文書,以張榜天下,告知百姓,稱元朝統治者已被徹底打垮。當朱元璋發現文稿中有一些“侈大之詞”時,曾批評中書省的丞相們說:
卿等為宰相,當法古昔,致君于圣賢,何乃習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況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于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為是也,可即改之。
又如,當時有人建議將被俘的元順帝之孫買的里八剌等人,以古代“獻俘”的陋習予以處死,并以此慶賀勝利,朱元璋則不予同意。他說:
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復。
此外,對散落在長城以南各地的元朝殘余軍政人員,朱元璋則采取招降優待的政策。他曾于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發布通告,一方面尋找元順帝的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希望他歸順明朝統治,到南京撫慰自己的妻子及眷屬;另一方面對那些散落在各地的元朝殘余軍政人員,只要能夠歸順,則一律不分等級,量才委用。
這些政策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有不少人采取了歸順的行動。但是,緩和政策代替不了戰爭,明朝北部邊境的局勢依然很嚴峻。為此,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派遣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前往北平“操練軍馬,繕治城池”,命濟南衛指揮僉事盛熙領兵2000人,濟寧左衛指揮房寬厲達領兵5000人,青州衛指揮僉事周興領兵4000人,萊州衛指揮同知胡泉領兵3000人,徐州衛指揮僉事司整李彬領兵2000人,“悉聽節制”。
朝廷在洪武四年二月,又接到大同衛都指揮使耿忠的報告,稱“大同地邊沙漠,……(元朝殘余勢力)亂兵殺掠,城郭空虛,土地荒殘,累年租稅不入,軍士糧餉欲于山東轉運,則道里險遠,民力艱難,請以太原、北平、保安等處稅糧,撥赴大同輸納為便。”因此,朝廷經過商議,決定“于山東所積糧儲,量撥一十萬石,運至平定州(今山西平定縣,在陽泉市區附近)”,再由“山西行省轉至大和嶺(即太和嶺),大同接運至本府及以附近;太原、保定諸州縣稅糧,撥付大同,以為儲之備”。
由此不難想象,洪武年間的北方邊境一直處在不斷的武裝沖突狀態。朝廷為了解決守邊戰士的糧餉問題,便實行過度的開中,即每年的淮鹽開中數量,都遠遠超過其生產能力和社會的消化程度,導致商人在獲得開中倉鈔之后,要在揚州作長時期的守候。
朱元璋去世以后,在明朝的戰爭史上又增添了一項新的內容,那便是所謂的“靖難之變”。這場發生于建文皇帝和燕王朱棣之間的骨肉自相殘殺,長達四年之久,地點則是從北平一直打到南京。勝利者朱棣雖于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登上寶座,是為永樂皇帝,但這時軍隊的糧食供應則顯得更加的緊張。
山東是這次戰爭的主戰場,百姓遭受損失很大,故在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初一日,皇帝敕命歷城侯盛庸,“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鎮守淮安。今山東布政使鐵鉉(原建文朝臣)亦已就獲,諸郡悉平,是皆宗社之靈,生民之福。朕念山東軍民困于兵革,轉輸已久。卿其息兵養民,使各得其所,糧餉續有處分”。其意思很清楚,便是要求盛庸繼續向朝廷提供糧食。
這時北平的糧餉供應十分緊張,永樂皇帝曾命戶部將全國各地的開中一律停止,以專門保證北平。這次開中,還把北平的開中則例,降到淮浙鹽每引米3斗、河東鹽2斗、四川鹽1斗5升的程度,甚至還提出,“聽大小官員、軍民人等
皆中,不拘次支給”。。這便違背了洪武年間制定的祖訓,即“凡公侯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家人奴仆行商中鹽,侵奪民利”,可見當時的軍餉供應緊張到什么程度。
同樣還是因為北平的軍餉供應緊張,永樂皇帝甚至允許犯人以向官府納米的形式贖罪,減少服刑的時間。即“上初以北平軍餉不繼,欲出獄囚輸米贖罪以給之,且省饋運之勞,命法司議。至是法司議奏,除十惡人命強盜及笞罪不贖外”,其他犯人則可按不同的檔次輸米贖罪。并且規定,只要把米輸到官倉,即可放人。
但即使采取這些措施,仍難以解決北平的糧餉供應問題,故戶部尚書夏原吉只好在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的十二月,再次向皇帝提出降低開中則例,因而有歷史上那條著名的“永樂時納米二斗五升”的則例出臺。其原文是:
戶部尚書夏原吉等言:比者河南、山東等處米價翔踴,北平鹽糧價重,商民少中。宜以原定淮浙鹽糧量減五升,每引止令納米二斗五升,其河南并川鹽仍如前議。從之。
明朝米1石約重139.43斤,即當時2斗5升米的重量為34,86斤(也即139,43×0,25)。這便意味著,在明朝永樂初年,商人僅用34,86斤米,便可在北平換到一張價值200斤淮鹽(或者浙鹽)的倉鈔。只是商人得到這份倉鈔,要積壓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才有可能從官倉領出鹽貨,然后到指定的地點去銷售。故我們在做成本核算時,應考慮這倉鈔積壓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的利息是多少,然后才有可能考慮商人是否有利可圖。
元朝被推翻以后,其殘余勢力退回到蒙古草原。蒙古社會也在明朝初年被分成韃靼、瓦刺和兀良哈三大部。這三大部之間,雖有實力的消長與沖突,但他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對明朝北方邊境構成威脅。僅在永樂年間,便有皇帝的五次親征。永樂皇帝本人,即死在第五次親征的歸途上。甚至在正統十四年(1449)還發生過著名的“土木之變”,蒙古軍隊一直打到北平的城下。
無休止的戰爭,導致無節制的開中,使商人的“困守支”問題嚴重到驚人的程度。朝廷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曾提出用日益貶值的資本鈔,兌換商人手里的倉鈔。如明宣德三年(1428),戶部尚書郭敦言:
洪武中[姑以洪武三十年(1397)計],中鹽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虛冒。請按引給鈔十錠。……至正統五年(1440),商人有自永樂中候-支鹽[姑以永樂二十年(1422)計],祖孫相代而不得者,乃令每引給資本鈔三十錠。
由上述史料可知,當時的“困守支”時間已經達到約20—30年的程度。這將嚴重挫傷商人參與開中的積極性,使鹽法難以維繼。朝廷為了調動商人的積極性,只好降低開中則例。此外,朝廷在洪武年間也曾出臺過一項“不拘資次支給”的政策。其含義是,對于已經造成積壓的倉鈔,仍按原來的秩序守支下去,但當邊地出現新的開中需求時,中納者可不挨在原有秩序的后面守支。如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尚書趙勉言,“舊例,納粟涼州,支淮浙鹽,則每引米四斗,河東鹽每引米五斗,不拘資次支給。今議輸粟甘肅,宜比涼州量減,淮浙鹽入粟三斗,河東鹽人粟四斗,仍不拘資次支給”。由此看來,這項政策的出臺年份,當在洪武二十三年以前。
但這項政策并未持續很久。這是因為,“不拘資次支給”政策的出臺,必將進一步打擊原有守支商人的積極性,而且時間一久,又勢必在“不拘資次支給”的商人當中出現另一種形式的“困守支”現象。因此到正統初年,朝廷又出臺了一項新的政策,即“常股”、“存積”鹽的劃分。
據記載,是“(正統)五年定淮浙長蘆每歲存積、常股分數。每歲額辦鹽課,以十分為率。八分年終挨次給與守支客商,謂之‘常股;二分另積在官,候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積見鹽。人到即支,謂之‘存積”。
后來,因新的開中需求難以滿足,曾不斷增加“存積鹽”的比例。“至(正統)十四年,淮浙存積鹽增至四分。景泰元年增至六分”。。甚至還將“常股鹽”也用于新的開中,并適當降低“常股鹽”的開中則例,以吸引商人。《明史》稱,“凡中常股者價輕,中存積者價重。然人甚苦守支,爭趨存積,而常股壅矣”。。該情況進一步演變,將導致成化年間鹽商職能的分化,以及允許商人以納銀代替納糧。這些都是因戰爭導致對糧餉需求的增加所引起的。
二、明中葉的情況
在兩淮鹽業經營中,鹽商職能的劃分是一項重大的變革。據史料記載,該變革發生于成化十九年。當時因“困守支”現象很嚴重,“淮浙鹽不能給,乃配支長蘆、山東以給之。一人兼支數處,道遠不及親赴,輒貿引于近地富人,自是有邊商、內商之分。于各邊中引者,謂之邊商;于內地守支者,謂之內商”。為此,筆者曾針對當時的戰爭隋況進行過探討。
當成化十九年來臨的時候,人們還看不出有戰爭的跡象。但到這年的六月,情況便發生了變化。十九日,朝廷接到大同總兵官都督同知許寧的奏報,稱他們抓到了長城以外游牧民族的俘虜,并據俘虜供稱,他們的首領小王子,正帶領眾多的人馬往邊境上涌來;后來經過秘密偵察,確實發現俘虜所來方向的路上,以及大同的東、中、西三路,均有對方人馬前來進犯的跡象。許寧表示,他們擔心防守的兵力不夠,因此“乞調延綏官軍五千,協同戰守”。
兵部尚書張鵬向皇帝建議,一方面朝大同方向調兵遣將,同時又派要員分頭去各邊防重鎮,以視察那里的兵備情況,使各處都有迎戰的準備。但總體看來,朝廷的態度還是比較冷靜的。即使到了七月十七日,當再次接到許寧的奏報時,皇帝仍告訴兵部的官員們說:
向者邊報屢至,虜情叵測,已令京營總兵,整兵以俟。今報甚急,當刻期發兵,然須慎重。古人有云,“臨事而懼”。此行師之法,未可輕易也。其仍遣人,會寧等覘視緩急,以為進止,庶兵不徒行,糧不妄費。
這時,大同方面已經發生了戰斗。北面游牧民族的首領小王子,于七月十一日率領三萬多人馬,大肆侵犯明朝的邊境。他們東西連營,競有五十余里的寬度。明朝守衛軍隊卻只有一萬多人。從大同兩側宣府、延綏派來的援兵,則尚未趕到。于是只好分兵把守,并經過兩天一夜的奮戰,終于把敵人趕出境外。明朝方面生俘敵方1人,斬首17人,繳獲馬54匹、衣甲弓箭等物品970余件,關鍵是奪回牲畜16600多頭,但也陣亡586人,受傷1101人,被射死馬1070匹。
以上所述,只是成化十九年六、七月份若干次邊境沖突中的一次。后來,朝廷曾針對這次戰斗中的指揮不當,導致傷亡過大一事進行過總結,并優恤犧牲人員的家屬,以及命令總兵官都督同知許寧等人“戴罪殺賊”。
我國古代在設置城池時,往往會在容易受敵的一面,于城門之外再構筑一道半月形的城墻,并留有一座城門。在兩道城墻之間所圍成的那片封閉的區域,被稱為“甕城”。戰斗中,當敵人闖入這片甕城時,守城者可將內外兩座城門同時
關閉,敵人便只能在這個甕城里面被城頭上放出的亂箭射死。
筆者在探討中發現,明朝北方似乎也有這樣的一個“甕城”。其位置是從山西行省的東北角,直到北直隸(今河北省)的西北角那一片相連著的土地。甕城的“外城墻”,是處在大同鎮以北的陽和衛,以及北直隸宣府鎮以北的萬全右衛一線的長城(也即相當于今山西省與內蒙古自治區的交界線);其“內城墻”,則是處在雁門關、平型關、倒馬關、紫金關,一直到居庸關一線的長城。即使在現代地圖上,我們仍能辨出,從山西省右玉、左云、大同、陽高、天鎮各縣往南,直至朔州、山陰、應縣、渾源、靈丘等縣市,都是處在這片“甕城”之內。明朝廷在這里設置這個“甕城”,并在這里屯兵積糧,正是它“高筑墻,廣積糧”基本策略的體現。而且,也正是這個基本的策略,導致明代的開中鹽法最先是在山西實施。
依據《明憲宗實錄》對成化十九年八月的戰事記載,我們可以了解到,這個月大同一線的邊境沖突幾乎沒有斷過。并且令人吃驚的是,當時的廝殺并不是發生在外城墻一帶,而是敵方人馬越過這道城墻,甚至再越過第二道城墻,深入到內地進行搶掠。他們來人之多,搶去的牲畜數量之巨,尤其進出長城如履平地,這些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都是十分吃驚的。
例如,據提督雁門等關參將支玉奏報:“(八月)初五日,虜賊擁眾,散人大同、應、朔等州縣剽掠,逼近本關,烽火照映川谷。臣于次日,引兵二千至關南,遇虜五六百騎,攻圍本關北口,即督兵擊之。虜稍卻,復聚千余騎,循關口而東,漫山南行,突入內地。乃督守備指揮陳隆等官軍五百,據口邀擊。……眾軍爭奮,虜遂奔北。我軍直追至馬邑,近虜大營而返,且請速催京兵策應。”。
從這份奏章來看,當時敵人不但已經進入到“甕城”內,而且還在馬邑縣境內安置大營(今天馬邑縣已不存在,它的具體位置是在今朔州市與山陰縣之間,即雁門關的西北面)。他們甚至還曾突破第二道長城,進入到內地搶掠。基于雁門關等處的緊急情況,朝廷曾馬上命令都督馮升充當游擊將軍,率官軍3000,第二天即刻啟程,向雁門關進發,不許延緩;又命令左軍都督僉事王義充當左參將,中軍署都督僉事楊玉充當右參將,練兵聽候調遣。
俗稱“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一旦發生戰爭,糧草問題便顯得格外地緊張起來。
八月初九日,監察御史徐鏞等人奏報:“軍旅之興,糧芻為重。近年各邊倉庫,費出無經,不足于用。戶部職在度支,當任其責。頃者言及,出師輒云無糧。聽征之馬,不為支草,則無備矣。請敕戶部悉心規畫。”
該奏章下到戶部,戶部官員則訴起苦來。尚書余子俊等人復奏稱:
各邊糧草無積,誠如鏞等所言。然洪武、永樂時,以天下歲征,給各邊軍馬歲用之外,尚有余積。自正統末年以來,京城及各邊,添調軍馬數多,無事之時,俱加給以草。而各處田地,又因造冊多有詭寄,故賦稅日減,供費日虧。且水旱蟲災,歲固常有賑濟之糧,例在還官,今皆罷為赦免。且國朝鈔法、錢法、鹽法,乃祖宗生財之源;胡椒、蘇木,俱官吏俸糧之助,今皆沮廢無積。由此觀之,蓋不特邊方無積,而內地亦然;不特今日可憂,而將來尤甚也。
針對這份奏章,當時并未議出能夠解決問題的辦法,而只是從官員到皇帝,大家都在講一些大道理罷了。可見當時的糧草儲備,已經到了捉襟見肘的程度。
成化十九年夏秋之際發生于大同一線的邊界沖突,是在八月達到高潮,并在冬季來臨時自然平息。據鎮朔大將軍、保國公朱永奏報,到九月中旬時,入侵者的首領已經遠遁,邊境上沒有警報了。至于朝廷后來如何總結這次沖突,其中包括如何表彰或處分有關的人員,以及如何加強城堡的建設等問題,則都不去管它。本文所要關心的是戰爭如何引起糧餉的緊缺,以及由此而導致鹽政變革的深化。
明朝的戶籍管理是實行專業化,軍隊中的軍士實行世襲制:凡是向軍隊提供軍士的家庭,被稱為軍戶;士兵的口糧,則有明確的規定。
就大同守邊軍士而言,自洪武、永樂年間以來,一直是執行“月糧”與“行糧”同時支給的政策。所謂“月糧”,是指對在冊的軍士,每月都發給基本的口糧。其標準是,不帶家口者,每人每月米6斗;帶家口者,再加米2斗,共計米8斗。所謂“行糧”,則是指軍士因公出差,可在月糧之外,再按日程領到另一份口糧。。
正統皇帝登基以后,因糧餉供應困難,曾打算降低軍士的口糧標準,卻遭到反對。如宣德十年九月二十四日,這時正統皇帝已經登基,行在兵科給事中朱純便在奏章中指出:
沿邊夜不收及守墩軍士,無分寒暑,晝夜了望,比之守備勤勞特甚。其中貧難居多,妻子無從仰給,乞量加糧賞,以恤其私。
正統元年九月,當時的戶部也曾經下文,試圖把士兵的行糧待遇取消,結果也遭到大同總兵官都督同知方政的反對。后經復議,還是把這項待遇保留了下來。
現在邊境發生戰斗,軍士們出勤打仗,便使“行糧”的支出數量大為增加。而且當地駐軍(即被稱為“主兵”)的數量是有限的,一旦發生戰爭,自身力量不夠,便要從外面調進不少“客兵”來支援,這也無疑要增加對糧餉的需求。
成化十九年十月初七日,當時剛在大同一線結束戰斗不久,戶部在討論大同糧餉問題時,便出臺了永樂初年曾經出臺過的一項政策,即令山西、北直隸各府的罪犯們,除真犯死罪,以及官吏受財枉法,惡貫滿盈者外,都可以按照不同的標準,納米贖罪。甚至不要求他們繳納米豆實物,而是折納銀兩即可。
在這次討論中,還出臺兩項與開中鹽法有關的新政策。一項是,為了把糧食盡快地運到大同,便招攬商人運米中鹽。其含義是,米是國家的,地點在北通州糧倉,商人在一個月內,每運米l石到大同,便可獲得淮鹽2引,并且是成化十七、十八年生產的存積鹽。另一項便是,進一步降低淮浙鹽在大同的開中則例,且不許勒索商人的財物,使鹽法遭受破壞。
明代1石米約重139,43斤(見本文上節)。由上述規定可知,若商人能在一個月內將國家的1石米從通州運到大同,則國家將給他淮鹽2引(共計400斤)。這便出現一個問題,既然米是國家的,朝廷為何不派自己的人去運輸,而要花大的代價請商人來運?合理的解釋只能是,當時在運輸條件上肯定存在著極大的風險和艱辛。
我們先不考慮其他問題,只考慮一位壯勞力用一個月時間,把1石米從通州運到大同,再從大同返回,估計總共需要一個半月的時間。其伙食量,應以每天1升米計算。。這樣,其往返一趟的耗米量,算得緊一點是0,45石,算得松一點則是0,5石。若再考慮途中有個閃失(如被強盜搶奪,或者翻船沉沒等),其賠本事小,關鍵是誤了朝廷規定的期限一個月,這時商人又該當何罪呢?
或許正是這些困難,促使開中鹽法在成化年間又出現一種新的變革,即盡管朝廷把則例降得很低,但仍無商人積極的響應,朝廷便只好同意改“以糧中鹽”為“以銀中鹽”。后來,隨著時
間的推移,甚至連在開中地點繳納銀兩,商人也漸漸地不愿意去。故朝廷又只好同意,將鹽貨在鹽產地發賣(如淮鹽的發賣地點便是在揚州),以便把所得的銀兩,再送到需要開中的邊關去,讓他們自己購買糧食。
只是需要說明,上面所稱“以銀中鹽”及“在鹽產地賣鹽”,在整個成化年間,都只是以個案的形式出現。即當時是各開中地點按照自己的情況,向朝廷提出要求,經同意后執行,朝廷尚未就此作出統一的規定。直至弘治五年,才由葉淇奏請皇帝同意,對此作出一項統一的規定。即商人只需在鹽產地運司繳納銀兩,便可得到鹽貨。然后,朝廷再把所得銀兩,收歸戶部太倉管理,以分給各邊。對此,史稱“葉淇變法”,并最初是在淮鹽經營中實施。
葉淇,字本清,淮安府山陽縣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長期在地方工作,并在成化年間累官至大同巡撫。弘治皇帝登基后,被召為戶部侍郎,并于弘治四年升為戶部尚書,不久又加太子少保。
筆者在《明孝宗實錄》中,并未找到關于葉淇變法的記載,更未見到批評變法的文字。由此可見,變法在當時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它只是將成化年間一件未加統一的事情統一而已。倒是可能在正德初年,因劉瑾廢除年例銀兩,導致邊關糧餉緊缺以后,才被人們逐漸議論,并被稱為變法的。
據陳洪謨記載:“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為先朝無此例,令戶部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顧尚書佐以天順年前無銀例回報。瑾大怒日:‘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甚缺。”。
由這段史料能夠看出,“葉淇變法”是發生在弘治五年(1492),向邊關發放“年例銀兩”的事情,也只能是發生在此以后,劉瑾卻要求查找天順朝(1465以前)的先例,這豈不是拿人開心?再加上當時的戶部尚書顧佐,不敢把真實情況披露出來,反而讓劉瑾大怒。
弘治九年三月,葉淇奉旨擔任殿試讀卷官,因跪著讀卷時間過久,曾昏倒在皇帝面前,有失體統。尤其當皇帝令太監詢問情況時,葉淇競忘記向皇帝引咎致歉,這更使皇帝不悅,并導致科道官員的彈劾。這年四月,葉淇以老疾為由,向皇帝請求退休。皇帝同意其請求,并關照用驛站車馬送其返回故里。弘治十四年,葉淇逝世,皇帝賜葬,贈太子太保。
《明孝宗實錄》在記載葉淇逝世時,寫有最后一段文字,稱“淇亮直有操執,歷官皆有能聲。其在戶部,尤能惜財用;每廷議用兵,輒持不可,蓋患轉輸之費也”。這是因為,葉淇曾在山西任職,知道那里的糧草運輸是多么的困難。當然,這段文字在稱贊他的能力與作風時,也批評他有些偏執。即“士論多其能執,而亦病其偏云”。。但愿這就是歷史上一個真實的葉淇,讓我們記住他。
三、明后葉的情況及結語
清咸豐元年(1851),洪秀全在廣西發動金田起義的消息傳至京城,朝野為之震動。當時曾國藩已在禮部任侍郎一職,署兵部,他在給皇帝的一份充滿激情的奏折中寫道:“自古開國之初,兵少而國強。其后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以陳述當時“國用不足,兵伍不精”的狀況。其實,這種狀況在明朝時也同樣存在。
即以京師團營官軍而言,早在成化三年時,便開始設置團營。當時是因京師衛戌官軍不足,便以河南等四個都司,以及南北直隸衛所的官軍,共計99463人,分為春秋兩班,輪番赴京訓練。
最初,那些帶兵的將領都各得其所,能與士兵同甘苦。上班者,無其他勞役來打擾;休息者,有家室之歡樂,很少有士兵逃跑的現象。但年份一久,人心便漸漸懈怠起來。管理不善,使士兵上班不久便“饑寒迫身逃亡”。繼任的將領畏罪,便想辦法“規避他圖”。到成化十九年八月,缺額已達15000多人,馬也死去16000多匹。當大同、宣府等邊關請調兵馬時,也只從中選出22000多人,其余則都是“勇怯相半脫”。
正是這種狀況導致明朝國防力量的虛弱。如當成化十九年邊境沖突發生時,雁門關的軍馬只有八百多匹,步軍也不到二百來人。因此,許多長城地段也就形同于虛設。
胡松,字汝茂,南直隸滁州人,嘉靖八年進士,做過知州,后到山西擔任提學副使。嘉靖三十年秋天,他曾就那里的邊防情況上疏朝廷,共提出十二個方面的問題。其中說到,在這年的六月,他曾見過被捕的境外游牧民族派來的間諜。據間諜交待,他們曾在上一年的秋天越過長城,掠奪興、嵐等縣(即今山西省興縣和嵐縣),并在獲得不少好處之后,今年春天以來,又在串聯各個部落,調集人馬,以準備再度南侵。
胡松說:“今山西郡縣詳得虜所遣諜,前后不下數十人。……散在京畿與山東、河北者,各不下千余。”胡松還在這份奏疏中報告了當地防務松弛、官員懈怠,甚至私通敵方的情況,從而得罪了不少人。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于南方。如嘉靖年間的倭患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當時,倭寇不但屢屢登陸上岸,而且深入到內地搶掠。嘉靖三十二年,浙東、浙西,江南、江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當年四月,倭寇犯太倉,破上海縣,掠江陰,攻乍浦;八月劫金山衛,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又自太倉掠蘇州,攻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二州。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復薄蘇州。六月由吳江掠嘉興,還屯柘林。他們縱橫來往,若入無人之境。
滑稽的是,在嘉靖三十四年的入侵中,有72名入侵者從浙江經徽州、蕪湖、南京等地肆虐一圈,竟不傷一人而去。后來,周暉引述了這一事情,他稱: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倭賊從浙江嚴衢過饒州,歷徽州、寧國、太平而至南京,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與之相對兩陣,殺二把總指揮,軍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門緊閉,傾城百姓皆點上城,堂上諸老與各司屬分守各門,雖賊退,不敢解嚴。夫京城守備,不可謂不密。平日諸勛貴,騎從呵擁,交馳于道。軍卒月請糧八萬,正為有事備耳。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門,即張皇如此,寧不大為朝廷辱耶?
周暉還稱:
倭賊既殺敗官兵,即日宿于板橋一農家,七十二人皆酣飲沉睡。此時若有探細人偵知其實,當夜遣一知事將官,潛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殺都盡,但諸公皆不知。兵聞賊至,則盛怒而出;一有敗衄,則退然沮喪,遁跡匿形,唯恐不密。殊不知一勝一負,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敗為功者,此正用計之時也。而乃甘于自喪,何耶?且又不用細作,全無間諜。遇著便殺,殺敗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到隆慶、萬歷年間,朝廷對北方游牧民族盡量地采取“款貢”政策,即允許對方進貢一些物資,朝廷再給予賞賜,并允許貿易往來。
萬歷十八年秋天,曾在西北的臨洮、鞏昌(即現在甘肅省的臨洮、隴西)一帶,發生過軍事沖突,朝廷也曾為之震動。當時內閣二輔許國(此為徽州鹽商子弟)的主張是,應給對方一個狠狠的打擊,使對方不敢再來挑釁,且皇帝也傾向于
這一舉措,但最終還是聽取了首輔申時行的意見,堅持“款貢”政策。現在看來,應當避免戰爭。申時行的圓滑謹慎性格,在這次討論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但問題是,采取了“款貢”政策以后,并沒有使朝廷的軍餉開支降下來。
萬歷二十二年,戶部尚書楊俊民在給皇帝的奏疏中,曾列有大量關于軍餉增加的數據。其中稱:“臣考嘉靖以前,九邊年例銀止一百萬有奇;而隆慶初年,遂至二百八十余萬矣;今查去年(即萬歷二十一年)所發,數至三百四十三萬,比隆慶間又增六十余萬矣。”
該奏疏還稱:“薊鎮舊止六萬七千有零。今至三十八萬九千余兩;密云舊止一萬五千有零,今至三十九萬四千余兩;永平舊止二萬九千有零,今至二十四萬六千余兩;……”
更多的數字已不必再列。這似乎又表明,曾國藩于清咸豐元年所稱“自古開國之初,兵少而國強,其后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之言,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或許正是這樣的情況,不但導致明代淮鹽經營中的“困守支”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而且隨著朝廷經濟狀況的愈加困難,致使兩淮鹽政變革朝更深的層次發展。下面便趁此機會,對明朝的兩淮鹽政變革,做一個簡單的回顧及小結,以便與上面所述的情況相對照:
1、洪武三年六月,始行開中鹽法。當時灶戶生產的全部鹽貨(含正額鹽和余鹽),須全部上繳官倉。朝廷則以這些鹽貨與商人做糧食的交換,并令商人將所得鹽貨,運送到指定的地點銷售。這時,朝廷依然是全部鹽貨的經營者,只是其中由鹽產地到引地的經營資本,是由商人支付,且商人不能與灶戶直接交易。這可被看作是明朝兩淮鹽政變革的第一階段。
2、洪武二十三年以前,因困守支便有“不拘資次支給”政策的出臺。
3、正統五年,有“常股”與“存積”鹽政策的出臺。
4、成化年間便出現“以銀中鹽”和“在鹽產地賣鹽”的情況,并在成化十九年,出現鹽商職能的分化,從而有邊商與內商的出現。
5、弘治五年,曾由朝廷做出統一規定,即商人在鹽產地運司納銀,便可獲得鹽貨,史稱“葉淇變法”。但該規定在嘉靖初年被改變為,正額鹽仍在邊地開中,并且仍由“邊商中引,內商守支”。只是這時已實行“余鹽開禁”,即凡向邊商購買倉鈔并守支的內商,可按一定比例,直接向灶戶購買一定數量的余鹽,以屆時正余二鹽并掣。霍韜甚至提出建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余鹽三百引”。“余鹽開禁”使商人可直接向灶戶購買余鹽,這可被看作是明朝兩淮鹽政變革的第二階段。
6、到萬歷年間,實行“倉鹽折征”,即這時商人繳納給朝廷的糧食,已完全演變為正額鹽的鹽課,商人不能再憑倉鈔到官倉支鹽,而是須向灶戶另外購買。與此同時,灶戶生產的全部鹽貨,也不再上繳官倉,而是按規定賣給持有倉鈔的商人(但這時灶戶也須向朝廷繳納課銀,有關這方面的內容,請見筆者另一拙稿)。朝廷則完全由經營者演變為管理者,并以此向鹽商收取鹽課。這可被看作是明朝兩淮鹽政變革的第三階段。
作者簡介:汪崇筼(1942-),男,高級工程師。
(責任編校林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