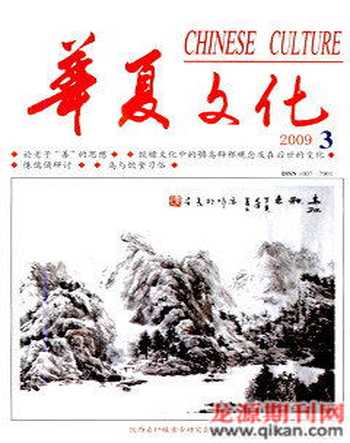從孔子與商鞅的從政經歷看兩種“成功”
郭繼承
在中國歷史上,立下豐功偉績的偉人可謂不少,但真正能稱得起圣賢的人,并不是很多。在鳳毛麟角的圣賢之中,又獨以孔子為尊。但如果以從政的時間與經歷而論,孔子除了短暫的魯國從政經歷外,自五十六歲周游列國,“累累若喪家之犬”,并沒有得到真正實踐自己理想的機會,與那些在政治上呼風喚雨、功成名就的人相比,孔子的落魄似乎并談不上什么“成功”。而比孔子晚一些的商鞅則不然。據《史記》記載,商鞅四見秦孝公,終因稱霸之道和強兵之術而得到秦孝公欣賞。盡管商鞅終遭遇車裂之刑,但施展自己抱負的愿望還是得到了實現。如果我們還原到春秋戰國之場景,孔子落魄,商鞅被任用;似乎商鞅春風得意;但歷史的評價卻恰恰不然。兩千多年以來中國歷史并沒有因為孔子的落魄而絲毫貶損于他,卻將圣人這一個無上尊貴的稱號加冕在孔子頭上。到了西漢的時候,董仲舒甚至在《天人三策》中將孔子稱之為“素王”。這其中緣由何在?為何一個并沒有機會推行政治理想的老人得到了如此尊貴的榮譽?這恐怕要從中國文化的基因中尋找答案。
在中國文化的脈絡中,對真正的知識分子而言,無論是“學”,還是“仕”,都不是純粹為了謀取“稻梁”,應該是將推行“道”視為自身自覺使命的群體。在《莊子·養生主》一章中,就連一個廚師,都主張由“技”而進乎“道”。孔子曾說:士志于道,而惡衣惡食者,未足議也。對于“道”的重要性,孔子曾經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因此,在于孔子看來,一個知識分子真正的使命,不是追求滿足自身的各種欲望,相反,應該把追求、實踐“道”作為人生的最高理想。
在《論語·微子》,曾經有這樣的記載: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日;“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于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孔子的態度很明顯,即:在春秋戰國亂世之中,人們被物欲、權欲所牽引,統治者甚至“率獸而食人”,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仁道”很難得到統治者的認可和推行,但是,“仁道”的合理性并不因為統治者的漠視而沒有價值。相反,“仁道”作為一個亂世中的文明火種,為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傳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凝聚中華文明傳承的靈魂,這也是中國文化最有魅力的地方。
在孔子看來,君子的使命與責任就是推行道義,實現“近者樂,遠者來”的政治理想,國泰民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心情舒暢,天下太平,文質彬彬,人民安居樂業。孔子所感慨的“天生德于予,桓(鬼隹)其如予何?”就是對自身使命的清醒認知。有了這種使命意識與擔當精神,面對人生的各種誘惑,孔子曾經說:“不義而福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孔子的學生子路在這個問題上,應該說得到了老師的“真傳”,在《論語·微子》中,曾有記載:子路從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莜。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蕓。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通過以上簡單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果以事功而論,孔子談不上叱咤風云,但從肩負道義而矢志不渝看,孔子可謂千古一人,一人千古。與此相反,商鞅則不是這種人。
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后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可見,商鞅并非不懂仁義之道,但在商鞅心中,實踐什么“道義”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如何看人下菜以討統治者歡心,從而為自己的所謂“成功”謀取機會。在商鞅的內心中,并非將推行仁義之道視為神圣的人生最高理想與價值,相反而是將其視為謀取個人名利的“工具”而已。就連司馬遷亦對商鞅頗有微詞,稱其為刻薄寡恩。
通過對孔子和商鞅的對比,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所謂成功,應該包括兩種含義:一種是對“道”的堅守,即無論怎么樣的艱難困苦,都能夠矢志不渝,這種將道義置于最高位置并自覺能夠抵制各種誘惑的言行,就是成功。這種成功是對人生使命的領悟,是對人生責任的擔當,更是對人生名利等誘惑的放下!這種成功以操守面對自己的心靈,不被物移,真正能夠做自己的主人!何謂圣人?圣人不在于“治人”,而在于治心——即降伏自己的心。享有這種“成功”的人,皆是那些“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大丈夫心中,皆是浩然之氣;相反,很多人都是做了自己貪欲之心的奴隸,哪里有孔子“我欲仁則斯仁至矣”的大氣與神氣!
另一種則是局限于追求“事功”,即那種將個人名利置于最高位置,單純地將實現個人價值視為最高追求。說到底,這種成功無非是絞盡腦汁為了實現自己的名利罷了。我們并非一貫反對一個人對事功的追求,關鍵是一個人的理想是否滲透了對社會和他者的責任?如果是抱著“個人最大”的所謂“理想”,即便是成功,無非是滿足了自己的身腹之欲而已。這種成功的背后,我們看不到道德人格的高大,相反看到的多是蠅營狗茍,看到的是“只要成功可不計手段”的陰險。
由此,我們也不難明白,為什么歷史上很多所謂成功的人卻沒有正面的評價;相反,那些看似不得志的人卻得到無上的尊敬和仰慕。孔子如是,屈原如是,許多志士仁人皆如是。當然,事功與道義之間并非一定對立,而應該是和諧融為一體。在中國歷史上,孟子的“仁政”理想即這種和諧統一的體現。但這需要統
治者有高超的智慧,否則一個被權欲綁架的統治者怎么會肯定“道義”的價值呢?
肩負道義,看似迂遠而闊于事情,但實質上卻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價值之一,是人類社會能否健康發展、太平祥和的根本保證。因此,我們不難看到,盡管歷史上不少血雨腥風,各色人物在貪欲名利牽引之下而刀光劍影,“流遍了郊原血”,但是正是因為“仁道”的文明火種一直在矯正著中國文明的進程,中華民族才能綿延數千年而至今天。孟子、韓愈、朱熹、王陽明等一大批人文知識分子,都自覺將踐行“道義”視為自身最高理想。孟子曾言:“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從孟子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得出,孟子并非沒有機會做官,也并非沒有能力做官,只是當時統治者根本沒有認識到“仁道”的內涵與重要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去做官,除了滿足自己的貪欲之外,根本不可能實現“仁政”理想。因此,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都會選擇拒絕。孔孟的這種做法,已經成為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一種自覺。
到了唐代,韓愈借鑒禪宗法脈的提法,提出“道統”一說。韓愈在《原道》中提出:“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當前有一些學者對韓愈指出的“道統”提出質疑,認為所謂“道統”,不知所云。但在我看來,中國文化的“道統”絕非“不知所云”。這種道統既包含了中國文化對“道義”內涵的思考,也包括了人們在實踐中對“道義”的擔當精神。如果我們冷靜總結中國的歷史乃至人類的歷史,會發現人類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道義不斷展開的歷史,在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固然會有很多逆流、回旋,但尊重人、愛護人始終是人類文明的內在要求。從古代的仁政,到現代的民主,盡管在具體操作的形式上有了變化,但在尊敬人的權利與尊嚴方面具有內在的一致。而且,如果沒有圣賢的這種擔當與堅守,中國文化中最優秀的人文精神就很難得到傳承,中華民族的命運究竟如何,就很難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