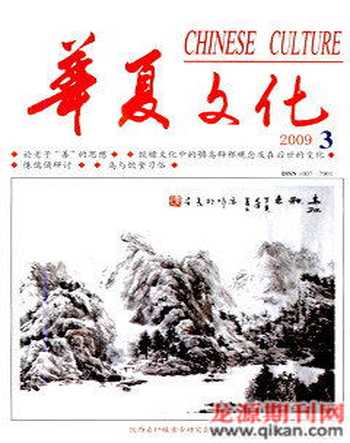論“正名”
聞 華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開篇很有意思,他既不是從三皇五帝說起,也不是從夏商周的某一個朝代完整開始,而是把周朝歷史攔腰截斷,從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著筆。這一斷限,有他自己的寓意。那么,司馬光究竟為什么取了這樣一個年限?《資治通鑒》不是斷代史,而是通史,這樣一個年限,除非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否則是不能取的。對于初讀《通鑒》的人來說,看到這個年份難免感到突兀。如果是從夏禹立國、商湯代夏、西周代商任何一個朝代開始寫,我們都可能會覺得多少都有道理。甚至從周室東遷開始寫,我們也不會覺得奇怪。作為通史,要講究王朝之間的連貫性,而司馬光的葫蘆里賣的是什么?
原因其實很簡單:這一年,晉國的大夫魏、趙、韓三家,取代了西周以來的晉國。這就是“三家分晉”。從春秋開始,周王朝的“天下共主”局面就不那么安穩了。春秋五霸先后逞強,你打過來他打過去,一派亂哄哄的景象。按理,在當時的分封制下,諸侯發生了糾紛沖突,周王要進行調解仲裁;違反了規矩的要進行懲罰。但是,春秋以后,由于周王室越來越衰弱,諸侯只是名義上尊周王為天下共主,實際上誰也不理睬它。周王只好睜只眼閉只眼。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曾經是一代霸主的晉國,也沒能守住晉文公傳下來的基業,幾個有勢力的卿大夫,串通起來就把晉國給滅了,自己取而代之。周天子承認了事實,加封瓜分了晉國的魏、趙、韓為諸侯。這種大臣起來推翻諸侯的事件,在亂哄哄的春秋以后,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但是,周王承認這種瓜分,并冊封瓜分者為諸侯,這是第一遭。
顯然,在司馬光眼里,三家分晉是比周室東遷更重要的歷史事件。很多人會感到迷惑不解。對于西周王朝來說,周室東遷是多么大的事件啊,國都豐鎬二京丟掉了,周幽王的性命丟掉了,好端端的西周從此變成了東周,難道這事件還不大嗎?如果司馬溫公從周室東遷開始寫,好賴都說得過去。三家分晉固然不是小事,但能夠同王朝更替相比嗎?干嘛非要取這么個事件作為開頭呢?我相信,不少看《資治通鑒》的人,都會對司馬光的這個起筆點感到迷惑不解。
司馬光自己的解釋是:三家分晉標志著周朝制度的實質性變化,而周室東遷僅僅是歷史事件。用現在的話來說,平王東遷,只不過是公司變換了注冊地點,原來的經營區域被競爭對手搶走了,沒辦法,公司換個地方另行開張;甚至周幽王的死亡,也不過是換了個董事長,公司還是原來的公司;而三家分晉,則是改變了公司章程,這就不是僅僅換地方的問題,也不是換人員的問題,而是公司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所以,司馬光認為,三家分晉比平王東遷更重要,從這里寫起更合適。
周朝的章程是什么?是禮制。從周公制禮開始,西周的整個統治體系,概括起來就是一個字——禮。禮是什么?禮就是名分,就是規矩。禮的內容有多種多樣,大到國家體制,社會規范,小到吃飯穿衣,走路姿勢,都由禮來確定。孔子吃飯,肉切得不整齊就不吃,這就是禮。禮的核心是等級劃分,表達方式就是上下位置和順序規則,不得僭越。沒有禮,就等于亂了套。象征秩序的器物和名分是不能亂套的,更不是隨便給人的。周厲王、周幽王不爭氣,把國家搞得不成樣子。但是,周王朝的根還沒斷,國脈尚存,就是因為后來的周室子孫還能守住名分。東周王室雖然只有巴掌大一丁點地盤,實力連個小諸侯都比不上,春秋的幾大霸主,論實力足以把周室滅了,但他們誰也不敢,就是因為名分問題。一旦突破名分界限,就會成為天下公敵,這就是名分的重要性。
但是,三家分晉,周王室自己毀壞了名分。你沒有實力,不能主持正義、討伐叛賊,也就罷了,作為周王,還給這些犯上作亂的卿大夫加封諸侯頭銜。這標志著周朝的禮制徹底玩完。所以,三晉列于諸侯,實際就是周室政治生命的終結。
司馬光的“正名”是不是小題大做,強詞奪理?并不那么簡單。從歷史的角度看,周室冊封魏趙韓,可能確實有它的不得已之處,但從邏輯的角度看,“正名”則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它可以給我們現實中的管理提供一些相應的參考。
“名分”往往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正名”的問題,從孔子起就予以高度重視,“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司馬光繼承的就是孔子這一思想。那么,“名分”的作用到底在那兒?人們經常“名實”連用,“名”這東西能當得了“實”嗎?用現在的話說:名分值幾個錢?
名分確實不能用錢來衡量,但它的作用是實實在在的。在歷史上,注重名分的正當性的例子,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比如,春秋五霸中的齊桓晉文,征戰別的國家,打的都是尊王攘夷的旗號,“尊王”就是名分。秦始皇統一天下,但是,周朝的“九鼎”卻找不見了。而九鼎恰恰是三代天子名分的象征物品。所以,秦始皇不找到九鼎誓不罷休,據說九鼎被沉到了泗水,秦始皇就組織人力幾乎把泗水徹底挖了一遍。后來搞出個傳國璽來才算拉倒。西漢劉邦起身草莽,得了天下,一介平民,要當皇帝,似乎在名分上有點欠缺。于是,他不惜拿他的父母親做幌子,宣稱他母親是在野外郊地感受了龍的身孕,于是,他就成了“名正言順”的真龍天子,當皇帝也就當得順溜了。西漢的國家名分象征物是傳國璽,于是,王莽篡漢,不把傳國璽拿到手里就寢食不安,為此還同他的姑母王政君鬧了別扭。明朝的武宗皇帝亂來,大臣們拼死諫諍,也是為了名分。嘉靖時的大禮議,萬歷時的爭國本,都是名分之爭。一直到清朝,大臣們還不停地要論證“我朝得國之正,亙古未有”。類似的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這就值得我們認真想想“名正”和“言順”的關系。并在這種關系中找到今天管理的參照系數。
固然,從孔子到司馬光,要正的“名分”是統治者的禮制秩序。但是,如果我們撇開“正名”所包含的時代內涵,而從“正名”的思考邏輯人手,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所謂“正名”,其思考的邏輯是名副其實。而這正是現代管理離不開的。用比較學術化的語言來說,正名首先是要追求行為理由的正當性,其次是追求行為與理由的一致性,最后還要防范行為與理由的背離。
首先,行為理由的正當性。這是任何一個管理者都必須重視的。人不管干什么,內心必須有一個信念,我干這個事情是正當的,是值得干的。在管理中,這就是組織目標的定位問題。任何管理,不管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存在一個對目標價值的考量問題。如果這個目標不值得實現,那所有的管理都沒有意義。古代由于時代限制,把這種目標定位為“天命”,所以皇帝下詔都要以“奉天承運”作為自己命令的正當性來源,社會上的草莽造反,也得打出天命的牌子。不管是小說中的“替天行道”,還是史料中的“黃天當死,蒼天當立”,都是表達這種正當性。沒有這種正當性,就沒有從事相應事項的必要,當然也就沒有管理。所以說,正當性是管理的立足點。
古代把正當性歸結于天命,并把天命與人情倫理、綱常禮教聯系為一體。今天隨著
社會的發展,正當性已經不再是天命之類東西,而是人類自身的價值實現。所以,一個企業,肯定要實現利潤,但是,利潤不是企業的最終目的。只有當實現利潤對社會有貢獻,能夠增進社會福利,促進社會發展,賺錢才是正當的。這就是所謂的“商道”。這個“道”,不是技巧,不是權術,而是道義。作為政府,肯定要實施統治,而只有這種統治能夠保障人民生活,維護社會安定,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個統治才是正當的。商有道,政有道,各行各業都有它的道,古人甚至說“盜亦有道”,就是強調這一點。作為管理者,首先廊當弄清楚的,就是你的“道”是什么,這個“道”,就是你做出行為的名義。這就是“正名”。周王分封三晉的不當之處,就是迫于壓力自行放棄了對正當性的堅持,以分封肯定了“大逆不道”的行為。如果一個公司,只管賺錢,而不管錢來得是否正當,那么,它的“道”就可能是歪門邪道,在具體操作上就會發生坑蒙拐騙,這個企業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會意義。從歷史上看,一個政府,如果不管人民死活,遲早會喪失自己的統治權力。所以,研究管理的學者,總是把一個組織的管理置于目標與價值的大前提下來進行相應考慮。
其次,行為與理由的一致性。管理的各種舉措,不管是制定制度規范,還是實際操作,都要保持行為和理由的一致,也就是名實相副。這個“副”不是簡單地符合,準確的含義應該是匹配、相稱。在這一方面,現實中的管理問題極多,最大的問題,就是機會主義。關于機會主義,經濟學中有嚴密的論證,說通俗一點,機會主義就是名實不副。為了取得“實”而不顧“名”的約束,拋棄“名”限定的行為準則,見利忘義,一切以“利”為取舍。
常見的機會主義問題,通常不會放棄正當的名義,但是在正當的名義下面卻干著名實不副的事情,其結果必然是自毀業基。比如,在制定薪酬制度的時候,把按勞取酬說得震天響,信誓旦旦強調多勞多得;但實際操作時,考慮面子人情上下級別等等因素,干多干少一個樣,甚至所勞和所得倒掛,薪酬并不反映業績,這樣,哪個員工會相信你是按勞取酬?這就需要“正名”。再比如,在用人時,嘴上說的是不拘一格,實際做的是論資排輩,哪個員工還會相信你是任人唯賢?這也需要“正名”。企業的宣傳說得天花亂墜,似乎一切都是為顧客著想,但實際運作卻是唯恐刀子不快,宰割不狠,從顧客那里能撈多少是多少,給顧客的服務越少越好。這同樣需要“正名”。所謂正名,具體操作雖然方式多樣,但準則只有一個,就是追求名實相稱。實不忘名,名不離實。“打左燈,向右拐”,有可能在眼下走上捷徑,但引來的問題就是指示燈不再起作用,久而久之,別人就不再理睬你的指示燈,甚至看著指示燈就會走到相反的方向。
對于如何堅持管理者的信念,做到名實相副,哈佛的管理學教授安德魯斯(Kenneth R.Andrews)強調,經理的實踐行為,比紙面上的規定更有力量。當某個產品發現質量缺陷但又沒有成文制度糾正時,總裁斷然下令召回這一產品,那他就無疑向員工傳遞出關于產品質量的明確信息(海爾的張瑞敏在創業時砸冰箱正是這樣)。而當有著嚴密的制度規范但經理在執行中卻“寬宏大量”的時候,員工獲得的肯定是另一種信息,可以馬馬虎虎大而化之的信息。所以,管理者的行為,能夠處處想到道義名聲,才能徹底杜絕機會主義。
再次,還要防范行為和理由的背離。所謂行為和理由的背離,是指追求虛名,這與機會主義有聯系,但也有區別。所謂聯系,是二者都反映出名實不副;所謂區別,是機會主義落腳于實,為了實而不顧名的約束;而追求虛名落腳于名,為了名而不顧實的不足。正因為“名”代表了正當性,所以,有的人會不顧一切只求名而忘了實,把名看得比實更重要,似乎只要“正義”在手,就能穩操勝券。這就會導致追求虛名,自己擁有的實力并不足以實現“名”指向的目標,卻不自量力。這種現象,在歷史中也十分常見。比如,東漢末年的袁紹務名,而曹操務實。袁紹空有虛名,反而因為他的虛名給自己帶來了災難。在三家分晉事件中,周王倒沒有追求虛名。也許有人會說,這正是周王務實的表現,恐怕不然。假如周天子不自量力,宣布討伐犯上作亂的魏趙韓,那才是貪圖虛名。周天子不這樣做是正確的,但是,冊封三晉的做法退讓得過了頭,這不等于務實,而等于把自己存在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交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