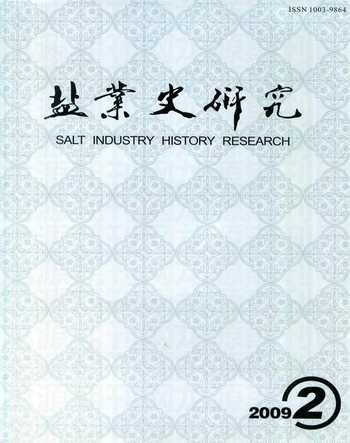“兩淮預提鹽引案”略論
余清清

摘要乾隆三十三年的兩淮預提鹽引案,是涉及兩淮鹽政、鹽運使與兩淮鹽商沒有將預提鹽引支付的銀兩上繳國庫的事件。史學界普遍認為此案是乾隆中期的特大貪污案件,是兩淮鹽官與兩淮鹽商相互勾結貪污的產物,這個案件揭露出清乾隆時期鹽務腐敗、官商勾結、賄賂成風。但實則不然,爭奪地方鹽政的控制權,才是這次案件爆發的真正目的。通過對這個案件的分析,可以了解乾隆在執政中期對兩淮鹽務的管理狀況。筆者重點從審理過程人手進行分析,進而發現乾隆重點審查的是兩淮鹽官,對兩淮鹽商采取了相對寬容的政策,并沒有進行實質性的審查。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乾隆皇帝以及中央政權與鹽商之間存在的無法割舍的經濟聯系以及兩淮鹽商在兩淮地區的重要地位。但此案后,中央并沒有完全控制地方鹽政。兩淮鹽務也逐漸衰敗。
關鍵詞兩淮預提鹽引案;兩淮鹽商;兩淮鹽官
中圖分類號:K24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864(2009)02-0030-08
乾隆三十三年發生的兩淮預提鹽引案,是涉及兩淮鹽政、鹽運使與兩淮鹽商沒有將預提鹽引支付的銀兩上繳國庫的事件。對于此案性質的判定,史學界普遍認為它是乾隆中期的特大貪污案件,是兩淮鹽官與兩淮鹽商相互勾結貪污的產物,這個案件揭露出清乾隆時期鹽務腐敗、官商勾結、賄賂成風。也有學者認為,此案純屬冤枉,實質是乾隆擔心中央權力被鹽官架空,懲罰鹽官的一種方法。在分析案件時,以往研究多關注案件審理的結果,僅從案件涉及的金額有一千余萬兩來判定這是一個特大經濟貪污案件,而沒有對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進行深究,也沒有將此案件放在乾隆中期這個大背景下進行分析。筆者對案件的審理過程仔細分析,發現這一案件并非如此簡單,而是存在若干可疑之處,這些可疑之處可能使我們觸及到乾隆在其執政中期對兩淮鹽務狀況處理的某種矛盾與困境。
一、兩淮預提鹽引案的由來
關于兩淮預提鹽引案的由來,《清通鑒》曰:“兩淮鹽區正式預提鹽引始于乾隆十一年,系因淮鹽行銷地區人口繁滋,需鹽增加,淮鹽額引當年繳銀一兩五錢余,較正引鹽課多獲利約銀二兩。嗣后乾隆帝屢舉南巡,兩淮鹽商迎蹕,治揚州等處行宮,極盡奢華,迨車駕臨幸,輒留數日乃去,而商人所費不貲。又頻歲上貢及幫貼歷任鹽政等進貢,亦踵事增華,商人難堪其累。遂以預提鹽引所得余利為公使錢,以為辦差、辦貢之用,而事皆未報部。至是,新任兩淮鹽政尤拔世發其弊。”乾隆帝即命軍機大臣檢查戶部檔案,經查并無造報預提鹽引所課之稅派項用數文冊。而自乾隆十一年開始預提鹽引,每年提引二十到四十萬不等,若以每引課稅三兩計算,二十年來所征稅銀應有千余萬兩。乾隆帝以歷任兩淮鹽政未向戶部報明收支情況,顯有蒙混不清,私行侵蝕情弊,即命傳諭江蘇巡撫彰寶速往揚州,會同尤拔世詳悉清查,務求水落石出。
《清通鑒》認為,整個案件是因為商人以預提鹽引所得余利為公使錢,以為辦差、辦貢之用,而鹽政沒有將余利錢的使用報戶部才引起的,并沒有承認這是一個貪污案件。揭發者尤拔世只是將鹽務的弊端報告而已,并沒有其他的用心。《清稗類鈔》也認為,正是由于“風聞鹽商積弊,居奇所賄未遂”,才導致了整個案件的發生。整個案件的發生都是一種巧合,并沒有更深的用意。
事情真是如此嗎?兩淮預提鹽引案涉及的時間是乾隆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三年,中間相隔了二十二年,經歷了幾任鹽政與鹽運使。為什么惟獨到了乾隆三十三年,才被新上任的尤拔世揭發出來呢?其原因在于前幾任鹽政更多的是地方權益保護者,尤拔世則是中央權益的代言人。
在乾隆時期,尤拔世多以朝廷代言人形象出現在地方行政中。如乾隆二十一年,他被乾隆帝派往九江關監督辦理窯務,外派的任務就是代表朝廷督察前監督唐英任內,長期“變價銀兩不能年清年款”、“遲誤錢糧”、征存稅項等不明之事。經過數月查明,九月初尤拔世即上奏折稟明這件事情的原委,提出方案,懇請朝廷處理。可見,乾隆時期的尤拔世由于具有豐富的與地方斗爭經驗,再加上乾隆帝的賞識,在中央治理兩淮鹽政的大背景下。他出任兩淮鹽政也就是中央加強地方控制很自然的一步結果。因此《清通鑒》、《清稗類鈔》中所言的余利錢的使用沒有報戶部,“風聞鹽商積弊,居奇所賄未遂”等原因僅僅是中央權利欲控制兩淮鹽政的一個引子而已。
二、對案件本身的分析
這個案件之所以會成為乾隆年間的一個大案,是由兩淮鹽務的重要性和案件涉及到人員的重要地位所決定的。
首先,從兩淮鹽業在國家經濟上的重要性來看。清代兩淮鹽業經濟更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有著重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鹽業可以為國家提供巨額稅收。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包括三塊:田賦、鹽稅和關稅。兩淮鹽場是全國最大的鹽場,額征鹽課幾乎占全國鹽課總量的一半。當時全國地丁收入約2600萬兩,最盛時3300萬兩,鹽課數約占二分之一。不僅如此,國家每有重大軍事行動,或天災年荒,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慶,鹽商就捐輸報效。兩淮鹽商捐輸額高達3826.6萬兩。即如果兩淮鹽務出現了嚴重弊端,乾隆年間的稅收就很難得到保證,整個國家的運轉將會出現不穩定的狀況。
其次,這個案件涉及到兩淮鹽商、兩淮鹽官和中央三方面的重要人員。
兩淮鹽商是乾隆中期最有實力的商幫,對整個國家經濟起著重要的作用。兩淮鹽商富可敵國,他們靠朝廷的寵惠和地方官府的庇護,成了中國社會最為顯赫的階層。他們是清廷財政的支持者,地域經濟的操縱者,也是地方事業的倡辦者。如案件的主要人物江春,“少攻制舉業,乾隆辛酉(1741)鄉闈以兼經呈薦,因額溢見遺,遂棄帖括經商揚州。練達明敏,熟悉鹽法,司鹺政者咸引重,推為總商。才略雄駿,舉重若輕,四十馀年,規劃深遠。高宗六巡江南,春掃除宿戒,懋著勞績,自錫加級外,拜恩優渥,不可殫述。曾賞借帑金三十萬兩,為鹽商之冠,時謂‘以布衣上交天子。”可見,以江春為代表的兩淮鹽商是—個財富過人,權勢傾天的特殊的地方利益集團。
案件涉及的兩淮鹽務官員也有特殊的背景。如:高恒,“字立齋,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高斌子也。乾隆初,以蔭生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出監山海關、淮安、張家口榷稅,署長蘆鹽政、天津總兵。二十二年,授兩淮鹽政。”可見,高恒有著良好的出身背景。另外,高恒的家族也與皇族有著密切的聯系,是皇室的外戚。如“方上誅高恒,大學士傅恒從容言乞推慧賢皇貴妃恩,貸其死,上日:‘如皇后兄弟犯法,當奈何?傅恒戰栗不敢言。至是,諭日:‘高樸貪婪無忌,罔顧法紀,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為慧賢皇貴妃侄,而稍矜宥也。”盧見曾,“字抱孫,山東德州人。康熙六十年進士,歷任知縣、知府,乾隆元年擢兩淮鹽運使”。他與大學士紀曉嵐有姻親關系,與金農、沈大成等人也有很深的私交。可見,中央對于兩淮鹽務官員的任命是謹慎的,
通常會挑選有資力和良好出身背景的官員來擔任。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兩淮鹽務官員本身也與中央保持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另外,案件中直接涉及的中央大員也不在少數。如刑部郎中王昶、內閣中書趙文哲、徐步云等人以私自送信與盧見曾皆獲嚴譴。大學士紀曉嵐也因此事而受牽連。
可見,本案所涉及到的人物包括了地方和中央的重要人物,并且這些人物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案件本身是發生在兩淮地區的,但是由于兩淮鹽務的重要性與案件所涉及到的人員的特殊性,使得這個案件不再局限為一個地方案件,而成為一個全國性的案件,成為乾隆朝三大案之一。
三、案件的審理過程
整個案件按照時間可分為兩部分,每個階段乾隆皇帝表現出來的態度也是不同的。
(一)六月份
在六月二十五日,江蘇巡撫彰寶呈上了第一份奏折稱:“會同尤拔世查辦預提綱引,……查歷年提引,各商共獲余利銀一千九十余萬兩。”并稱:“乃竟隱匿不報,前鹽政等居心實不可問。……惟是預提引張銀兩,一切俱系總商經手,因傳喚總商詳訊,并令其開出清單。”于是便得到了以下供詞:“據稱歷年辦貢及預備差務,共用過銀四百六十萬兩,尚有各商未繳余利銀六百數十萬兩。”通過對鹽商的復審,總商黃源德、江廣達等又供稱:“據辛巳綱(乾隆二十六年)兩次交過高鹽政(高恒)銀八萬五千九百余兩。丙戌綱(乾隆三十一年)又送銀四萬兩。乙酉綱(乾隆三十年)又送銀一萬兩。均系管事人顧蓼懷經手收進。”“又自乾隆十四年起,代吉鹽政(吉慶)辦貢物,共墊銀三千余兩。”“又二十一年,代普鹽政(普福)辦如意銀三百二十兩。”
皇帝就第一份奏折批示:“著傳諭彰寶等,即速按款查究。除折內所稱綱引應交官帑,各商未繳六百數十余萬兩,并該商等代鹽政等一切冒濫支銷應行追出歸公之項,自應按數查辦外,至歷任鹽政等如此任意侵肥,審明有應著追之項,如力不能完,亦應于商人等名下按數分賠。再該鹽政等在任日久,其中必有留寄兩淮等處,令商人生息漁利情事。該商等即應一一供明,和盤托出。如此時稍有含糊,將來一經發覺,亦惟該商等是問。并著彰寶曉諭各該商。”接著,乾隆皇帝傳諭:將原授給六大總商的職銜盡行革去。
就六月二十五日的奏折來看,乾隆皇帝對鹽商的態度是很強硬的,認定他們負有重大的責任。首先是鹽商們越權了,做了鹽政應該做的預,備差務的事情。其次,在具體執行時,他們存在著冒濫支銷的行為。最后,兩淮鹽商對歷任鹽政侵肥行為也負有間接的責任,并與鹽政之間存在著金錢的聯系。
乾隆皇帝對鹽官的態度更為強硬。一開始就將鹽官的罪名定性為“侵肥”,并且在“侵肥”前面加上了“如此任意”這四個字,說明乾隆皇帝對鹽政的行為深感氣憤與震驚。所以才會在沒有明確證據的情況下,開始推測鹽官們的其他罪行即“令商人生息漁種情事”,一定要對鹽政徹查到底。
但對二者之間的強硬態度又是不同的,乾隆皇帝對兩淮鹽商主要是在金錢方面的強硬,要求鹽商補交所有的銀兩與承擔鹽政所侵肥的銀兩,并且主動配合積極交代鹽官“侵肥事實”。可見,從一開始,乾隆皇帝對兩淮鹽商的懲罰就限定在金錢方面,并且將兩淮鹽商作為“從犯”來對待,要求其積極地揭發“主犯鹽政”的罪行。而對鹽政的強硬態度則是超越了金錢的范圍,不僅對其侵肥的事情徹查,還要對“令商人生息漁利”的事情徹底調查。
六月二十六日,乾隆對兩淮鹽商的態度則有了明顯的變化。“惟是兩淮鹽務關系數省民食。現在各商俱有應行質訊之處,若因此稍有推諉觀望,致運鹽觴或有壅滯,則是有心貽誤,惟恐眾商等不能任其咎,尤拔世即悉心籌劃并明切傳諭。”從這份諭旨來看,乾隆皇帝對兩淮鹽商的態度顯然緩和了很多,擔心兩淮鹽商因為自己太過嚴厲的態度耽誤兩淮鹽務。從時間上來看,乾隆皇帝選擇在第二天就立刻發出這道上諭,足可以證明其對兩淮鹽商的重視程度,更可以表明對兩淮鹽商則是寬大處理,區別對待的。所以,在案件的初期,乾隆皇帝就表明了對鹽商輕、鹽官重的相反態度。至于鹽商和鹽官的關系,乾隆皇帝也認定存在著官商勾結,共同侵肥的關系。
(二)七月一九月份
案件在這三個月的審理,主要分為兩個部分進行,一是從顧蓼懷那里嚴加審問,得到高恒侵肥的有關證據。二是對鹽商進行審問,得到其他鹽官侵肥的有關證據。
第一部分:關于對顧蓼懷的審問: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癸巳日記載,顧蓼懷最初在揚州的供詞是:“自乾隆二十三年起,陸續收過黃源德等五商銀四萬八千兩;又收洪充實銀三萬兩。”“三十年收汪啟源銀一萬兩”。“二十五年又收黃源德等五商銀七萬一千余兩。”
供詞證明了兩淮鹽官收受了大量銀兩,但顧蓼懷并沒有將臟銀的用途說清楚,這就為他自己留了后路。顧蓼懷被提到北京后,即將供詞全部推翻。“據顧蓼懷經手銀十五萬余兩,俱悉代商人置辦物件,并無交與高恒收受情節,與揚州所取證供全不相符。詰其因何供詞互異情由,則稱在揚州時,承審之揚州府知府不準說是代辦物件,勒令供稱繳進高恒署內。”為此,揚州官員和鹽商江廣達到北京對質,從而又得到另一份供詞:“緣顧蓼懷初到揚州時,因無高恒所質,即妄供交高恒收受;即至進京,又以無商人可質,即稱系商人托令辦物。其實顧蓼懷經手之十五萬兩,系高恒托令向商支銀制辦物件,并非高恒盡行侵用,亦非商人托令代辦。”。顯然,在顧蓼懷、高恒處,案件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第二部分:關于對鹽商的調查
七月十一日:乾隆皇帝付出上諭:“即傳集各商總,切實訊問,令將普福任內各次提綱如何散給商眾,……若各商代為隱飾,別經發覺,則伊等獲罪更重矣。”七月十六日,彰寶上奏稱:“各總商因各鹽政將引張多多賞給所得余利,獨多樂于代辦古玩器物,以酬加賞引張之惠。”
根據這兩份奏折來看,兩淮鹽商是在為鹽官開脫罪名。他們也認為鹽官沒有侵肥,也承認了自己浮開銀的罪名,所以導致了一些余利銀的侵吞,并稱“并無將余利又還普鹽政之事”。另外,鹽商也未供出高恒等人“留寄兩淮”的罪行。
乾隆皇帝對此深表不滿,下詔:“著傳諭彰寶等,即提各商到案,詳悉開導,逐層研詰,務令供吐實情,水落石出,不得任其含混抵飾。如各商執迷不悟,其事豈能終不敗露?將來別經發覺,則是各商自取重罪,即該撫等亦不能辭其咎乎也。……所有此項無著銀兩,將來無可追抵,仍應于該商名下追還。同一應行人官之項,何必為普福狡展隱匿,甘心代人任過耶?各商等前于屢次南巡,承辦陳設諸事,彼時因念伊等出力急公,故稠疊厚加恩赍。……(今)朕從寬不加伊等罪譴,已屬逾格施恩。今止令其歸還款項,于情理應屬當然,而眾力亦非不給。可將此剴切諭商眾知之。”
可見,乾隆皇帝進一步明確地將鹽商和鹽官分開來處理。兩淮鹽商的身份由被調查入轉換成了重要證人。乾隆皇帝對鹽商采取了“動之以情,曉之
以理”的政策,要將鹽商和鹽官的共同聯盟瓦解,將鹽商拉到乾隆皇帝這一邊來,共同懲治鹽官。中央要將兩淮鹽務弊端—查到底的決心是一目了然。
調查的最終結論是:“原任鹽政高恒、普福以侵蝕鹽引余息,并受鹽商金,擬斬侯。為高恒置辦貢物之商人顧蓼懷擬絞侯。”前任鹽運使盧見曾被判處死刑。歷任鹽運使被受到牽連的有河南布政使何謂,江蘇淮徐道吳嗣爵均被降三級調用。已經解任之運使趙之壁被革職。前任總督尹繼善,交部嚴加議處。刑部郎中王昶、內閣中書趙文哲、徐步云因私行送信與見曾,獲厲譴。就連大學士紀曉嵐也牽連責戌。
鹽商們除了承擔自己應該付的那些銀兩,還被迫承擔涉案的兩淮鹽官的一些繳納銀。因為高恒、普福名下無可追抵之項,所以均著落總商名下賠完,通共計應追繳銀一千一十四萬一千七百六十九兩六錢。所有鹽商交給鹽政置辦物件的銀兩都被定性為“有意結納,于中取利,以至浪費無節”。
整個案件到此也就結束了,鹽商和鹽官的最后命運也是不同的,鹽商除了要在本年先補交一百二十七萬余兩,其余分九年按限追繳之外,還要每年比以往要多付一百多萬兩。高恒、普福等不僅沒收家產,還丟掉性命,對兩淮鹽官而言,這種懲罰是最嚴厲的。
四、原因分析
同樣是被告,兩淮鹽商和兩淮鹽官的最后命運卻有天壤之別,為什么乾隆皇帝會采取兩種不同的手段呢?以乾隆皇帝為代表的中央政權與地方鹽商之間存在無法割舍的經濟聯系,再加上鹽商在揚州的地位和巨大的影響力是促使乾隆皇帝采取不同措施的主要原因。
首先,兩淮鹽商是清政府經濟收入和皇家花費的一大支柱。以乾隆三十三年為界,在此之前兩淮鹽商共捐輸972萬余兩,之后兩淮鹽商捐輸的數額達到1900萬余兩,總共多達2872萬余兩。捐輸的大部分銀兩主要花費在軍費和備乾隆皇帝私用上。具體如下:
從上表可見,軍費和備皇家花費的金額達到了2437萬兩,占到了所有捐輸的85%左右。可以這么認為,兩淮鹽商是乾隆皇帝國庫的一個重要的來源。軍費和皇家花費中很大一部分都依賴鹽商的捐輸。因此在公在私,兩淮鹽商都是乾隆皇帝另一個重要的“國庫”。此外,除了為乾隆皇帝提供大量的銀兩外,兩淮鹽商還充當了乾隆皇帝的“經濟投資人”的角色。康熙時期,內務府每年會向鹽商貸銀數百萬兩,作為鹽商運鹽的周轉資本,然后再收取一定的利息。到了乾隆年間,這種借貸成了一種名義上的借貸。乾隆皇帝直接將捐輸之款交給鹽商“生息”,做無本的生意。而鹽商實際上要多付出利息錢。
兩淮鹽商與乾隆皇帝有著經濟上的密切聯系。這種聯系性就使得乾隆皇帝不可能去判處兩淮鹽商的死刑,也不會將鹽商的專賣權取消并將他們的家產充公,或者再重新挑選新的人選來從事鹽務。因為至少這些兩淮鹽商們還是很懂得“討好”乾隆皇帝的,是乾隆皇帝重要的經濟利益伙伴,而且乾隆皇帝也需要這種“討好”。
其次,兩淮鹽商與中央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如處分過重,會牽扯到整個朝局的穩定。如在乾隆三十年,曾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太監張鳳潛逃至揚州,最后卻被江廣達所拿獲。而內務府各衙門嚴緝累月竟不能獲,居然還讓張鳳逃到了揚州(8月初8日)。這更證明兩淮鹽商與中央政府有著密切的聯系。又者,刑部郎中王昶、內閣中書趙文哲、徐步云、大學士紀曉嵐等人的卷入也都證明了兩淮鹽商與中央官員之間密切的關系。
再次,兩淮鹽商在揚州也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是保持地方穩定發展的一個重要集團。兩淮鹽商在救災賑濟活動和社會福利方面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果他們遭受金錢以外的過重懲罰,就會導致兩淮地區的動蕩。
兩淮鹽商在兩淮地區積極從事救災賑濟活動,為地方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根據嘉慶《兩淮鹽法志》記載,筆者做了以下整理:
清代兩淮鹽運使衙門經費內有“淮南雜項”一款,乾隆三十三年核定為一百零九萬五千余兩,乾隆五十一年核減為一百零六萬兩。這筆款項支出中有救生紅船工食,撥補書院、育嬰、普濟等堂經費。在經費有一定保障以及鹽商的支持下,在兩淮鹽區淮南、淮北較為普遍地建立起育嬰堂、普濟堂、救生船,另外還建有收養所、藥局等機構。除此之外,鹽商還對淮南北城市的街道、橋梁、溝渠、水井等也常出資新建或改建。
綜上所述,兩淮鹽商對中央財政的重大影響、與中央官員的密切關系、在兩淮地區的重要影響力是促使乾隆皇帝對兩淮鹽商采取妥協態度的重要原因。
五、案件對兩淮鹽務的影響
案件以中央勝利而結束,乾隆帝成功地瓦解了兩淮鹽商和兩淮鹽官的聯盟,懲治了貪官。預提鹽引的銀兩均列入國庫,為國庫充實了銀兩,控制了兩淮鹽政。乾隆皇帝開始重新規劃兩淮鹽務,治理其弊端。乾隆三十四年冬,江蘇巡撫彰寶、兩淮鹽政尤拔世遵旨議奏兩淮鹽政辦貢章程。兩淮鹽政辦理貢物向外支銀四萬八千兩內動用一萬二千兩,每年向內務府辦造冊報銷,然此區區小數自然不敷常貢之用,故歷任鹽政亦未曾造報。審理兩淮提引案中,彰寶等奏稱,每年辦貢約需銀五、六、七萬不等,自十一年(1746)至三十二年(1767)約用銀一百十余萬兩。乾隆帝遂命妥定章程。彰寶、尤拔世建議外支銀應全用于辦貢,另外裁革陋規銀一萬七千四百余兩,每年共有六萬五千四百余兩作為辦理常貢和奉特旨交辦各物件之用。凡有應辦事件,鹽政不得與商人直接交涉。下軍機大臣議行。但是乾隆皇帝的目的并沒有達到。鹽商所偷漏的一千余萬兩鹽課,乾隆皇帝沒有完全收回。嗣后于三十五年(1770)、三十六年(1771)、四十六年(1781)一再展限;四十七年(1782)已完至第十三限時,奉旨豁免二百萬兩;四十九年(1784)南巡時又將尚余銀一百六十三萬余兩豁免。
其次,乾隆中期以后,各省商告疲。而兩淮的鹽業也開始衰敗。自乾隆初年起,由于額引暢銷,向于正引之外預提下綱目二十萬至四十萬。但自四十六年預提壬寅綱之后,至是四年未經兩淮鹽政奏請預提。這樣一來,國庫又少了一筆支出。兩淮鹽商開始衰落,總商江廣達的家產亦日漸消乏。乾隆三十六年,乾隆帝曾賞借江廣達三十萬以資營運。
六、結論
概言之,兩淮預提鹽引案是在中央治理兩淮鹽務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是中央加強兩淮鹽政控制的一個導火線。乾隆皇帝審理此案時,注意將兩淮鹽官與兩淮鹽商區別對待,將整治的重心放在了打擊兩淮鹽官上,通過削弱兩淮鹽官的力量,從而達到中央對兩淮地方鹽務展開有效控制的目的。對待兩淮鹽商,他則采取了寬容的政策。兩淮鹽商與乾隆皇帝之間密切的經濟聯系以及兩淮鹽商在兩淮地方事務上重要的影響力是促成乾隆皇帝采取此政策的主要原因。乾隆皇帝并不想要過分的打擊兩淮鹽商。而是希望加強自己對兩淮鹽商的控制力,從而保持中央和兩淮地方經濟的穩定。乾隆皇帝在處理兩淮鹽務時,試圖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掌控兩淮鹽務,盡量緩和與兩淮鹽商的關系,使得兩淮鹽商積極為中央效力。而兩淮鹽商也由于中央政府的庇護,在這次政治風波中生存了下來。但是,他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不得不積極捐出更多的銀兩來維護這種政治關系。結果是,雙方都增加了負擔。在沒有制度化的保證下,兩淮鹽商擺脫不了衰落的命運,而乾隆皇帝也無法保證兩淮鹽務正常有效的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