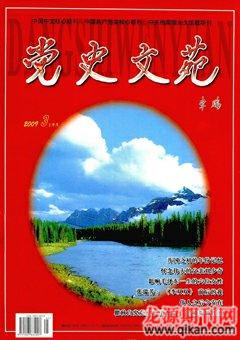張瑞芳:《李雙雙》前后的我
張瑞芳 王 嵐

口述者:張瑞芳
采 訪:王 嵐
采訪時間:2007年12月6日,
2008年3月21日
采訪地點:張瑞芳家
張瑞芳小傳:生于1918年。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跟隨姐姐參加“民先”活動,1938年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開始黨的組織關系由周恩來直接領導。1949年2月取道香港回到解放后的北平,10月,作為政協工作人員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之后調往北京電影制片廠。離開北影后進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出演新中國第一臺話劇《保爾·柯察金》,飾演冬妮亞。1951年10月調往上海電影制片廠,先后主演了《南征北戰》、《母親》、《家》、《聶耳》、《李雙雙》、《大河奔流》、《泉水叮咚》等影片。電影《李雙雙》曾獲第二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并多次隨國家領導人出訪國外。
瑞芳老師您好!很高興見到您。來之前,我拜讀了您的自傳體新書《歲月有情》,很全面,很真實,也很生動,真沒想到您的革命經歷這么豐富,更沒有想到您還有一位革命的媽媽。
我在書里寫的很坦誠,都是真的,包括我的感情生活。其實我媽媽的經歷比我豐富多了,她老人家很早就參加了革命。總理曾對我們說過,你們的母親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們兄妹幾人加起來都多。我娘對黨的事業貢獻多大,總理心里最清楚,他對娘的評價比對我們兄妹幾個加起來都要高!1944年,組織上安排我娘去延安治病。在那里,她見到回去參加整風的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對娘的精神稱贊不已,當面對她說:“你的情況我都知道。一位中將夫人,像你這樣,確實難能可貴。”新中國剛剛成立,日理萬機的總理就抽空到北京法通寺的家去看望我娘。我娘去世后,他還為我娘的墓碑題了字“廉維同志之墓”。據我所知,總理為革命母親題寫過墓碑的只有兩位:一位是我娘,另外一位就是孫維世的母親任銳同志。
瑞芳老師,您是我們敬仰的老革命家,老藝術家,一生經歷豐富而坎坷,這些都在您的書里得到了體現。我今天來,還是想麻煩您再談談解放后到上海電影制片廠工作期間的一些難忘的人和事。
這些我書里都寫了。
是的,我看了,這真是一份寶貴的歷史記錄。解放后,您一開始是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后來又到中國青年藝術劇團,在話劇《保爾·柯察金》中飾演冬尼亞,這是新中國的第一部話劇,一直到1951年10月才到上影。到上影前,您還去向周總理作了告別?
我到上影前曾經給總理寫過一封信,大致意思是:
我奉中組部之命,調到上海電影制片廠工作了,過了中秋之后十八九號動身去滬,矛盾了很久的舞臺、電影問題,不解決自解決了。
我直接收到組織部給我個人的信,決定我的工作調動,恰在我被批準參加土改學習中途,使我覺得很突然,后來方知組織部早有此決定,劇院當局拖延未執行而已。
調動不調動,在我都沒關系,主要是思想上解決問題,一切問題都可解決了。我很慚愧我的工作做的太少,多工農兵的打哈哈、思想感情體驗太差,對新人物的創造缺少把握,這是我目前最關心、急于下放的原因。年初我們曾有過兩個月的工廠生活,使我們這群知識分子有了很大的收獲。工人同志的集體性、主人翁感、對國家人民的負責態度、對未來充滿信心等,擴展了我們的心胸和視野,在大踏步前進的歡樂的隊伍中,確實覺得個人的事顯得多么不足道。
此次參加土改未成,預備到華東局去爭取參加,組織部也答應為我寫信去,多在生活里鍛煉改造自己。希望您將來在我拍的片子中能檢查我這方面的成績。過去您對我鼓勵過多批評太少,這是我向您提得意見。
在北京雖然很難見到您,但總覺得隨時可以見到您。現在離開北京了,覺得與您分別了,特向您告別問好,祝您健康!小超大姐好!

總理對我一直是很關心的,在重慶時,總理就是我的單線聯系人,我的組織關系一直到解放時都在總理那兒。那次我去西花廳,總理留我作了一次長談,我毫無保留地向黨組織坦露了我在感情生活上的困惑、煩惱,總理耐心地聽我講,在傾訴的過程中,我覺得自己的靈魂得到了一次凈化,我明白了要做一個共產黨的好演員,不僅政治上業務上對自己要求要嚴,在其他問題上也應該有共產黨員的好品格。
總理在重慶第一次和您談話時,就勉勵您做“共產黨的好演員”,那么這次總理又對您提了什么要求嗎?
總理對我一直是鼓勵的。
您到上影后,拍了不少電影,在影幕上留下從影以來的許多的第一個,第一個工人形象(1954年,在上影黑白故事片《三年》中扮演紗廠女工干部趙秀妹),第一個民兵形象(1952年,在上影與八一廠合拍的黑白故事片《南征北戰》中扮演女村長兼民兵連長趙玉敏),第一個母親形象(1956年,在上影黑白故事片《母親》中第一次扮演了一位革命母親的形象),還第一次演了個喜劇人物,就是《李雙雙》中的農村婦女李雙雙,得到了廣大觀眾的喜愛。
李雙雙是得到了觀眾的認可,這里也有好多因素。1959年后,全國各電影廠都有點不敢碰現實題材的影片,原因就是怕把握不好挨批,覺得還是拍歷史題材好,特別是古裝戲比較保險。《李雙雙》幾乎是當時唯一一部現實題材的影片。戲中主角李雙雙是個性格開朗、是非分明、熱愛集體的普通農村婦女,她一直斗爭的對立面也不是什么階級矛盾,而是鄉里鄉親,甚至包括自己丈夫身上的落后思想和處世方式。這樣的內容,誰也不知道會不會拍到一半就下馬,還是拍完以后再挨批?
現在的演員尤其是一些出了名的所謂大腕,常常可以同時接演幾部戲。而您為了演李雙雙,從1961年7月9日提前一個多月就開始投入到河南林縣的外景地,和當地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那樣的日子您覺得苦嗎?
《李雙雙》是部喜劇,但我們拍的時候,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最嚴重的時候,我們到河南林縣拍外景,印象最深的是,吃得很艱苦,幾乎一天到晚在喝南瓜湯和榨過油后的黃豆渣餅子。
從1961年開始拍攝到1963年影片獲獎,這期間《李雙雙》經歷過怎樣的曲折?聽說當年拍完后在廠里只是作為一個中等片子看待的?

《李雙雙》是1962年公映的。事實上,在拍《李雙雙》之前的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了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同時,文化部也在新僑飯店召開了全國電影故事片創作會議,會議研究貫徹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如何改進文藝工作領導等問題,史稱“新僑會議。”周總理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前一個會上提出《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草案)》,史稱“文藝十條”,后一個會上提出《文化部關于加強電影藝術片創作和生產領導的意見(草案)》,簡稱“電影三十二條”。在這次全國電影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特別號召電影要創“四好”,就是故事好,演員好,鏡頭好,音樂好。而故事好成為被著重強調的一個方面,這樣一來,“典型人物”的塑造,就成為電影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那就是既要把握政治上的平衡,還要在藝術上表演精湛。我們拍《李雙雙》的時候正好是在這當口,雖然說不上是“新僑會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可以把這部電影看成是這次會議精神正確的一個佐證。
“新僑會議”后,直到1964年,電影生產又掀起了一個不小的高潮,先后拍攝了一批好片子,如《甲午風云》、《阿娜爾罕》、《燎原》、《冰上上的來客》、《早春二月》、《紅日》、《白求恩》、《霓虹燈下的哨兵》、《農奴》、《英雄兒女》等等,還有好多。后來,被稱頌一時的“中國二十二大明星”,其實也是這個時候的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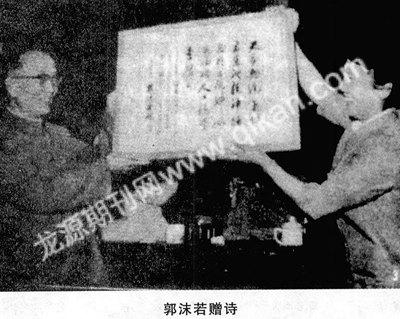
影片是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為背景的,在那樣嚴肅的時代背景下,卻用輕喜劇的手法來表現當時農村大量存在的人民內部矛盾,您演起來覺得有壓力嗎?
當年按照作者李準的要求,雙雙的性格就是要豁得出去,可是等我甩開膀子要豁出去的時候,導演魯韌首先就緊張了,不時地提醒我,悠著點,悠著點!當時我們大家的心態可以用“火燭小心”四個字來比喻,前提是寧可溫點,千萬不要因為強調喜劇效果而落得個“丑化勞動人民”的罪名(由紅代會北京電影學院井岡山文藝兵團、江蘇省無產階級革命派電影批判聯絡站、江蘇省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在1968年1月發行的《毒草及有嚴重錯誤影片四百部》中的批判詞為:抹殺階級斗爭,宣揚人性論)。因此在每個鏡頭前,到最后往往是采取最保險的方案,演起來真不爽,真是難受。好在影片公映前,拍了一段預告片,當時剛剛從學習畢業的吳貽弓在給導演做助理,他支持我放開來演,其中有一個鏡頭是雙雙又氣又恨的捶打喜旺,“打敗”喜旺后又哈哈大笑。后來影片中幾組喜劇味較濃的鏡頭,原本是作為預告片用的。
周總理也很關心、喜歡《李雙雙》。
總理和小超大姐都很喜歡《李雙雙》。1962年6月,我們帶著這部片子出訪日本,回到北京后,一天小超大姐約我去吃晚飯,總理見到我就說:“今天請你吃螃蟹,因為你拍了一個好戲。”我當時心中一喜,又不敢亂猜好在哪里?就試探著問:是不是正好配合了八屆十中全會以后的農村政策?總理有點不以為然地對我說:你不能完全這么看,這個影片在藝術上也是有可取之處的,你的表演也有新東西。聽到總理對我藝術上的肯定,真是讓我從心里感到欣慰!我演趙玉敏和趙秀妹時,總理就對我說:“你演了一個農民,又演了一個工人,都有點樣子了。”這期間,我其實也為扮演現實人物有過抱怨,抱怨吃力不討好,總理對我說:“演古人比演當前的人容易,因為沒有人見過他們。演現實生活里的人不容易,因為人人都能看出他像不像。”可以說,在李雙雙身上,我的演技可以說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因為在總理眼里,我一直是進步的。而觀眾對我的評價,就象總理說的那樣,結論是還算像的!
1963年《李雙雙》榮獲第二屆電影“百花獎”,說明您在李雙雙身上確實下了不小的功夫。
作為一名演員,努力演好每一個角色是最起碼的,也是應該的。《李雙雙》在當時能留下這么大的影響,和這部電影是那個時代少有的一部尚屬成功的現代題材影片有很大關系。不過,能獲得全國各地那么多觀眾的普遍贊揚,也是超出我的想象的。
記得那年我們帶著《李雙雙》來到上海郊區的莘莊人民公社。
聽說《李雙雙》來了,社員們興高采烈,很多人提前做好工作,紛紛趕到俱樂部,七八百個座位很快就坐滿了。在放映過程中,人們不斷發出暢快的笑聲,很多社員在劇場里就贊不絕口。看完電影,有十幾位社員又留下來談了不少感想。
這部反映我國農村人民公社新生活的喜劇片,受到社員們的同聲贊好。他們認為影片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主人公李雙雙熱愛勞動、大公無私一心為集體的思想品質,正是我國先進農民的集體主義思想的集中體現。通過影片,可以使廣大農民進一步認識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重要性,從而進一步調動農民的集體生產的積極性。有位社員說:“我看了一遍,還想再看一遍。為什么呢?因為這部電影生活真實,人物真實,演的就是我們莊稼人自己的事,看了很舒服。即使是落后的人物,我也要看。就拿喜旺來說,他愛勞動,只是因為有點怕吃虧的思想而不讓妻子參加修渠;他自己沒有損公利己的企圖,但對別人貪公家小便宜的行為,雖然看不慣卻又拉不開情面,不敢阻擋……像這樣的人,在我們社員里還是常碰到的。”
有的社員提出:“要向李雙雙學習!”認為雙雙有著先進農民的典型性格,她能堅持真理,不怕困難,不向落后勢力低頭,又勇于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電影開頭的一場戲,因為孫有婆拿了公社的幾塊桶板,雙雙就和她斗爭。有位社員說,李雙雙這種熱愛集體利益的行為真叫人敬佩。談到影片中評工記分的戲,大家發言就更熱烈了。一位女社員說:“我們生產隊評工分時,像影片中大風被批評、不高興轉身就跑的現象也有。記工分是容易得罪人的事,人家提議讓雙雙的丈夫喜旺來做,她不但沒反對,還動員喜旺當記工員。這樣高的覺悟是我們要學習的。”生產隊一位女干部:“雙雙當了婦女隊長,在評補助工分時,自己雖有困難,但堅持不要公家的補貼工分,這種大公無私的行為已經是很難得了,尤其是她反對給不愛勞動的副隊長金樵補助,更是了不起。在這點上,我們往往還存在著情面觀點。”
好幾位社員都談到,李雙雙的可敬可愛,還表現在處理家庭關系上。對丈夫她尊重、體貼,而在原則問題上卻毫不含糊,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幫助丈夫提高思想。有一位女社員談到自己的切身體會時說:“堅持真理,不遷就落后,真不容易!像雙雙就是因為對喜旺進行批評,喜旺趕大車去了,雙雙哭了。但最后是喜旺終于認識到錯誤,她勝利了。而我呢?鬧到丈夫差點要走,就再也硬不起來了。”說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
所以后來我們曾經戲言:現在的演員戲多,過去的演員觀眾多。在第二屆“百花獎”頒獎會上,郭沫若還給我題了一幅墨寶,郭老送我的詩句是:天衣無縫氣軒昂,集體精神賴發揚。三億神州新姊妹,人人竟學李雙雙。當年由郭蘭英演唱的電影插曲《歌唱李雙雙》也是風靡大江南北。有幾次,在北京的交誼舞晚會上,當這首樂曲響起的時候,總理總會向我走來,邀我共舞,這樣的時候總會引起全場的一陣歡笑。周總理一邊踏著舞步,一邊哼著《歌唱李雙雙》的曲調,還一邊說:“這歌詞不好記,幾段之間容易串行。”那樣的時候,可以說是我感覺最欣慰的時候。

拍完《李雙雙》后,您又忙些什么呢?聽說那段時間您獲得了一個綽號,叫“趙丹的政委”?
“新僑會議”之后的一年,是文藝界氣氛比較活躍的一年,也就是“文革”期間被重點批判為文藝黑線回潮的一年。拍完《李雙雙》回到上影劇團后,當時應云衛為劇團導演了夏衍的著名話劇《上海屋檐下》,趙丹導演了曹禺著名話劇《雷雨》。電影演員沒有攝制任務時就排演話劇,這是個老傳統,對內是為了不要荒疏演員的業務,對外則是觀眾特別喜歡近距離地看電影演員演話劇。我那時剛剛結束《李雙雙》的工作,就輕輕松松地去看《雷雨》的彩排。沒有想到很快得到局領導瞿白音的通知,要我隨話劇組立即去山東,擔任演出隊的領隊,還幽默地對我解釋,趙丹在藝術上“眾望所歸”沒有問題,但組織紀律方面有時連自己都管不住,還要有個人專門管著他,這個職務只有你能勝任了。于是我就當了一回趙丹的專職“政委”,隨團巡演,從那時起我就有了“趙丹的政委”的綽號。在山東演出時,我們總是被觀眾團團圍住,演出前、散場后,劇院門口常常造成交通堵塞,后來不得不警車開道,車門直接頂著劇院門口的臺階,演員們才能順利下車到后臺,否則就不能保證正點開演了。回上海后,我的“政委”任務完成了,《雷雨》開始在長江劇場上演,場場客滿。記得著名話劇導演黃佐臨看了電影演員們演的《雷雨》后,曾說過:你們能否到香港去演出呢?
《李雙雙》之后,您一直很忙,還拍了好些片子,但有的根本沒有和觀眾見面就直接進入了倉庫,比如《李善子》,廣大觀眾根本就不知道還有這樣一部影片。
這部電影是根據朝鮮的一部現代戲《紅色宣傳員》改編的。這也是我們與鄰邦朝鮮文化交流的一個項目,他們排演朝鮮版的《紅樓夢》,我們則排演中國版的《紅色宣傳員》,并且同時改編拍成五彩影片。《紅色宣傳員》講的是一位朝鮮農村姑娘李善子,熱愛集體,熱愛勞動,大公無私,帶領民青盟員,也就是民主青年聯盟,相當于我們的共青團組織,發展生產,幫助落后鄉親,最后奪取豐收的故事。

李善子好象和李雙雙很像,您演起來應該得心應手的。
1963年4月25日,周總理來上海開政治局會議,和其他中央領導一起來看我們的演出的話劇《紅色宣傳員》。總理對我們戲的評價是“戲很好,其他同來的同志也說好。”他認為我們的演出水平是高的。我們聽了都很高興。
1963年下半年,我們根據總理的建議,組成了中國電影工作者學習訪問團赴朝鮮,團長是鄭君里。當時主要是想通過拍攝現代版的《李善子》,學習朝鮮寫現代戲的經驗。去朝鮮之前,小超大姐還接見了我們,特別為我們定下了十六字方針,就是“謙虛謹慎,認真學習,客隨主便,時間不拘。”到了朝鮮,因為是中國的總理推薦的,所以我們享受到了很高的接待規格,連金日成主席也接見了我們。我們參觀了所有外賓參觀的項目,我們還要求到《李善子》的原型人物李信子的家鄉去看看,后來李信子出來和我們進行了一次座談。我們還和朝鮮電影《紅色宣傳員》的女主演宋英愛見了面。那次回國后大半年左右時間,由王煉編劇的劇本終于完成了,我就投入到正式的拍攝中。1965年,片子總算完成了,送北京審查。總理為審查這部片子,還特意調出鄭君里解放后拍的其他幾部片子,記得我們陪同看過的就有《聶耳》、《枯木逢春》等等,總理還對鄭君里說,你是不是太過于追求唯美主義了?有一次,總理又約我和鄭君里去西花廳。總理問鄭君里:江青同志看過影片了?她說什么?鄭君里沉吟了好一會兒才說:她說,你不能這樣下去了,再這樣下去就完了……總理聽他這么說,也就不再問了。
這部影片前后看過的人有:陳丕顯、曹荻秋、曹禹、歐陽山尊、康生、江青、周揚、陳伯達、劉白羽、司徒慧敏、田漢等,但各方權威人士只是看,卻聽不到他們的反映。我曾經單獨問過田漢同志,他也只是對我的表演作了個評價,說我演的李善子比他們演的更樸實。后來,總理還要鄭君里和我帶著片子到廣東找正在養病的柯慶施征求意見,他一見我們進門就對鄭君里說:這些年你就聽他們的,不聽我們的!柯老說的“他們”,當時我并不清楚是誰,只是不停地記錄著,生怕漏掉了一些重要指示。實際上這個“他們”指的是夏衍和陳荒煤,那時他們已經“靠邊”了。所以,這部片子又過時了。
那時候已是“文革”前夕了?
是的。當時國內政治已經開始全面醞釀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準則了。這部片子是人家朝鮮的原創劇本,改也不是,批也不能,再加上那時國際關系比較微妙,在當時“階級斗爭”的形勢下,還要講什么以情感人,互助、互愛和集體主義,似乎也太不搭調了,所以,這部電影也就無疾而終,被送進倉庫,連觀眾面都沒有見上。可以說,《李雙雙》之后,我一直在困惑中忙碌著,而不知道這一切都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總理為此還對我說過:瑞芳,對不住了,耽誤你兩年八個月。
這個時間怎么算?
因為我從話劇《紅色宣傳員》到電影《李善子》,整整忙碌了兩年零八個月。
粉碎“四人幫”后,我一下子又忙了起來,甚至比“文革”前還要忙。電影界和其他各行各業一樣,也是百廢待興。我除了拍戲,還多出來了許多其他工作,要招募、培訓新學員,指導大型舞臺節目、連續劇電視片、專題電影記錄片的編導和排演,參與廠里領導層的管理工作……此外,還多出來一大塊工作,就是頻繁的社會活動,從全國黨代會、政協,到上海市黨代會、政協,還有婦聯工作、外事工作等等,這些活動,對我是一種榮譽和責任,也是組織上對我的信任,所以我絲毫不能怠慢,必須恪盡職守。
前幾年您和親家一起搞了個養老院,在社會上反響很好,現在還在正常運作嗎?
正常開著,這都是我兒子和兒媳的主意。他們在國外經常去做義工,就是到一些養老機構去做志愿者,我兒子就想要把這樣的理念帶回國內。所以有機會我們就和親家一起開辦了“愛晚廳”養老院,盡管很累,也不賺錢,但是看到住在那里的老人都很開心,我們也很高興。
養老院是專對文化、文藝界人士開放還是向所有社會人員開放?
愿意住進來的老人都可以,沒有身份限制。只是地方太小了,滿足不了更多老年人想住進來的需求,不過,最近有人來談合作的事情。
這是好事啊,可以搞搞大了。您也經常去嗎?
經常去看看,和他們一起說說唱唱,大家都開心。
瑞芳老師,謝謝您接受我采訪,衷心祝您健康長壽。
謝謝!○
責任編輯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