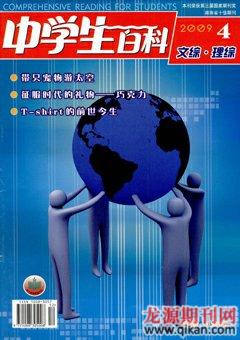四氯化碳的是與非
張 春
當森林火災發生而消防人員又尚未趕到時,并不是所有的樹木都只能坐以待斃。生長在非洲的一種“異類”——梓柯樹,就能在火災發生的第一時間內參與滅火。每棵梓柯樹都長有幾個大疙瘩,隱藏在樹杈間,上面布滿了密密麻麻的小孔。一旦遇到火光“刺激”, 梓柯樹就會發出指令,通過小孔把疙瘩里的汁液噴射出來,從而把附近的火“澆滅”。
梓柯樹的汁液之所以能滅火,是因為其中含有大量的四氯化碳。四氯化碳是種不助燃、不自燃的物質,并且沸點非常低。當溫度達到 76~77 ℃時,它們就會變成蒸氣。蒸氣狀態下的四氯化碳比空氣要輕很多,不容易逃散,而是會密集在火源四周,把正在燃燒的物質包圍起來,起到隔絕空氣的作用。得不到更多的氧支援,火焰自然就熄滅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梓柯樹的啟發,反正四氯化碳很順利地進入了滅火器,在大大小小的火災中扮演救星。不過現在,它已被趕出消防隊伍。光就滅火而言,四氯化碳是個能手,可它有毒,不僅僅是自己有毒,還能“生產毒”。 四氯化碳的化學性質本不活潑,對某些金屬卻有很強的腐蝕作用。毀壞點東西就算了,偏偏沒這么簡單。在高溫條件下,四氯化碳與赤熱的金屬相遇,會產生大量的光氣。在實驗室中要制取光氣,就是將四氯化碳與鹽酸反應。光氣是一種窒息性毒劑,傷害呼吸器官,引起中毒,甚至死亡。
人類對四氯化碳認識和利用,有確切記載的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早在1858年,德國化學家霍夫曼就意識到四氯化碳非尋常物,經常拿四氯化碳來做實驗。有一次,他在用四氯化碳處理苯胺時,無意中得到一種紅色物質,可以直接用來染毛發、絲以及棉織品。霍夫曼把這種意外制得的染料稱為堿性品紅。此后,他又在這個基礎上,相繼制得了多種合成染料,如堿性藍、醛綠、碘綠等等。因此,在合成染料的發展史上,四氯化碳算是有小小功勞的。
除了能滅火,四氯化碳還有個非常突出的特性,那就是能與多種有機溶液劑混溶,能溶解油脂、蠟、樹脂、瀝青、橡膠、精油以及磷、硫、碘等。如果用生活化的語言來概括就是:四氯化碳有著無比強大的去污能力。跟瀝青有過親密接觸的人應該知道,瀝青沾到手上或衣服上之后,想要用水和洗衣粉一洗了之真是非常困難,不過有了四氯化碳幫忙,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就像梓柯樹和人類拿它來滅火一樣,四氯化碳順理成章地被拿來做了清洗劑。
干洗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一種不用水的洗滌方式,讓有機溶液滲入到衣物中,把依附在紡織纖維表面的頑固污漬去除。在干洗技術處于起步階段的19世紀中后期,干洗用的溶劑是苯、煤油、汽油等,無一例外都是可燃性物質,因此常常造成火災。當時干洗店老板腦子里總裝著兩件事:一是怎么多掙錢;二是怎么防范不讓一把火把前面掙的錢給燒光。
直到1897年,干洗店老板才告別了整天提心吊膽的日子。這一年,一個德國人把四氯化碳引入到干洗劑中,把干洗技術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與煤油、汽油相比,四氯化碳的去污能力顯然更勝一籌,更重要的是它不會冷不丁就制造一場火災來折騰人。干上干洗活的四氯化碳也并非十全十美,有毒是一個方面,另外它還“吃機器”,對設備具有腐蝕性。不過正是由于它的出現,啟發了人們的新思路。1918年,歐洲開始改用三氯乙烯來取代四氯化碳。至此,干洗業才蓬勃發展起來。
雖然四氯化碳在滅火和清洗這兩件事情上都有過自己的輝煌,但都是短暫的。人們因為它的優點而“拿起它”,又因為它的缺點而“放下它”。用一句話來評價它在歷史上的功過,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任勞任怨的壞孩子”。現在,這個“壞孩子”的日子更不好過。人們恨不得用最堅固的籠子把它關起來,不讓它隨隨便便就混進空氣里。這一天的到來,是因為我們的天空不再健康,出現了“漏洞”,即被稱為天空之癌的臭氧漏洞。
臭氧層是地球的“保護傘”,是保護人類免受強紫外線侵害的天然屏障。破壞臭氧層的原因有很多,而四氯化碳是頭號殺手。自20世紀30年代起,每年排放到大氣中的四氯化碳達數千噸之巨,其中一部分是從干洗店里“逃”出來的,另外還有一部分來自空調的制冷劑(制冷劑中的氯氟烴以四氯化碳為主要原料),這給臭氧層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四氯化碳上升到平流層后,在紫外線的照射下,會分解出氯原子,而一個氯原子就可以破壞成千上萬個臭氧分子。由此帶來的惡果是,臭氧層出現漏洞,照射到地球上的紫外線越來越強。
如今,四氯化碳已經被禁止用做干洗劑,而是改用四氯乙烯等可以回收的化學物質,但為什么四氯化碳依然源源不斷地出現呢?這是因為四氯乙烯價格高,有些干洗店為了節約成本,便偷偷地用四氯化碳來代替。
編輯/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