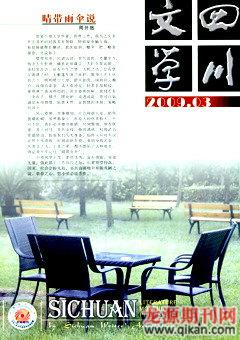度行天下(二題)
徐國良
寵度
星期天上午,朋友約我去釣魚。盡管我坐的吉普與他坐的奔馳極不協調地在山路上蜿蜒蛇行,但共同的愛好抵消了這種反差。
一行人剛及水庫邊坐穩,朋友那只身價上萬、渾身噴著香水氣名叫“賽賽”的獅毛狗便在草地上搖頭晃腦,扭腰撅腚,賣弄風情。
水庫下是一片如鏡的稻田。一位老農正吆喝著老牛掌犁耕耘,一對八哥在運動著的牛背上時起時落。幾只白鷺在田中悠閑尋食……這如畫般的田園風光被狗破壞了。那賽賽沖著犁田的老牛狂吠,兩只狗眼怒目圓睜,噴射著仇恨,聲音雖不洪亮卻透露著兇惡,令人聞之心悸。老牛從田埂西頭犁到東頭。它從西頭吠到東頭;老牛從東頭犁到西頭,它又從東頭吠到西頭。
老牛對聲聲狗吠充耳不聞,仿佛心靜如水。偶爾也抬起眼皮冷冷地斜一眼那叫得再兇卻總不敢下田的狗東西,依然默默地一步一個腳印躬身前行。掌犁的老農卻實在忍不下去了,厲聲斥責道:“你這光吃飯不干活的家伙,亂嚎什么!”
遭老農怒斥后,獅毛賽賽息聲片刻,見老農不罵了,又時斷時續地吠了起來。
眼前狗吠牛耕的場景。朋友似乎習以為常,我卻鈞興游移——這油嘴好閑專舔人腿馬屁、喜鉆婦人懷抱的狗家伙為什么要對默默勤耕在田間地頭的老牛如此憤憤然呢?人們為啥對不干活者犯擾干活者的行為又無動于衷呢?對以奉獻為本的老牛冷漠,對什么事都不干的狗類寵愛甚至視為“心肝寶貝”——這種愛的錯位和顛倒,將給人類帶來多少情感的誤區喲!
由此,我想到了都市鼠害。這些年,隨著人們日趨豐衣足食,不少人把剩余精力轉到了寵貓身上,貓亦身價倍增。主人不僅給它們買魚買蝦買肉食,還為它們洗澡洗臉灑香水,甚至帶上床與人同枕共眠。貓們吃飽喝足睡沙發躺席夢思,還用得著日夜辛苦站崗蹲點潛伏守隙待鼠嗎?貓不“上班”,鼠孽必然肆無忌禪招搖為害。鼠害越重——人們越去寵貓——貓價越長——貓越受寵——老鼠越多。如此惡性循環,貓成了寵中極品,老鼠成了遍地“風景”。不管白貓黑貓,都成了不咬老鼠的寵貓。
有天,朋友在床頭捕獲一只母鼠,將其打傷后放在貓的嘴邊。貓竟不知斯為何物,一陣嘻嘻哈哈之后,便與之親吻,與之調情。在挑逗戲鬧中,老鼠恢復了元氣,逃之夭夭。貓兒戀戀不舍地目送了許久,才怏怏地回到電視機前的沙發上,伸個懶腰,聳聳肩膀,盤腿坐觀人間的愛情武打新招。但電視機里總不見剛才那腰圓腚肥的鼠妹出現,很是掃興,不久便哈欠連連,鼾聲綿綿了。
悲哉!貓已失去貓性,貓已不諳貓業、貓職——貓已不是貓了。我真擔心不知道哪一天,貓們會被老鼠吃了去的。
由此,我再想到保護區內的獼猴。猴們本是棲山食野之物,在風餐露宿中一代代繁衍生息并磨煉出了對疾病和自然災害的免疫抵御能力。不幸的是,近些年人們的寵猴之舉已經可怕地改變了獼猴幾千年的生存本能,使其由自食其力的獵食者蛻變成了坐等嗟食的美味洋餐者,且愈來愈驕橫無忌,時有游客因給食慢了而遭猴們撕咬。70年代初還經常下山采擷野果的猴們,到了80年代已經懶得下山,每天坐食游客和管理人員送上的美餐。90年代以后。它們對地瓜一類土食品已不感興趣,更中意于經過人類精心加工制作的糖果、餅干、糕點。吃得口干舌燥,山中的泉水已是不愛喝了,硬要從游人手中搶奪瓶裝果汁以及各種礦泉水。游人稍有怠慢,輕則口中“嗷嗷”怨聲連連,重則齜牙咧嘴扯衣奪包。
從尋覓野食到坐待嗟食,進而挑揀現代美食,猴們的確以其聰明的進步給人帶來了樂趣。可在這些樂趣之后,猴們原生素質的退化、與疾病和自然災害抗爭能力的弱化,甚至有感染人類傳染病毒而夭折的危險,人們可曾想過?這種日益退去了猴性的猴們在人類的精心保護下就算生存繁衍日益壯大,對于生態平衡,對于動物進化又有什么意義呢?倘若遠古的猴子受到這種保護,還會產生今天的我們——人嗎?
近日讀報,得知有些國家有些地方已將人工養育了多年的猩猩等動物放歸原始森林,讓其返璞歸真,實乃科學之舉。
我不是生物學家或動物學家,我僅從感觀直覺所思,吁請人們樹立正確的寵物觀,不要只顧自己好玩,要多想想寵物給動物和人類帶來的危害和災難!那種貌似以人為本實則以狗(或貓等)為本的事在當代人的生活中屢屢發生:清清靜靜一層樓,忙忙碌碌幾戶人,他偏要養一只愛叫的狗,深更半夜狗吠聲聲,害得左鄰右舍睡不好,上班沒力氣,開車打瞌睡,飲食乏味,精神恍惚,他還以保護動物為名,遲遲不愿送走這廝;干干凈凈一池水,男男女女游正歡,他偏要帶只狗下去與人同游,還振振有詞地說,動物也需要運動,為什么不能與人同泳;漂漂亮亮一大堂,杯杯盞盞酒食酣,他卻把一只貓抱上桌與客同餐……不管社會如何發展,文明如何進步,人與動物總是有區別的。如果弄得人和貓狗沒有任何區別,甚至人不如貓狗,這就不是社會的進步,而是社會的悲哀了。
不可否認,寵愛是人類的一種心理和情感需求,不管是寵物還是寵人。但凡事須有度,寵亦有度,倘若寵而無度,結果便是異化。由此,我又想到了國人對子女特別是對獨生子女的寵愛。是否可以再做些深層次的思考呢?國外許多有識之士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為我們樹立了“寵度”榜樣。
美國的家長不管家里多么富有,要求男孩子12歲以后就給鄰居或自己的父母剪草坪、送報紙,賺些零用錢,女孩子則做小保姆去賺錢,讓孩子們從小認識勞動的價值。美國南部一些州立學校為培養學生獨立生存,適應社會的能力,還特別規定:學生必須不帶分文獨立謀生一周,方能予以畢業。條件似乎苛刻,卻使學生們獲益匪淺。沒有一位家長拖后腿、走后門、搞小動作。
加拿大父母為了培養孩子在未來社會中的生存本領,從很早就開始訓練他們獨立生活的能力。在一個記者家中,兩個上小學的孩子每天早上要去給各家各戶送報紙雜志。看著孩子興致勃勃地分發報紙,當記者的父親感到很自豪:“分這么多報紙雜志不容易,很早就起床。無論刮風下雨,都要去送,可孩子們從來都沒有耽誤過。”
在瑞士,父母為了不讓孩子成為無能之輩,從小就培養他們自食其力的精神。譬如,對十六七歲的姑娘,初中一畢業就送到有教養的人家去當一年女傭,上午勞動,下午上學,既鍛煉了勞動能力,又有利于學習語言。因為瑞士有講德語的地區,也有講法語的地區,所以這個語言地區的姑娘通常到另一個語言地區當傭人。
德國法律規定,孩子到14歲就要在家里承擔一些義務,比如要替全家人擦皮鞋等。這樣做,不僅是為了培養孩子的勞動能力,也有利于培養孩子的社會義務感和責任感。
日本人教育子女有句名言:“除了陽光和空氣是大自然賜予的,其它一切都要通過勞動獲得。”許多日本學生在課余時間都要去校外參加勞動賺錢,有錢人家的孩子也不例外。日本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給他們灌輸一種思想:不給別人添麻煩。全家人外出旅行,不
論多么小的孩子,都無一例外地背上一個小背包。有人問這是為什么,父母說:“他們自己的東西,應該自己來背。”
我國改革開放整整30年了,外國人的生產經、生意經、管理經學了不少。外國人的瀟灑享受、自由浪漫、乃至性開放也學了不少,可這外國人教育孩子的科學方法似乎學得不多。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來看,不管學習什么科學,首先要學習培養人的科學,這是最根本、最基礎的,忽視了這個根本和基礎,其它一切先進的東西都是靠不住的。大唐盛世的沒落,大清帝國的垮臺,都是因為忽視了科學育人。如今全國上下都在提倡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千萬別忘了解放教育子女的思想。忽視了這個解放,不僅改革開放的成果難以鞏固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強盛也將成為一句空話。
奴度
在人類歷史上,奴隸是經過了長期的殘酷的階級斗爭,才徹底推翻了奴隸制。但社會發展到今天,有些人還是奴性難改,心甘情愿地做著沒有奴隸制度的形形色色的現代奴隸:房奴、車奴、股奴、網奴、卡奴、兒奴、藥奴、節奴、貓奴、狗奴、鳥奴、豬奴、守財奴……使自己的生活充滿奴性。
別人發了財,買了名車,換了新宅,當然感到幸福快樂。于是他也打腫臉充胖子,從正常吃的、用的,甚至兒子的奶粉中擠出錢來,買回了一臺臥車。自從買了車后,夫妻的早餐都省掉了,節省的錢還不夠給車加油保養。這樣就是開著車上路,能有多少真正的幸福感呢?別人發了財,住進了復式樓,他也東借西湊住進了新建的小區。可是,每天早晨門一開,就要想方設法應付前來討債的人。他說沒錢,鬼才相信沒錢的人能住上這么好的房子!那種借錢過日子、住新房的感覺能幸福嗎?我們為什么一定要犧牲自己真正的幸福,當車奴、房奴,去點亮別人眼中的光環呢?
我們每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本該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尊嚴和操守,本該用自己的生活方式過自己追求的好日子,為什么要跟著別人的感覺走,別人做什么,一定要跟著去做呢?當然,如若跟著別人去做好事善事,也是一種積德行善之舉。可許多時候是因為別人說好,我們并沒有覺得好,就盲目地跟著別人去做。這實際上是做了別人的奴隸,讓別人的感覺左右了自己的行為。我們為什么不根據自己的愛好和追求,干自己想干的、能干的、開心的、快樂的事情呢。
就說這節日吧,如果全世界各民族統統都過一個節日,還叫什么各族人民,不就成了一族人民?正因為每個民族都有本民族的文化、風俗、節日,這才使得此民族區別于彼民族。節日也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我們中華民族的中秋節、端午節雖然很有意義,很有文化底蘊,可西方人從來不過。他們認為這是中華民族的節日,應由中華民族獨享,和他們沒有關系。除非到了中國,才會入鄉隨俗地隨著我們樂一樂。可我們為什么非要跟著洋人過許多洋節呢?不管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節日,只要好玩,能創造機會玩,很多中國人就去湊熱鬧。根本不問這個節日有什么來歷、什么意義。一到情人節、圣誕節、愚人節、狂歡節、復活節、感恩節……不少中國人比外國人更傾情,更瘋狂,更通宵達旦,更奮不顧身,不少人已經成了洋節的節奴,你說蠢不蠢?
還有那些貓奴狗奴寵物奴。他們和朋友在一起,不是交流工作經驗、切磋家庭建設、談論世道人心,而是匯報自家的貓們狗們的生活狀況,交流發生在貓狗身上的奇聞趣事。沒有故事的,挖空心思也要編造一點。好讓大家樂樂。他們每天下班,不是親配偶、親孩子,而是向撲上來的狗們貓們伸出雙手,還萬般親熱地呼喚:“寶貝。媽媽(爸爸)抱抱你。”每天上街,給人買吃的要反復砍價,省了又省,給貓狗等寵物買吃的半點都不小氣。路邊討飯的人把手伸痛了,也舍不得給一毛,給貓狗買吃買穿,花多少錢都不心痛。鄉下親戚來家睡一晚,人家一走立馬洗凈床單被套,貓狗上床與人共眠卻從不嫌棄。出差開會為了照顧貓狗,情愿不乘飛機擠火車乘汽車。半路出了車禍,不問人怎樣,先看貓狗傷著沒有。自己感冒發燒了,硬扛著不去醫院,貓狗若打了個噴嚏。就擔心它不舒服,急忙抱去看寵物醫生……一旦當上了貓狗等寵物的奴隸,日子竟過得連貓狗都不如了。
我們為什么不讓自己的日子過得輕松一點,非要找那么多狗呀貓呀鳥呀甚至豬呀來“奴”住自己呢?有人說厭惡了人世間的人情冷漠,爾虞我詐,在這些畜生身上能找到人身上找不到的真情和坦率,尤其欣賞狗對主人的忠誠。可是,狗對主人再忠誠,我們能靠狗來過日子?能指望狗來養家活口、安身立命?能靠狗來建設國家?如果我們把花在狗身上的金錢和精力用到人身上去,不是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更有利嗎?
另外,我們也應反思一下,狗為什么對主人忠誠,還不是因為我們對它好,給它吃,給它住,哺養了它們。倘若不是你家養的,看看它能對你好嗎?不咬你才怪!想想我們對人的態度,真是比對狗苛刻。譬如我們養育兒女,就希望他一定要讀好書,然后考上大學,還要是重點;參加工作首先要占到一個有錢有權的崗位,即使當不了大官,也要爭取弄回大把的鈔票……這些要求,你會加諸于狗嗎?
既然我們對待人遠比對待狗苛刻,怎能怨恨人情冷漠,怎能責怪人間沒有真情呢?我們在責怪別人時,應該認真反思自己,我們對待自己的同類是否真誠無私了?
我們許多人之所以對狗親熱對人冷淡,喜狗而厭人,不過是因為狗對主子惟命是從,絕對不可能有自己的獨立意志。這便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奴性,正與它的主人以及一切“奴”們的秉性吻合。拒絕獨立性,不喜歡自由意志,崇尚盲目跟從,正是這些人共同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觀正在向社會各領域蔓延。比如一些單位領導在用人問題上就喜歡惟命是從的奴才,導致許多年輕人不是立志成才,而是立志成奴,不是向人才學習,而是向奴才學習。這是很可悲的。這種唯奴是取的用人觀,別指望能干好事情。
凡事均得有個度,即便是喜歡順從,也要有個底線。有個例子可以為我們提供參考:二次大戰時,美國駐菲律賓的總統軍事顧問麥克阿瑟手下有個叫艾森豪威爾的將官要求調走,麥克阿瑟開始舍不得他走,最后還是忍痛割愛了。麥克阿瑟的妻子問丈夫為什么不以軍人的命令留住他,麥克阿瑟袒露了自己的用人觀:“艾森豪威爾是個人才,卻不是奴才——我既要人才,也要奴才。人才有用不好用,奴才好用沒有用,最好是人才兼奴才。”在現實生活中,才氣和奴氣兼備的人不多,但麥克阿瑟的用人觀為我們如何限制奴度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如果沒有自己的獨立精神和見識才干,光有奴氣而無本事,貌似好用,其實是最沒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