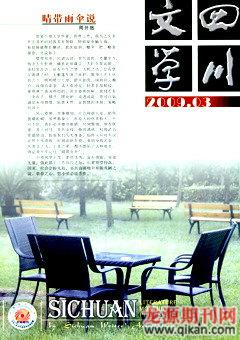茶事三題
秦志豪
柔茶似柴火獵獵
說到茶,人們總會最先想到天真動人的采茶女或綠樹水畔優(yōu)雅的品茶人,可誰會料到這細(xì)柔的葉片卻是一粒粒火種,而那清香悠遠(yuǎn)的茶湯也像一觸即燃的烈油?這便是我國歷史上唯一由茶農(nóng)發(fā)起的農(nóng)民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
王小波原是蜀州青城縣農(nóng)民。以前普遍認(rèn)為,這一帶是著名的產(chǎn)茶區(qū),茶農(nóng)不種五谷只種茶,與耕田的農(nóng)民一樣交稅,宋太宗時,實行“榷荼”法(即政府對茶葉實行專賣),大批“采茶貨賣,以充衣食”的茶農(nóng)因而失業(yè)。宋朝的官員由此大肆貪污勒索,地主商人從中投機取利,富者更富,貧者更貧。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遭受殘酷壓迫的旁戶、(又稱佃客,是一種投靠戶,世代相承,被豪民“役使之如奴隸”)破產(chǎn)的農(nóng)民和失業(yè)的茶農(nóng)等約一百人,以王小波為首在青城發(fā)動起義。
不過現(xiàn)從大量史料看,宋太祖、太宗時期,政府對川峽地區(qū)的蜀茶沒有禁榷。當(dāng)時政府對蜀茶的基本政策是“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北宋中期成都人呂陶也說得相當(dāng)清楚,他在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先后擔(dān)任蜀州通判、彭州知州、梓州轉(zhuǎn)運副使、成都轉(zhuǎn)運副使等地方官,不僅熟悉蜀茶的沿革,還很關(guān)心茶法。他在熙寧十年(1077年)三月的奏疏中寫道:“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種茶,”“自來采茶貨賣,以充衣食。”
茶農(nóng)們無論是自耕或佃耕,生產(chǎn)的茶葉,“乃百姓己物”。自己都可以處理,只向官府交納賦稅。這也就是《文獻(xiàn)通考》所說的“民賣茶資衣食,與農(nóng)夫業(yè)田無異”。從淳化到天圣、皇佑年間,北宋朝廷對茶法的計議頻繁,先后采用了許多辦法。然而這段時間,蜀茶一直沒有禁榷,只許蜀茶在川峽境內(nèi)“聽民自買賣”,不得自行輸出川峽地區(qū)。這是宋統(tǒng)治者以茶易馬和防止“邊事”的需要。
蜀茶的禁榷開始于熙寧年間。《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說:“蜀茶舊無榷禁,熙寧間始令官買官賣,置提舉司以專榷收之政。”而這時在全國原禁茶地區(qū)卻已廢罷禁榷。正如呂陶所說:“今天下茶法既通,而兩川獨行禁榷。”可見起義在前禁榷在后。但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王小波起義之時雖然宋政府對川峽茶葉沒實行榷禁,但當(dāng)?shù)毓賳T為了私利卻效仿榷禁地區(qū)牟取暴利。
從宋代的文獻(xiàn)記載,結(jié)合學(xué)者在灌縣的實地調(diào)查。可以看到當(dāng)?shù)刎湶璧牟粌H有茶商、茶販,更多的是茶農(nóng)。他們自種、自運、自銷,既是茶葉的生產(chǎn)者,又是茶葉的運輸者,也是茶葉的販賣者。但不管怎樣,王小渡和最初起義的參與者是茶農(nóng)無異議。起義后他們很快攻克青城縣。接著,直插彭山,懲殺了貪暴恣橫的縣令齊元振,眾至一萬余人。此后,轉(zhuǎn)戰(zhàn)于邛州(今四川邛崍)、蜀州(今四川崇慶),所到之處,令鄉(xiāng)里富人大姓報其家所有財粟,除留其家用外一切調(diào)發(fā)分給窮人,得到群眾擁護(hù),隊伍增到數(shù)萬人。十二月,起義軍在江原縣(今四川崇慶縣東南)與官軍激戰(zhàn),王小波被西川都巡檢使張玘射傷。仍奮力殺死張玘,攻克江原。王小波終因傷重犧牲,其妻弟李順被推為領(lǐng)袖。這次起義在中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的均貧富口號。
由此可見,茶,也能讓人品出不平則鳴的豪爽性格和英雄氣概。
最思雪水泡茶飲
想用雪水泡茶的念頭不是來自茶論專著,而是始于很早以前讀《紅樓夢》。
在小說第四十一回上節(jié)“櫳翠庵茶品梅花雪”中,賈母等人酒足飯飽來到櫳翠庵,妙玉在花木繁盛的小院為賈母用舊年蠲的雨水在官窯脫胎填白蓋碗中泡上老君眉后:
便把寶釵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她出去,寶玉悄悄隨后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nèi),寶釵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tuán)上。妙玉自向風(fēng)爐上扇滾了水,另泡一壺茶。寶玉便走了進(jìn)來,笑道:“偏你們吃體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趕了來飺茶吃。這里并沒你的。”當(dāng)妙玉邊說邊笑用不同的器皿為寶黛二人斟了茶后執(zhí)壺來到寶玉面前,只向海內(nèi)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xì)細(xì)吃了,果覺輕浮無比,賞贊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的茶是托他兩個福,獨你來了,我是不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領(lǐng)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是了。”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么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嘗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浮,如何吃得。”
你看這雪水泡的茶,不說茶具的精,環(huán)境的美,只看品茶人的天真情態(tài)和率真語言,怎不讓人心動意牽?
《紅樓夢》中提到茶的地方不少,似乎每飯必茶,每聚必茶,有名字的茶就有:六安茶、老君眉、龍井、楓露、普洱茶等。對泡茶之水也評述的不少,對泡茶的器皿也可謂極盡渲寫。但這“櫳翠庵茶品梅花雪”的“雪水茶”卻在我心中留下了一個情結(jié)。
讓這個情結(jié)復(fù)蘇的是后來讀《金瓶梅》,書中雖提到不少茶,但都不是真正意義上我們所說的,多是花果茶,如什么胡桃茶、松子茶、蜜餞茶、木樨芝麻薰筍茶等等,但在第二十一回卻寫了吳月娘掃雪烹茶一節(jié)。記憶中西門慶一家總是勾心斗角相互傾軋,而這一回寫月娘掃雪烹茶,卻將書中極少的和諧場面推到了頂點。因而更思念能喝一杯雪水泡的茶。可惜所居成都四季溫潤很難見雪,有時雖見雪花飛揚但落地即溶,哪還能積一杯水來泡茶?
直到有一年,這個愿望終于實現(xiàn)了。
那是一個星期天,一早在床上就覺異樣,起床打開陽臺門一看,女兒墻上居然積有幾毫米厚的雪。于是一聲驚呼,把老婆女兒全部喊起來。拿出一個不很大的白瓷盆,一起動手小心翼翼抓不沾灰塵的雪,居然弄了一小盆。一上午女兒都不時報告雪溶的程度,那等待的心情可謂難以言表。后來雪終于溶化殆盡,便將雪水倒入水壺,燒開后注入投了茶葉的雙龍杯。看著這杯雪水泡的茶,雖覺得少了點掃雪的雅趣,但畢竟釋解了心中雪水泡茶的癥結(jié)。淺淺啜一口,覺得與尋常水所泡并無什么區(qū)別。深深抿一大口咂巴幾下吞入腹中,也無讓人回腸蕩氣的感覺。郁悶良久,自言自語道:可能現(xiàn)在污染大了,這雪已不是從前的雪了?
若能天公作美巧遇大雪,一定再炊雪烹茶細(xì)細(xì)品之。
蒙山歸來憶茶香
初游蒙頂山,全是因為茶,因為那“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的名句。后來才知這頗具煽動性的詩句最早出自元代李德載的小曲《蒙山頂上春光早》:“蒙山頂上春光早,揚子江心水味高。陶家學(xué)士更風(fēng)騷,應(yīng)笑倒,銷金帳,飲羊羔。”
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在《琴茶詩》中說:“琴里知聞唯淥水,茶中故舊是蒙山。”把蒙山茶與古名曲并列稱頌。黎陽王的《蒙山白云巖茶詩》中說:“若教陸羽持公論,應(yīng)是人間第一茶。”清代名士趙恒的《拭蒙茶詩》,對蒙山茶更生動形象地加以稱道:“色淡香長品自仙,露芽新掇親手煎。一壺沁入詩脾后,夢醒甘回兩頰涎。”據(jù)載,蒙頂茶始于西漢,距令已有兩千多年。從唐朝開始被列為“貢茶”,一真沿襲到清末。蒙山貢茶又分為“正貢”與“陪貢”:每年春茶采摘時,由地方官擇吉祥之日,率領(lǐng)鄉(xiāng)紳僧眾。祭拜神靈,然后按夏歷周歲天數(shù),采芽葉365片,精制成“正貢”茶,專供皇帝祭祀宗廟之用;“陪貢”茶則制28斤,只供皇帝享受。
蒙頂茶之所以享有經(jīng)久不衰的盛名。首先在于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蒙山位于名山縣西部,與雅安接壤,由上清、玉女、井泉、甘露、菱角等五峰組成。諸峰回峙,狀若蓮花,山勢巍峨,峻峭挺拔,常年細(xì)雨蒙蒙,煙霞滿山。古籍記載:“蒙山上有天幕復(fù)蓋,下有精氣滋養(yǎng)。”清代康熙年間名山知縣徐元禧的《竹枝詞》非常形象地道出了蒙山變幻多端的云霧特征:“蒙山之巔多秀嶺。惡草不生生淑茗。剛得曦陽來借照,陰云又已漫空生。”
其實蒙山茶好除了自然環(huán)境和制作工藝外,還因為一個凄美的傳說:
很古的時候,青衣江有條仙魚,經(jīng)過千年修煉化成了美麗的仙女。仙女扮成村姑,在蒙山玩耍,拾到幾顆茶籽。這時正巧碰見一個砍柴的青年吳理真,兩人一見鐘情,魚仙將茶籽贈給吳理真訂了終身,相約來年茶籽發(fā)芽時,魚仙就前來和理真成親。
魚仙走后,吳理真將茶籽種在蒙山頂上。第二年春天,茶籽發(fā)芽了,魚仙出現(xiàn)了。兩人成親之后,相親相愛,共同勞作,培育茶苗。魚仙解下肩上的白色披紗拋向空中,頓時白霧彌漫籠罩山頂,滋潤著茶苗。茶樹越長越旺。魚仙生下一兒一女,每年采茶制茶,生活倒也美滿。
但好景不長,魚仙偷離水晶宮私與凡人婚配的事,被河神發(fā)現(xiàn)。河神下令魚仙立即回宮。天命難違,魚仙只得忍痛離去,臨走前囑咐兒女要幫父親培植好滿山茶樹,并把那塊能變云化霧的白紗留下,讓它永遠(yuǎn)籠罩蒙山,滋潤茶樹。吳理真一生種茶,活到80歲,因思念魚仙,最終投入古井而逝,后被人尊稱為茶祖。
品飲這樣的茶,何止是一個“香”?
從蒙山歸來已十余年了,城中的茶館不少,賣茶的商店也多,茶的品種檔次應(yīng)有盡有,但總也找不到蒙山茶中那難以言說的意境……
本欄目責(zé)任編輯:張即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