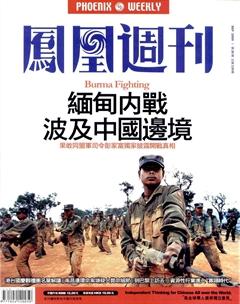吳祚來:到巴黎上訪去!
吳祚來
來自安徽的女大學生李蕊蕊,因在學校遭遇不公正對待,便上訪北京,還沒有向有關部門提交申訴,就被關進了‘詼賓館”(北京聚源賓館),6小時后即遭到強暴,而涉嫌施暴者正是賓館的“看守”。案發之時,已有70多名各地來京的特殊“住戶”被帶進賓館,擁擠于這家毗鄰北京火車南站的灰色院落內的簡易房里(8月6日《南方周末》)。一個女孩子,獨自來京,因為對北京的向往與信任,她相信北京能還給她一個公正,或者給一個說法。但遺憾的是,她得到的是人生的大災難。
灰色的賓館屬于“民間”,涉嫌強奸的小強的身份也是“民間”,有關部門任由民間力量“擺平”李蕊蕊們,北京因此失去了一次伸張正義的機會。正義之旗在北京上空飄揚,但李蕊蕊們抵達不到旗幟之下,分享不到旗幟帶來的正義之光。這一切,都是一種極度的為穩定而穩定的思維造成的,為穩定而讓正義停留在憲法上,讓追求正義的人,永遠走在歧路上,維護穩定的人,也因此走在歧途上。并不想就這個事件深入談下去,但我倒是聯想起發生在18世紀異域的一些故事。今天說起來,似乎仍具深義。
1762:到巴黎上訪去!
1762年5月9日,中國的乾隆皇帝對兩淮巨商獎賞之后,就回到自己書房批閱各地來的奏章,然后開始鋪紙寫詩,每天不寫上一兩首詩,他就無法入睡。但他對詩歌的愛好,并不能代表他對文化人的寬容,文字獄在他的手上,一點不少于他的父親與祖父。順便說一句,還是這一年,大清在新疆設立總統伊犁等處將軍,治地在惠遠城(現在新疆伊犁的霍城縣)。
太陽照臨東方以后,又開始照臨西方,夜幕在東方降臨后,又開始在歐羅巴大地上彌漫。
也就在這一天,遠在法國一座小鎮圖盧茲,吃完晚飯后的讓·卡拉斯一家,災難卻悄然降臨。卡拉斯的大兒子自殺了。這個兒子與父母有不同的信仰,因為不信仰天主教,所以他無法獲得律師準入資格。一次賭博失敗后,抑郁寡歡的他感覺生命沒有任何意義,就自盡于家中。無端的傳言卻使這個家庭更添屈辱,鎮上的人們認為,是卡拉斯一家人合謀殺害了有不同信仰的兒子,傳言在小鎮上肆虐,讓絕大多數人深信不疑,也讓大多數法官確信。
這是怎樣的一座小鎮呢?
他們每年都要舉辦一次節慶,紀念他們曾經在兩個世紀前的那一天,屠殺了4000名信仰新教的公民。他們以屠殺異教徒獲得的“勝利”為自己的驕傲,他們一年一年地慶賀并炫耀。盡管法院公布決定嚴禁紀念這種丑惡的節日,但圖盧茲居民仍然將其視同自己的賽詩會。這樣的群體在一起,仍有著強烈的嗜血的狂熱,他們看到卡拉斯一家的災難,以為是神降臨給他們的另一次機遇,要通過審判將卡拉斯處以車裂死刑,以紀念他們即將到來的節日。
這是一個對異教、對異端思想絕不寬容的時代,從民間到宮廷。也就在這一年夏天,巴黎高等法院將《社會契約論》與盧梭的另一部著作《愛彌兒》當眾撕成碎片焚燒,還下達逮捕令,緝拿盧梭。
盡管有法官根據現場偵查記錄不認可卡拉斯一家有罪,但最終的判決結果卻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愿望,時年68歲的老66歲的老卡拉斯被處車刑,法官們希望通過嚴刑逼供使老卡拉斯認罪,沒有得逞。在劊子手行刑的時刻,老卡拉斯不但不承認自己有罪,還替劊子手祈禱,愿主赦免這些無知人的罪行。這卻使劊子手與法官們大為驚駭,使他們不得不改變對卡拉斯家人的判決,盡管對卡拉斯家人的判決有悖于法理。因為如果卡拉斯一家人合謀殺害了長子,那么都應該視為同罪。
卡拉斯的鮮血濺滿卡拉斯夫人身上。這位突遭劫難的夫人一無所有,次子被流放,女兒被強行關進修道院,家產全部沒收。孑然一身的夫人走投無路。但還是有路見不平要伸張正義的人,他們積極支持卡拉斯夫人到巴黎去親自向國王申冤。這位來自英國的婦人,聽到巴黎的名字都使她膽戰心驚,省城如此險惡,到了都城又將面臨怎樣的險境?她只有抱著赴死的心理,去巴黎上訪。
無論宗教掀起怎樣的狂熱,巴黎的法律體系還是保持著自己應有的理性與正義。
巴黎最高法院著名律師德·博蒙先生親自為她辯護,并且起草了一份判決書,征得15位律師簽名,后又有兩位大律師加盟,將他們的辯護詞出版發行,將收益用于對卡拉斯夫人的資助。整個巴黎與歐洲都被感動,表現出巨大的同情心,支持這位夫人討還公道。基于理性與法律的新民意形成強大的潮流,使人們相信正義將通過法律回到世間。
到巴黎上訪,曾是卡拉斯夫人的恐懼,但巴黎卻用法律與理性還有同情心,使卡拉斯夫人得到了愛與公道。當公義回到卡拉斯夫人心中,巴黎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正義與恒久的尊重。民間的吁請直接進入國王的內閣,將女兒、兒子重新還歸母親,一家3人得到重聚團圓,大法官為他們流淚,整個巴黎何嘗不淚流滿面?
還是那座小鎮,那座陷入宗教迷狂的小鎮,用宗教情緒影響公正審判的小鎮,卻發來異樣的聲音:與其讓當時錯判的朗格多克8個法官陷入不義,不如讓卡拉斯一家繼續受辱,應該將卡拉斯一家人獻祭,以維護當地法官的榮譽。
伏爾泰說:他們沒想到,法官的榮譽如同其他人的榮譽一樣,在于糾正自己的錯誤。
巴黎上訪使法國歷史上少了一份冤假錯案,不,少了不止一份冤假錯案。如果這樣的錯案堂皇地記錄在法制史上,就會有更多的冤假錯案接踵而至,使巴黎應接不暇。如果巴黎人對卡拉斯夫人沒有同情心,巴黎的著名律師、法官對冤案置之不理,或推到當地政府解決,那么,它的結果可能不堪設想。為一個人主持公義,就是為全體人主持公義;為一個人主持正義,就是為城市、為國家、為歷史,甚至為人類主持了正義。
伏爾泰沒有花時間去思考法制的建設與信訪制度的建立。因為法律在當時似乎并沒有問題,相對獨立;信訪也沒有問題,即便是國王在強權統治。因為律師與法官在相對獨立地審判,不關國王什么事情,也沒有造成王國巨大的不穩定。
伏爾泰因此思考了什么問題呢?
關于“寬容”。造成一個城鎮迷狂的,是宗教不寬容,造成卡拉斯家庭冤案的幕后真兇,伏爾泰還認為,是不寬容。因為宗教不寬容,造成了歐洲大地上普遍存在的殘殺與暗殺,“劊子手磨刀霍霍,而教派卻不斷增多,盛怒代替了忍耐,人們也學會了敵人的殘忍,九次內戰使法國殺戳荼毒,尸橫遍野”。伏爾泰接著質問:“有些人斷言,人道、寬容和信仰自由都是可怕的東西,但是,說老實話,它們造成過上述那些可怕的災難嗎?”
這位思想大師、法國先賢,埋下頭來,寫就一本書,就是匯入世界名著系列的《論寬容》。這本書扉頁上寫著,“為讓·卡拉斯身故而作”。通過這本書,他要人們與他一起思考:宗教是應當仁慈寬厚,還是殘忍狠毒?今天的法國,伏爾泰與盧梭都被敬供在先賢祠中,而當時的國王路易十五卻將其視為自己的敵人。這位殘暴的國王曾對伏爾泰怒不可遏:“難道不能讓這個人閉嘴嗎?”正是統治者的殘暴,才引發了暴力與革命而不是提倡寬容與信仰自由的伏爾泰。
法國有革命的洗禮,用革命者與反革命者的鮮血來洗。當統治者血腥殘暴的時候,我們無法回避革命者的血腥的正義。當社會能夠通過法制與理性進行改良的時候,我們不能倡導暴力。
法國也用圣水洗禮,用正義與理性,用思想與德性來洗禮。伏爾泰,倡導的是和平、寬容與理性。
上訪的困難,上訪的災難
當時的法國沒有設立信訪接待機構,只是法院獨立地審判了卡拉斯夫人的申訴。當時的法國宗教盡管不寬容,但還不至于窮盡心機,阻撓卡拉斯夫人到巴黎上訪。當然,地方當局也不可能指派專人,到巴黎截訪,讓卡拉斯夫人的問題,回到當地解決。
如果當地政府在巴黎將卡拉斯夫人強行安置到一個可控制的賓館,“管吃管住,解決問題”,并躲避媒體監督與報道,使卡拉斯夫人的問題“灰質化”,以拖延戰術使卡拉斯冤案成為法國歷史上永遠的難解之謎。而伏爾泰也壓根兒不知道,在法國某地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一起令法國蒙羞的事件,歷史又將如何書寫?
當時的法國(距今247年),沒有人提供這樣一種理論思維,就是通過壓制正義、壓制上訪,來維護王國的穩定。如果有人認為,卡拉斯夫人上訪,會造成革命力量興起,會引發法國大革命,那么,可憐的卡拉斯夫人只能犧牲自己與家庭的正義,來維護國家大局,使自己永遠走在上訪的路上,而無法到達終點,更無法獲取應有的正義。圖盧茲小鎮,法官們仍然逍遙自得于自己的不正義的判決,并等待著另一次不公正的判決來臨。伏爾泰也不可能寫出令法國與歐洲乃至世界動容的《論寬容》。讓國家獲得所謂的“穩定”,讓民間社會得到真正的“敗壞”,就會成為法國的國家精神追求,或成為法國社會的潛規則與暗實力。
路易十五無論如何殘暴,法國地方小鎮無論如何宗教迷狂,還好,巴黎的法律還能為蒙冤者升起一面正義的旗,使法國民間社會看到希望,也使法國歷史與法蘭西民族,獲得一份基于伸張正義的尊嚴。
讓我告訴你另一個安徽姑娘王蕊蕊(化名)的故事,這是我當時身邊發生的故事。
1990年,來自安徽的大學畢業生王蕊蕊考上了廣播學院研究生(現為傳媒大學),當她復試完成之后,導師告訴她,這門專業因為各種原因,不招生了,讓她明年再考或轉學他校。當她找到我們這幾位在京的同鄉后,我們的主張是到國家教委申訴。王蕊蕊到了國家教委,接待她的有關部門一位領導親自過問,并明確指示廣院招生辦,考上的王蕊蕊由所在學校調整專業,不得讓其個人另謀學校。王蕊蕊因此獲得了研究生學習機會,3年后順利畢業。
國家的權力意志與正義的伸張如果聯為一體,就能發揮巨大作用。如果當時的教委有關領導不接待來訪者,那么王蕊蕊就可能失去了學業,甚至可能走在上訪的路上;如果有灰色賓館的話,王蕊蕊就可能成為現在的李蕊蕊。
國家是通過追求穩定來獲得穩定,還是通過追求正義價值來獲得穩定?這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有人提出三個至上,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顯然是正確的、善意的取向,但并未明說三者之間的關系。其實在法律追求與國家追求、政黨追求之上,是人民利益至上,也就是正義至上。正義至上了,正義獲得伸張,民意就支持政府與執政黨,執政黨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通過正義的伸張,獲得一致。就是這么一個簡單的邏輯!
執政黨、政府、法律、民間力量、媒體,如果共同致力于將上訪問題公開化,將上訪個案公開化,聯合打壓那些制造不正義、不守法的地方政府、官員或勢力,使他們敬畏法律與正義,敬畏北京的權力意志,國家權力意志與法律正義聯為一體,國家的精神與社會穩定就會通過正義確立起來。我們現在看到的呢,是上述這些力量處于分離狀態,真正發揮作用的,卻是灰色力量,一種暗力量在維系著所謂的穩定局面,也就是強奸李蕊蕊的小強,還有灰色賓館,在實際控制著訪民,也就是控制著希望獲得公平正義的民間社會。
卡拉斯悲劇發生之后,伏爾泰思考的是“寬容”,李蕊蕊事件之后,中國主流社會要思考的卻應該是“正義”。國家要將“社會正義”作為第一價值來追求與倡導,正義對于公民社會與公民個體來說,都是第一價值,國家使用自己的權力意志來確立社會正義的主導價值,通過正義與和解,來實現和諧與穩定,這才是理性的、正確的路徑。當地方政府正在走向利益追求的時候,我們最需要中央政府確立價值追求作為權力意志的核心。
編輯 葉匡政 美編 黃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