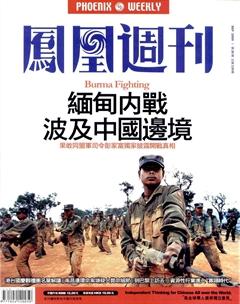韓福東:胡耀邦為何反對包產到戶
韓福東
今年是建國60周年,重新翻撿一下當代的一些史料,還是很有意義的。在1 961年共和國建政的第15個年頭,我國曾遭遇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挫敗。高歌猛進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催生出的“大躍進”,非但未能實現“趕英超美”目標,反而落了個饑荒慘淡。中央高層內部的分歧開始顯現,包括毛澤東本人·度都有了包產到戶可以試驗的意向。
胡耀邦此時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他帶了三個人在這一年的9月份,沿著黃、淮河平原農村跑馬觀花,考察了一番。雖然“所到之處,群眾都說形勢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調了,不瞎指揮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勞多得,生產、生活有了奔頭”,但胡耀邦仍在向毛澤東報送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農村察看》中,稱“包產到戶”為“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毛澤東在四天后批示:寫得很好,印發各同志,值得一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P574~575)
因為這個報告是耀邦同志所寫,它才格外具有文本價值。我們該如何理解他彼時的立場與抉擇?須知,我們今天看來荒誕不經的某些制度建設與政策走向,在當年卻有著十二分的正當性,非但不好笑,反而在一個不斷被強調的社會背景下有了堅硬的合法性內核。這就是時代的局限。
合作化運動是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起錨的。它有民意基礎(廣大貧下中農歡迎天上掉下的餡餅),理論上頗為動人(單只是即將到來的“拖拉機時代需要連片耕地”一項,就足以讓人對分散的小農經濟的落后有所認識,更何況還有一整套意識形態的支持),在實踐中也有斬獲(干勁十足的“翻身農民興修水利,成績斐然),不消說,榜樣的力量也是無窮的(蘇聯老大哥作為冷戰一極,外表光鮮)。
反對合作化的是些什么人?那些要拉馬分隊的,以中上農和富農為主;而他們正是要改造的對象。至于“大躍進”的災難,也完全可以歸結為一時的冒進和干部瞎指揮,邏輯上并不是合作化的必然結果。
合作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還可以推諉給傳統,認為只是過渡期癥候,而且更為辨證的是,它們與成績比起來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系”。亦即,問題受到遮蔽。好笑么?我們現在面對其他轉型社會的問題時,恐怕還尚未跳脫出此一思路。
所以胡耀邦在報告中說:“這種做法(包產到戶)已出現了一些難以解決的矛盾和糾紛……發展下去,最終會導致降低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并非無的放矢。現在公布的報告部分并未詳述哪些矛盾和糾紛,但它或許包括:鰥寡孤獨的贍養、公共設施的興建與維護,以及個體經營與即將到來的機械化耕種的可能沖突……
因此,“大躍進”暴露的問題,終未能抵過胡耀邦對另一種價值的強調——被強化的反資本剝削與殖民的背景,以及對一種終極目標的確信,決定了哪種價值是時代的主軸。當一個主義被樹為“普世價值”(套用當下的一句流行語),它很可能將逐漸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因為這個作為真理化身的主義,有其自身的價值偏好,在關涉到兩種價值的沖突時,可能會本能地遮蔽另一種價值,而放大它所偏好的部分。而它所遮蔽的那種價值,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可能又會被發現格外重要。
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主義都有異化的可能性。
20世紀足夠豐富多彩,留給我們的歷史省思也足夠多。那些曾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的理念,其風行一時,都有深刻的歷史與社會背景。如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再如蘇聯的集體農莊主義,那著魔一般的信仰,也根植于一種在批判現實世界不公基礎上積累的合法性。誰敢說我們今天不會犯一個僅僅是改頭換面了的類似的錯bR?如果只是換了一種主義,而仍沿襲遮蔽與放大的老路子,那我們可能要唏噓于黑格爾的那句名言:我們從歷史中所學到的惟一東西是,沒有人能夠從中學到任何東西。 編輯 葉匡政 美編 黃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