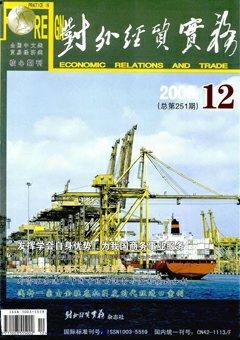簡評《鹿特丹規則》
姚新超
2008年12月聯合國通過了《聯合國全程或部分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公約》(《鹿特丹規則》),決定于2009年9月23日在荷蘭鹿特丹開放簽署。該規則制訂的主要目的,是取代現有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以實現貨物運輸規則的國際統一。與以往的國際公約相比,《鹿特丹規則》包含許多革新性的內容。該規則生效實施后,無疑將對國際貿易實務和慣例、國際航運及其立法等產生重大影響。
一、規則誕生的背景
在《鹿特丹規則》誕生之前,關于規范國際貨物運輸的公約包括《海牙規則》、《海牙一維斯比規則》和《漢堡規則》。上述三個公約同時并存的局面,進一步加劇了國際貨物運輸規則的不統一。其結果是,極大地增加了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為此,國際社會不斷呼吁對國際貨物運輸規則進行全球統一。
國際貨物運輸方式的變化是《鹿特丹規則》誕生的重要原因。過去海運和陸運通常是分段進行的,承運人僅對其運輸區段內的貨物負責。但隨著集裝箱多式聯運的發展,一份運輸單據、承運人負責全程運輸的門到門運輸越來越普遍。而《海牙規則》和《海牙一維斯比規則》只規范船至船運輸,《漢堡規則》也僅擴大至港到港運輸。這種承運人的責任期間不僅與運輸實踐相脫離而且無法滿足貨主門到門運輸的要求。自2002至2008年,歷經6年,新的國際公約終于誕生。由于2009年9月將在荷蘭鹿特丹正式簽署發布,因此新公約被稱之為《鹿特丹規則》。
《鹿特丹規則》共計18章、96條。與以往的國際貨物運輸公約相比較,《鹿特丹規則》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二、承運人責任期間擴大
為了適應集裝箱多式聯運“門到門”運輸方式的變革,《鹿特丹規則》明確規定,承運人的責任期間自承運人或履約方為運輸而接收貨物時開始,至貨物交付時終止。由于該規則擴大了地域適用范圍,因此承運人的責任期間可延伸至“門到門”。
該規則第一次將承運人的責任范圍確定在“海運+其他”,即海運區段及與海運連接的陸上運輸,鐵路、公路、內河水運甚至是航空運輸都包括在內。這是規則的重大變革之一。因此,該規則拓寬了承運人的責任范圍,有利于維護貿易商的利益。
三、承運人義務與賠償責任的變化
《海牙規則》下,承運人的責任基礎是“不完全過失責任”。《漢堡規則》采用了推定過失責任,即完全過失責任。
《鹿特丹規則》也采用了完全過失責任,廢除了現行的“航海過失”免責和“火災過失”免責。但其對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定不同于《漢堡規則》。承運人除了證明自己沒有過失外,還可以通過證明存在一項或多項免責事項免除其對貨物的賠償責任,除非索賠方可以證明免責事項的產生是歸因于承運人的過失。《海牙規則》下承運人的基本義務是,謹慎處理使船舶適航和妥善管理貨物的義務。《鹿特丹規則》原則上秉承了上述規定,但其具體義務內容有所不同。
1.增加“履約方”和“海運履約方”的概念。《鹿特丹規則》除界定了“承運人”的概念,還首次界定了“履約方”和“海運履約方”。“履約方”是指承運人以外的,履行或承諾履行承運人在運輸合同下有關貨物接收、裝載、操作、積載、運輸、照料、卸載或交付的任何義務的人;以該人直接或間接在承運人的要求、監督或控制下行事為限;并且不包括不由承運人,而由托運人、單證托運人、控制方或收貨人直接或間接委托的任何人。“海運履約方”僅限于貨物自裝貨港至卸貨港期間履行或承諾履行承運人任何義務的履約方。內陸承運人僅在履行或承諾履行其完全在港區范圍內的服務時才視為海運履約方。該規則極大地擴展了承運人的范圍和含義,以使該規則盡可能與運輸實踐相符。
2.承運人保證船舶適航義務的時間延長。《鹿特丹規則》基本保留了傳統適航的內涵,明確適航義務的標準仍然是謹慎處理。但該規則將承運人保證船舶適航的義務由《海牙規則》的“開航前和開航時”延長至整個海上航程。同時該規則順應了航運實踐的發展,明確規定承運人提供的集裝箱應適于且能安全接受、運輸和保管貨物,并在整個海上航程中保持這種狀態。
3.承運人管理貨物義務從七個環節擴大到九個環節。《海牙規則》規定,承運人的管貨義務貫穿于七個環節(裝載、搬運、積載、運送(輸)、保管、照料和卸載所運貨物)。《鹿特丹規則》明確規定,承運人應當妥善而謹慎地接收、裝載、操作、積載、運輸、保管、照料、卸載并交付貨物,即管貨義務貫穿于九個環節。承運人管貨義務的擴大有利于保障貿易商的貨物權益。
4.承運人遲延交付貨物的責任變化。《海牙規則》未明確規定遲延交付問題。《漢堡規則》首次規定了承運人應承擔遲延交付貨物責任。依據《鹿特丹規則》第17條,若托運人能證明:貨物滅失、損壞或遲延交付,或造成、促成了滅失、損壞或遲延交付的事件或情形是在承運人責任期內發生的,則可以要求承運人對貨物滅失、損壞和遲延交付負賠償責任。依《漢堡規則》,承運人對于遲延交付造成損失的賠償責任不超過該遲延交付貨物應付運費的2.5倍,但不得超過運輸合同應付運費的總額,即規定了兩次限制,而依《鹿特丹規則》第60條規定,只有一次限制,即為遲延交付貨物運費的2.5倍。
5.承運人賠償責任限制數額提高。根據《鹿特丹規則》的規定,承運人對于貨物滅失、損壞的賠償責任為每單位875SDR或毛重每公斤3SDR。這一規定較之《漢堡規則》從每件貨物666.67SDR或每公斤2SDR(以其高者為準)分別提高了31.24%和50%。
6.承運人免責事項發生變化。依據《海牙規則》,承運人可以按照其第4條規定的17項免責事項享受免責權利,且僅明確了第17項“兜底條款”免責的舉證責任。
《鹿特丹規則》延續了《海牙規則》的基本理念,但與《海牙規則》采取“開放式列舉”不同。《鹿特丹規則》采用了“封閉式列舉”,即明確規定免責事項僅限于公約列明的15項。但也有以下變化:第一,增加了“海盜、恐怖活動”的規定。這反映當今航運實踐的現狀和發展情況。第二,明確火災免責僅限于在船舶上發生的火災,不包括陸地上發生的火災。第三,根據以往公約的規定,只要是救助或企圖救助人命或財產都構成合理繞航,承運人無需對由此導致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但《鹿特丹規則》則強調,對于財產救助的免責必須是采取合理措施的結果。第四,增加了為避免環境損害而采取合理措施導致的貨損承運人可以免責的規定。
整體而言,《鹿特丹規則》下,承運人或其履約方的義務和責任有所加重。這一變化符合當前國際航運發展的趨勢。
四、批量合同當事人具有較大的合同自由
以往國際貨運公約均對承運人的責任進行嚴格限制,以防止承運人濫用合同自由和自身優勢免除或減輕其責任。《鹿特丹規則》一方面對運輸合同當事人的合同自由進行嚴格限制的同時,另一方面則在其第80條賦予批量合同當事人較大的合同自由,即在承運人與托運人之間,批量合同可以背離(增加或減少)本公約規定的權利、義務和賠償責任,即合同自由。所謂批量合同是指,在約定期間內分批裝運約定總量貨物的合同。貨物總量可以是最低數量、最高數量或一定范圍的數量。其常見的類型是班輪運輸中的服務合同。
隨著現代物流的發展,批量合同已大量使用。賦予批量合同當事人合同自由的基本理念是在簽訂批量合同情況下,承運人和貨方之間的權力、義務相對來說比較平等,是否簽訂合同,簽訂什么樣的合同由承托雙方決定。《鹿特丹規則》考慮到某些貨主力量和地位的增長,具有平等談判的能力,為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而對批量合同作出特別規范。
五、港口經營人須遵守強制性公約
《鹿特丹規則》將海運履約方的范圍擴大至任何在海運過程中參與處理和管理貨物的群體,因此港口經營人承擔與承運人相同的賠償責任。以往港口經營人的責任通常適用國內法,而國內法對港口經營人的責任既無最低責任又無責任限制規定。現在將其納入公約中,作為海運履約方,與承運人同等對待。這一變化對港口經營人可能會產生雙重影響,一方面可能加重了港口經營人的責任,但另一方面,可以享受與承運人相同的責任限制,有可能降低其責任。
六、貨主責任及義務的變化
與過去的國際公約相比較,《鹿特丹規則》對貨主的義務規定更加明確。
1.托運人實行“推定無過失責任制”。《鹿特丹規則》對托運人的賠償責任制的規定是過去公約所沒有的,即在對承運人發生損害時,除非承運人能證明是由于托運人違反本公約規定的義務或托運人的過失造成的,托運人無需承擔賠償責任。
上述規定對托運人比較有利,按照這一規定,一旦發生貨物滅失或損壞首先推定托運人沒有過失,承運人必須承擔舉證責任,舉證不成則托運人不負責任。
2.托運人對承運人的義務。《鹿特丹規則》第27條規定了托運人應向承運人承擔的責任。該條規定:(1)托運人應交付備妥待運的貨物。在任何情況下,托運人交付的貨物應處于能夠承受預定運輸的狀態,包括貨物的裝載、操作、積載、綁扎、加固和卸載,且不會對人身或財產造成損害。(2)根據第13第2款訂有約定的,托運人應妥善而謹慎地履行根據該約定承擔的任何義務(即承運人與托運人可以約定由托運人、單證托運人或收貨人裝載、操作、積載或卸載貨物。)(3)集裝箱或車輛由托運人裝載的,托運人應妥善而謹慎地積載、綁扎和加固集裝箱或車輛內的貨物,使之不會對人身或財產造成損害。
3.向承運人提供信息、指示或相關文件的義務。《鹿特丹規則》第55條對托運人提供有關信息等的義務予以明確規范。該條規定:托運人應向承運人或履約方及時提供承運人履行其在運輸合同下義務而可能合理需要的有關貨物的信息、指示或文件;若承運人經合理努力無法確定控制方,或控制方無法向承運人提供適當信息、指示或文件的,則應由托運人提供此種信息、指示或文件。若承運人經合理努力無法確定托運人的,應由單證托運人提供此種信息、指示或文件。
4.貨方承擔裝卸、卸載、積載(FIOST)義務。《鹿特丹規則》第13條第2款規定,若經承運人與托運人協議,可由托運人、單證托運人、收貨人負責裝載、操作、積載、卸載貨物。
這一規定的含義是:第一,該規則允許承托雙方訂立由貨方承擔裝卸、卸載、積載(FIOST)義務的協定,并明確其合法性。第二,通過該規則的規定,明確了托運人或單證托運人應當承擔該項義務。
5.收貨人及時提貨。《鹿特丹規則》第43條和44條規定,一方面收貨人有義務及時提貨;另一方面對收貨人及時提貨或及時接受交貨設置了條件,其條件是收貨人“要求交付貨物”,即向承運人要求交付貨物的收貨人才有及時接受交貨的義務。換言之,收貨人(包括提單持有人)在沒有向承運人要求交付貨物時,他們并無及時提貨的義務。另外,收貨人還必須證明其收到了承運人交付的貨物,否則承運人可以拒絕交貨。
6.記名提單的提貨義務。目前,關于記名提單的交貨問題,各國的規定差別較大。《鹿特丹規則》試圖通過其第45條和第46條的規定,對記名提單下的貨物交付問題制訂統一的國際規范。依據該規則第45條,只要收貨人證明自己的身份,即可提貨而無需繳回提單;而第46條又設置了若單證載明必須繳回提單才能提貨的,則應當憑單證交付貨物。由此可以看出,《鹿特丹規則》將記名提單分為兩類,即提單上載明必須繳回提單才能提貨的,則要求憑單交付貨物;若無此載明的,則無需憑單交付貨物。很明顯,上述規定試圖同時滿足不同國家的法律的不同規定。
七、單證托運人的地位
《鹿特丹規則》首次設置了“單證托運人”的概念。它是指托運人以外的,同意在運輸單證(注:如提單)或電子運輸記錄中記名為“托運人”的人。在貿易合同的買方與承運人簽訂運輸合同,如F組貿易術語的條件下,買方是理所當然地成為“托運人”,而負責向承運人實際交付貨物的賣方則可成為“單證托運人”,即運輸單證中記載賣方為“托運人”。 “單證托運人”的規定其實就是為解決以FOB為條件的貿易而制訂的。
以FOB條件出口貨物時,由于買方安排貨物運輸并與承運人訂立貨物運輸合同,此時買方是托運人。賣方將貨物交給承運人接管后,通常要求承運人向其簽發以賣方為托運人的運輸單證,如提單。于是就出現,運輸單證上的托運人(賣方)不是與承運人訂立運輸合同的托運人(買方)。國際社會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曾進行了不少探索。《鹿特丹規則》界定了“單證托運人”的概念,企圖解決這一問題。這一創新界定的特點是,(1)“單證托運人”不是“托運人”,托運人才是與承運人訂立運輸合同的人,“單證托運人”與運輸合同的承運人不存在合同關系;(2)“單證托運人”在向承運人實際交付貨物后,必須經“托運人”同意才能向承運人索取運輸單證并在單證上記載;(3)對“托運人”規定的權利與義務適用單證托運人。
八、控制權與貿易實務銜接
《鹿特丹規則》還首次引入控制權概念。所謂“控制權”即貨物控制權,是指根據該規則規定,按照運輸合同向承運人發出有關貨物的指示的權利,具體包括就貨物發出指示或修改指示的權利,但此種指示不構成對運輸合同的變更;在計劃掛靠港或在內陸運輸情況下,在運輸途中的任何地點提取貨物的權利;由包括控制權人在內的其他任何人取代收貨人的權利。
根據該規則的規定,托運人、單證托運人、單證持有人、收貨人等都是運輸各個階段有資格主張“控制權”的人,即“控制權人”。這一新的規定,使得提單僅表示對“物”(貨物)的控制權,而非為“物權”憑證,這對平息提單究竟是物權憑證、所有權憑證、抵押權憑證還是債權憑證之爭可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在以往的國際貨物運輸中,多數情況下使用的是可轉讓提單,賣方可以通過控制提單來行使對貨物的控制權。但目前海運的情況有所變化,使用可轉讓單證的情況正在逐漸減少。《鹿特丹規則》規定控制權可以保護未使用可轉讓單證進行貨物運輸的賣方利益。因此,該規則關于控制權的內容是全新的,有利于貨物運輸與貿易實務的銜接。
九、無單放貨的規定
承運人無單放貨問題是國際貨物運輸中爭論多年的問題。《鹿特丹規則》考慮到在航程較短的運輸情況下,憑提單放貨實際操作上存在困難,因而允許在一定條件下,按照一定的程序可以不憑提單放貨,即無單放貨。這是一個非常新的規定。
該規則將航運實踐中,承運人憑收貨人的保函和副本提單交貨的習慣做法,改變為承運人憑托運人或單證托運人發出的指示交付貨物,且只有在單證持有人對無單放貨事先知情的情況下,才免除承運人無單放貨的責任。若單證持有人事先對無單放貨不知情,承運人對無單放貨仍然要承擔責任,此時承運人有權向上述發出指示的人要求提供擔保。該規則為承運人實施無單放貨設定了條件,即可轉讓運輸單證必須載明可不憑單放貨。
《鹿特丹規則》關于無單放貨的規定,雖然本意值得稱贊,但其最大的憂慮是可能損害提單作為貨物控制權憑證的作用,而承運人可以不承擔賠償責任的風險,可能為其圖謀欺詐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