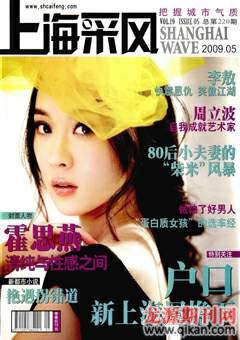胡楊鏡頭下的上海變遷
胡凌虹
上海百姓生活流
記者:28年前你就開始做《上海弄堂》專題系列,而且針對的是上海的所謂“下只角”部落,你為何選擇這些地方作為你的攝影主題?
胡楊:當時大家熱衷拍攝的都是光鮮的照片,帶有宣傳色彩,缺少“草根性”。我覺得上海弄堂不僅僅是石庫門,小資也不是上海的全部,我想彌補這一塊內容。同時,1978年中國政府實施“改革開放”政策,1980年上海市政府開始著手城市改造。我意識到“下只角”的弄堂將被拆除,于是決定拍攝記錄“下只角”弄堂,以民間的眼光來反映居民們的日常生活,展現底層上海老百姓的生活流。
記者:生活在“下只角”弄堂的居民是怎樣一群人,給你最大的感觸是什么?
胡楊:這里的居民大多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湖北、四川等地來上海打工的產業工人。由于受經濟條件的限制,“下只角”弄堂里居民的住房面積普遍都很小,人均面積2至6平方米左右,兩三代人同堂的現象非常普遍。家家戶戶的門緊挨著門,平日里房門大都是敞開著的,鄰里之間相互串門,過著類似于“社群”的生活,被稱為“都市里的村莊”。由于長期生活在一起,左鄰右舍無形中也建立起了不是親人,但勝似親人的和睦關系。弄堂里有一句俗話“遠親不如近鄰”,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人們的生活存在著較大的相互依賴,不管誰家發生困難,鄰居們都會有力出力,有錢出錢,互相幫助,相互照顧。
記者:從二十多年的變遷中,你覺得“下只角”居民們生活以及心理層面有怎樣的轉變?
胡楊:近二十年來上海許多“下只角”弄堂已經被拆除,原先弄堂里的許多居民住進了獨門獨戶,有客廳、臥室、廚房、衛浴室的公寓。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居住的建筑格局的改變,人們之間的關系開始越來越淡漠、疏遠了,同一樓層的鄰居“住在隔壁,離得很遠”。從某種角度看,對自身隱私的保護也是法律意識增強的表現,但是我們還是不禁要反思:難道社會的發展、經濟的增長,必須以人情作為犧牲的代價?我要向社會學家、建筑學家提出一個問題,是否可以把公寓房有私人空間的優點和弄堂里的鄰里和睦親密關系結合起來,建設出更人性化的居住環境?
記者:之前有“上只角”、“下只角”地域上的貧富之分,你覺得現在上海貧富差距拉大了還是縮小了?
胡楊:以前只是地域不同,但是每家每戶的月工資收入是差不多的,由于種種原因,有些人分到了“上只角”的房子,不過并不表明比“下只角”的人家有錢。但是現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世貿濱江,湯臣一品等高檔住宅區,房價非常高,而虹口、楊浦、普陀區里還有不少貧民窟。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地區,即便是政府提供給難民住的廉租房,人均面積也在30平方米左右,每幢大樓里都有公用客廳,可以租用開PARTY,還有健身房和游泳池。加拿大政府對國民居住的標準定得很高。
記者:你拍攝上海近三十年,實際上也見證了改革開放三十年里上海的變化。從橫向看,在不同的年代各有怎樣的特征,從縱向看,有怎樣大的轉變?
胡楊: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全國而言,上海人是很有自豪感的。當時上海每年上交給中央的錢占全國的1/6,許多全國名牌產品都出自上海,外地人以能吃上、用上、穿上上海產品為榮;八十年代,上海人發現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紛紛出國留洋謀求發展,“一流人才走出國,二流人才進外企,三流人才留國企”;九十年代至新世紀,上海的經濟騰飛了,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國的人才,以及當年出國學成的人才都紛紛回流前來上海尋求發展,上海人又一次有了感覺。但同時又感覺自身競爭實力不強,上海人普遍太安于過舒適的“小日子”,缺乏競爭的勇氣和闖勁。
記者:你覺得為何開放的環境沒有影響到上海人,雖有經商頭腦,但缺失了大膽創業的氣魄?
胡楊:上海人雖然“精明”但是氣魄不大,缺乏做出“大手筆”的勇氣,比較喜歡過舒適安逸的“小日子”。
中產階級更戀家
記者:2004年1月到2005年2月底,你拍攝《上海人家》專題系列,總共拍攝了500戶人家,包括富裕和貧窮的,以及中產階層。不同階層的人對“家”的理解、感受應該不同吧?
胡楊:中產階級更加留戀家,他們喜歡安逸的生活,注重享受。家對窮人而言沒有太大的吸引力。而富人很忙,在外應酬不斷,家就像賓館一樣。
記者:500戶人家各有不同,但是否有某些共性的地方?
胡楊:對。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他們都會將自己的家布置得很舒服,有裝潢意識和愛美意識。我有一個朋友,他家只有16平方米,但是他很巧妙地隔出了臥室、會客區、衛生間、吧廳、兒童娛樂區,可謂“螺絲殼里做道場”。有人家里窮,沒錢買墻紙,就在墻上貼滿了超市里的廣告促銷單,非常有特色;有錢人的家裝潢布置就奢華講究,有人把70、80平方米衛浴間的天花板和墻上貼滿金箔;有人把浴缸放客廳里,邊看DVD,邊泡澡。
記者:上海人很注重家的私密性,這種意識是什么時候開始的?
胡楊:上世紀90年代起,上海人在保護個人隱私方面的意識開始加強了。原因在于,第一,富人不愿意露富,怕稅務局、窮親友找麻煩;窮人也不愿意顯窮,怕被人看低。第二,外表不一定能看出是否有錢,但家能體現出來。比如,拍《上海人家》時,我想去一位以前很有名的女歌唱家的家里拍照,她委婉地拒絕了。因為雖然住在“上只角”,但“過期明星”收入不多,丈夫又生病,家里境況不佳了,所以不愿意出現在媒體上。
上海本地青年要有危機感(
)
記者:繼《上海人家》和《上海弄堂》之后,你又推出了《上海青年》專題,通過采訪并拍攝了300位生活在上海,出生于1970~1989年的青年,你發現上海青年有哪些特質?
胡楊:根據我的采訪,發現70后更有責任心,80后相對較自我。他們的共同點在于穿著和觀念時尚,與外國青年差別不是很大,都很國際化。比如對待一夜情等性觀念方面,他們可能比外國人更加開放。他們對政治不太感興趣,更多的關心自己的未來,希望有更豐厚的收入供其享用。大都很現實、很物質。
記者:在采訪拍攝中,你覺得來上海闖蕩的外地青年和本土的上海青年有怎樣的差異?
胡楊:我很推崇 “新上海青年”,上海本地的青年最起碼依靠父母有吃有住,而新上海青年是真正的白手起家,租房子、掙錢。在價值觀上他們會更現實一些,因為每天都要面對現實,必須比本地青年更努力、更優秀才能不被淘汰,在情感上他們很孤獨。很多本地的青年在能力和素質上沒法跟新上海青年比,所以上海本地青年要有危機感啊!
記者:你覺得上海青年與上一輩的困惑有怎樣的不同?
胡楊:中年人生存壓力最大,單位里是骨干,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所以中年夫妻間吵架多,自殺率高。而年輕人有理想有志向,希望事業上有發展,但是在甜水里泡大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交際、組織協作能力較差,成功就相對較難,而且交際圈小,很多當婚當嫁的青年人連找對象都困難。
記者:從年輕人身上可以看到未來,你覺得上海的未來會怎樣?有憂慮嗎?
胡楊:其實以前我不太看好80后、70后,覺得他們沒有50后、60后有責任心,媒體上也是貶義的評價多。但是做完《上海青年》專題后,通過與他們的交流,我對他們有了新的認識。“5.12”四川汶川地震期間,涌現了一大批青年志愿者,在國家和人民有危難的時候有所擔當,很優秀。所以對未來不必擔憂。
上海與攝影師
記者:上海給你的影響,或者說帶來的最大的益處是什么?
胡楊:其實原來我不太喜歡上海這座城市,覺得上海男人,就像我自己不大氣,太患得患失,目光短淺。于是我就去北京歷練了一番,北京的氛圍更加大氣,回來后我發現自己視野開闊了,氣魄也變大了,所以我能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策劃、實施我的選題。《上海弄堂》拍了二十八年,《上海人家》至今采訪拍攝了500多戶人家。所以我覺得上海的男人應該去北京生活一段時期,心胸可以變得更開闊;北京的女人應該到上海生活一段時期,言行舉止會變得更有情調。
記者:有一個概念叫“海派攝影風格”,具體看這是怎樣一種風格?
胡楊:是海派文化的衍生,其實上海攝影有很多流派,是多種流派的匯合。海派文化包羅萬象、海納百川。
記者:你覺得上海這座城市能給予攝影者怎樣的成長土壤?
胡楊:第一,從影像的角度看,改革開放的這三十年里是上海開埠以來最豐富多彩的。有許許多多的題材可拍攝,為攝影人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我還有許多專題想拍攝,希望能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
胡楊:
紀實攝影家。作品有“上海影像三部曲”一一《上海人家》、《上海弄堂》、《上海青年》。作品曾在英國國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法國東京宮美術館、澳大利亞昆士蘭美術館、奧地利現代藝術博物館、芬蘭國家美術館和當代藝術博物館、荷蘭攝影博物館、北京今日美術館展出,曾參展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俄羅斯攝影雙年展、廣東攝影雙年展、山西平遙攝影節,2009年9月還將參加美國國際攝影中心的展覽;攝影集被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和德國科隆火炬手出版社出版,作品被澳大利亞昆士蘭美術館、廣東美術館、山西平遙攝影博物館以及各國私人收藏。